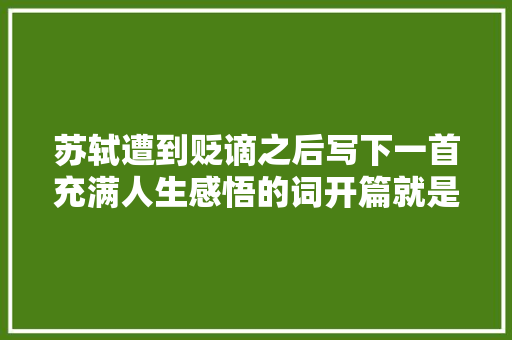作者在这首词中,借助对中秋夜晚的自然场景,以及自身心境的描写,以细腻、婉约的笔法表达了对兄弟苏辙的思念之情。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赏析《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北宋·苏轼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口语译文:
人间间过往的经历,就像大梦一场。短短几十年的生命,又要遭遇几次不幸呢。入夜后,秋风卷起落叶,在回廊上发出嗡嗡鸣响。这浓得化不开的愁情,已经染到了我的眉边、鬓上。
没有好酒,访客自然稀少。天边的明月,又时常被云遮住。在这个团圆之夜,究竟是谁在陪伴着天上的明月?我手握着羽觞,满怀凄然地望向北方。
想要精确地理解这首词,就不得不提到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和韶光。从这首词中的内容,我们很随意马虎判断得出结论:这首词一定是写于苏轼42岁时,即公元1079年“乌台诗案”发生往后。
苏轼在“乌台诗案”发生以前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比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墨客要幸运得多。他二十二岁少年景名,之后被外放到凤翔当了一个签书判官。
但是这统统,并不是由于受到了任何人的打压,只是由于他当时太年轻,天子想磨炼他。后来他和新党的人反面,自请外放到杭州,过的也是风花雪月的洒脱人生。
在杭州这个地方,苏轼还顺便纳了一个十二岁的小妾王朝云。不过在杭州任上时,苏轼虽然已经与兄弟苏辙天各一方了,但是在苏轼身边的“狐朋狗友”一贯很多。
以是,这统统都与《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中提到的“酒贱常愁客少”情形不符。“酒贱、客少”是在他被贬黄州往后,才会涌现的情形。
由于“乌台诗案”事涉谋逆,只管由于天子的庇护,苏轼并没有丧命,但是初被流放之时,他的精神状况,曾经处于生平中最为糟糕的时候。
由于溘然遭遇人生的大起大落,苏轼担心遭到亲朋好友的嘲笑,以是一到黄州,自己就先跑到一座和尚庙里住了一两个月。后来创造彷佛并没有人取笑他,他才敢出门。
结果苏轼在黄州时又生了一场重病,外界一度传说他已经去世去。在这种繁芜的情形下,他身边的亲朋好友骤然减少,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此有人认为,这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是苏轼在黄州时所作。不过,这首词更有可能是他晚年被贬到海南儋州时所作。由于“酒贱常愁客少”,同样适用于他被谪儋州时的情景。
这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开头第一句“世事一场大梦”,便给人以强烈的震荡。仿佛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但它只不过是庄子“人生如梦”思想的延伸而已。
实在这一句词,也并非是苏轼“大彻大悟”之后的感想。自打二十岁成名之后,在苏轼生平中的各个阶段,都不断地重复发出“人生如梦”的声音。
可以说“世事一场大梦”,便是苏轼对人生的最基本的认识。这种道学家的人生不雅观,是苏轼在眉山期间形成的,与他之后的任何遭遇都无关。
至于之后的各种不幸打击,只是在不断地证明这种人生不雅观的精确罢了。词中的第二句“人生几度新凉”,才是对作者心声的直接反响。
自从“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先被贬到黄州。后来苏轼在晚年又因得罪新党,被贬惠州、再贬儋州。
如果说这首词是写在黄州期间,那么便说不上“人生几度新凉”了。以是有人认为这首词,是苏轼在儋州所写。
其余,词末提到了“北望”一词。如果把这首词看作是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作品,那么他身在海南,北望中原就说得过去了。
如果苏轼填词时身在黄州,苏辙当时人在江西,处于黄州东南方向,那么“北望”又当作何理解呢?于是也有人把末句的“北望”阐明成苏轼在“北望汴京”,说他词中还在惦记着圣恩。
不过这样的阐明,明显不符合苏轼“中秋词”的一向风格,同时也不符合这首词一开始定下的基调。
“世事一场大梦”二句,表面上看说的是人生统统皆是虚妄,不值得想念,但是事实上专指功名利禄都是虚妄。
由于人们对功名的热切愿望,每每换来的是各类残酷的打击。这些打击,便是这首词里所说的“人生几度新凉”。
苏轼生平三次遭到贬谪,初贬黄州四十二岁,虽然极度痛楚,但是末了熬过来了,还写下了千古第一名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但是二贬惠州,三贬儋州时,他已经是一位头秃齿摇的花甲老人了。经由屡次打击,多番贬谪后,一想到这些不堪往事,苏轼只会以为痛楚万状。
就连秋夜回廊上的风,都在为他的不幸遭际发出不平的鸣响。秋絮像秋霜一样,染白了他的眉毛和鬓发。
试问在这种情形下,苏轼还会对“圣恩”抱有什么期望吗?如果还有,那么他可能是屈原、杜甫,绝对不可能是苏轼了。
以是这首词的创作主旨,只能是思念弟弟苏辙。而“北望”一词,也只能是望向苏辙所在的方向。
如果从上面这个角度来理解这首词,那么词下阕的“酒贱”二句,便是作者当时处境的真实写照了。
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后过得十分清贫,在黄州时他还能吃猪肉,到惠州他只能啃羊骨头,但是末了贬到了儋州,他就连猪骨头都啃不上了。
初到外洋蛮荒之地,苏轼乃至连一个办公地点都没有,只能寄住在一间庙子里,以是哪里来的朋友呢?同时,“月明多被云妨”一句也是实写。
最末两句“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悲惨北望”的创作手腕,类似白居易的“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这是在假借对明月的关照,陈说自己在中秋佳节对弟弟苏辙的思念之情。
结语《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当中蕴含的哲理,虽然走不出庄子画下的道道,但是在抒怀氛围的渲染方面,依旧颇为出色。
词的上半阕由人生哲理出发,写到个人经历总结。再通过“风叶鸣回廊”详细场景的渲染,到达“眉头鬓上”的细节描写。
以层层剥壳的办法,从抽象到详细,以极具情绪的细腻的描写,揭示了众人盲目追求功名利禄的悲剧性。
词的下半阕落足于现实,借着对云中“孤光”的关照,表达出了苏轼对兄弟“共看明月”的失落望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