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曾敭
鼎革之际平淡居京
张曾敭因秋瑾案开缺浙江巡抚后,病情一度恶化,有传言他常对人说:“秋瑾女士之事,吾之过也”。自卸任浙巡至辛亥革命爆发,张住在北京顺治门外贾家胡同,此后他险些没有留下笔墨记录,这里据一些碎片资料,对其居京生活略加缀叙。
张居京期间,屡有传言称清廷拟将其再次起用。《顺天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十仲春二十七日(1908年1月30日)刊文:“开缺山西巡抚张曾敭,闻政府以其才具不宜外任,但其于外省环境阅历尚熟,拟保其留京,以侍郎位置之,或调入资政院,以免有遗才之患。”随后该报又刊出:“开缺山西巡抚张曾敭才堪大用,政府各大臣议令或入资政院襄助统统,闻张现仍力辞,拟回籍养疴。”但张并未回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仲春时仍在北京,且病情好转。十月,《大公报》宣布称:“前浙江巡抚张曾敭起用之说喧传已久,刻据宦海近息……闻某枢臣以该抚前在闽藩任内政绩颇属可不雅观,拟即保以闽督之任。”然目前未见任何清廷欲再次起用张的官方资料。其仕途生涯在秋瑾案后,永久闭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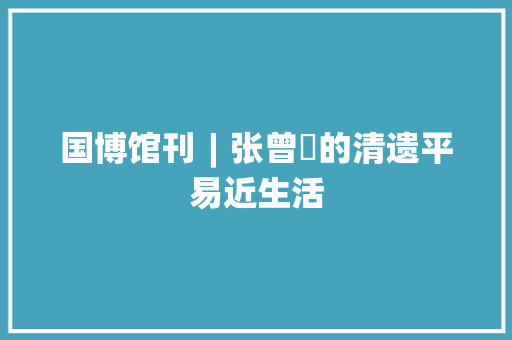
张居京期间,多次看望张之洞,并与鹿传霖等人往来甚频。鹿于光绪三十四年仲春十一日拜访张之洞,张曾敭在座。四月十四日,张拜会鹿。八月初十,鹿拜会张和李符曾。孔祥吉提及张曾敭前去看望病中的张之洞。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张之洞去世。二十三日,江瀚前去哀悼,遇见同来哀悼的张曾敭。是年闰仲春,蛰居25年的陈宝琛再次入京为官,后与张来往甚密。陈写道,张之洞去世后,他常与张曾敭一道回顾过往,感慨时局。玄月一日,江瀚拜访张,二人相谈甚久。玄月初八日,张找江瀚,对其所撰《宗孔编》十分讴歌,索两册而去。玄月十五日,江去祭奠张之洞,遇见同来的张曾敭。十七日,江“赴张宅吊文襄公并为陪……伊与小帆中丞因祭文忠先去”。十月二十二日,江拜访张未遇。由是不雅观之,张其居京期间,并无太多活动,多为退休官员的日常生活。
同年玄月十四日,林纾、沈瑜庆等人相聚于张曾敭寓所,评论辩论伊藤博文被刺身死一事。林说:“伊藤处心积虑,欲灭中国……虽为日人元勋,于我则首恶也……吾国当枢,乃皆庸才,不能乘此奋发有为,则伊藤之去世,于吾初未有补充。”林道出此言时,张亦在座。可见他虽未生动于宦海,却依旧关注着时局变革。因此,张卸任巡抚后的生活,多系僚友间的相互拜会。此外,张与僚友相聚时,亦关注着时势变革,却也仅限于此,再未涉足任何政事。
辛亥革命后,许多前清官员以遗民自居,张亦然。沃邱仲子在1921年出版的《当代名人小传》中,便将张归为清室遗臣。清室覆亡后,张“避地涞水”。在这里,他与劳乃宣多有交往。劳于1911年隐居涞水。闻劳隐居后,陈宝琛有诗云:“忍见衣冠同一劫,得安耕钓即吾乡。”后陈又作《得韧叟涞水书叠前韻为答并柬小帆》。“小帆”即张曾敭。这是陈宝琛和张、劳二人来往较为密切的一段韶光。辛亥后大变的场合排场,使拥有权势的前清旧臣一时无所适从,他们与处于相同境遇的遗臣相互倾诉,以获抚慰。
1912年2月15日,即清帝逊位后的第三天,陈宝琛、宝熙二人前往涞水看望张、劳二人,并留有《十仲春二十八日同瑞臣楼樵访小帆韧叟于涞水再叠苍字韵》,谓:“山向畿西自郁苍,看人襟泪一行行。相从旷野伤吾道,差喜幽居近帝乡。雾凇障天消夜雪,风沙捲地失落春阳。杜鹃臣甫容勤拜,东眺犹应胜乐浪。”据此,张隐居涞水的韶光,至迟应在1912年2月之后。同年,劳乃宣、张曾敭、宝瑞臣、徐梧生等人“同赴易州西陵拜景庙暂安殿,并谒泰陵”。此时民国肇建,张去拜会清皇陵,便是他誓作遗臣的佐证。
因张曾任封疆大吏,且敕令杀害了以秋瑾为首的革命党,而革命是导致清朝覆灭的主因,故张在遗民群体中享有较为爱崇的地位,成为遗民诗词歌颂、书写的工具。
章梫所作《赠张筱帆中丞一首》有云:“畺符脱手狎渔樵,亲见铜仙泪未销。载酒月明晋阳寺,沈珠风靖浙江潮。词林物望拥前辈,故国衣冠梦早朝。蹇蹇孤忠谁作伴,桐乡遗老与招邀。”该诗写于1912年4月前后。林立认为,遗民词人间多形成一些身份分外的文学团体,相互酬唱,以在精神上彼此扶持,张等亦然。章梫先容了张的归隐生活后,对其任山西、浙江两省封疆大吏的业绩作了评述。“风靖浙江潮”指张敕令杀秋瑾事,只管事态和时局并未随着张卸任而平靖。章梫将张称作“词林”中的前辈。
秋瑾
林纾作《五君咏》有云:“张渊静、劳无功、胡瘦堂、温毅夫、李梅庵皆余友也,有诏徵之未至,而诸镇兵已临城矣。渊静称鲠亮,临老卸疆寄,避难隐涞水,食贫甘盐䜴……渊静幸数见,义愤累攘臂……渊静甫治任,烽烟已如沸。”张号“渊静”,林纾称其鲠亮,指张行事刚直。林纾诗中的张,为官时刚直耿介,在时局巨变的环境中浮沉数载难有作为,待卸去职务后,避世隐居。林纾将张塑造成了退出政坛后,甘贫乐道的隐士。
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中录有“弢庵师长西席”拜访张后的一首诗,谓:“蛰庵之外,如劳韧叟、张渊静则隐于涞水,荷锄削迹,世论高之”。弢庵师长西席有《再访渊静、韧叟涞水村落居》云:“自是人间待尽身,菰芦苦处愧遗民。朝朝掉鞅金鳌路,独自冠裾托侍臣。”陈宝琛字“弢庵”,是为此诗作者。“劳韧叟”指劳乃宣。故此诗系陈宝琛在1912年5月10日探望劳、张二人后所作。王逸塘的记录透露,张曾敭和劳乃宣隐居涞水不问世事,是十分为“世论高”的。此中的世论,当指遗民群体论张、劳二人。
王所录是在他看来主要的四句,实在该诗原题为《三月廿四日再访小帆韧叟涞水村落居》,前八句谓:“昨来腊尽顷春残,棋局长安总未安。场圃规成亭亦结,远山如画就君看。两村落还往一牛鸣,炊黍羹蔬数短更。此景从来谁梦到?菊花开后尚论兵!
”显然,陈宝琛认为纷争不已的局势短期内不会沉着。值得把稳的是,王逸塘将原诗中“同是人间待尽身”写作“自是”,“犹自”写为“独自”。原句“同是人间待尽身,菰芦苦处愧遗民”的表述更具张力。在陈看来,他们的人生迟早会走向告结,而他却正奔忙在政局动荡的朝野中。陈曾以“吾起废籍,傅冲主,不幸迈奇变,宁恝然遗吾君,苟全乡里,名遗老自诡耶”?勉励自己不做避世隐居的遗民。但访问了张、劳二人后,陈书“愧遗民”之句,解释二心坎深处对自我的选择产生了些许愧意。
涞水距光绪帝陵墓崇陵很近,张“于奉安时临哭”。在奉安仪式中,张再次巩固了遗民身份。后张搬家天津,这里是清遗民的聚居地,他“益杜门不与人事”。张与缪荃孙交往颇久。张移居天津后,缪荃孙多次前去拜访。据缪1914年10月13日日记:“拜吴仲怿、吴佩伯慈铭、张小帆、章式之、吕镜宇、翁弢夫。”越日“辰刻上津沪,张小帆前辈送行,晚抵济南”。
1917年,《晨钟报》上刊登了一首《津门晤张小帆中丞感赋》,诗云:“苍黄无泪湿金铜,渊静斋头拜寓公。小别三年疑隔世,破空一语问移宫。寒潭雪冱难为浪,高顶云孤不任风。且幸蒲轮迟上道,天留余地待孤忠。”该诗署名“古人”,其作者系林纾,后收入《畏庐诗存》。林纾在媒介中写道:“天子让政……盖非亡国不止,而余诗之凄凉激楚乃甚于三十之时。”故林纾诗集多为对清室的追思之作。通过林纾此诗也可看出,张晚年虽以遗臣自居,但与他人不同的是,张属于少有诗作记述心绪的隐居者。“国家不幸诗家幸”,在清末民初同光体诗繁盛的期间,张并未参与个中。
通过论析上述诗词,可对时人眼中的张曾敭稍有理解:一位从前在官场浮沉,民国建立后避世隐居的清遗民。此外,多见他人咏张的诗词,却少见他唱和之作。总之,张卸任浙抚后的生活较为沉着,多系与僚友的相互拜会。辛亥革命后,张以清室遗民自居。除此之外,几无其他社会活动。这是否会给人一种印象,即张在晚年险些没有任何心迹表露,只是在默默无闻中度完余生?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二烈女”事宜中的作为
1916年的天津城里,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
天津卫,真叫个狗,出了个土混戴富有,拐骗逃难小姐妹,卖到娼门去耐劳。天津卫,真叫个棒,张家烈女有一双,拼去世不做卖身女,吞了洋火儿两命亡。天津卫,真叫个损,出了个推事刘虎臣,颠倒黑白逼去世人,三条人命换赃银。天津卫,真叫个邪,天算夜的冤屈无处申,当年的苏三又转世,洪洞县里没年夜大好人。
据传,上面这首歌谣系天津“秀才善人”刘道原所编,然后教给他接济的托钵人传唱,一时传遍天津街。歌谣中的苏三出自著名京剧《玉春堂》,讲述的是蒙冤妓女苏三终获平反的故事。所谓“又转世”,乃指民国初年轰动津门的“二烈女”事宜。
“二烈女”系南皮偏坡营村落(今属东光县)人,其父张绍廷十几岁在天津红河套扛活,后在一家瓷器店学买卖,被金姓店主招赘为婿。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瓷器店被毁,张绍廷租来一辆黄包车坚持生存。绍廷一日丢了车,车主索赔,其无力偿还。戴富有闻此事后,派与绍廷相识的王宝山前去,假装安慰,乘机提出若将一女出嫁,所得聘礼可偿还债务。绍廷赞许。王宝山做媒将春姑许给戴富有宗子,并立书约。1913年,绍廷病卒,戴妻马氏邀金氏携两女同住,金氏察得戴教二女妓院歌词,后悔不已。马氏又劝金氏再嫁,金氏一怒之下搬出戴宅。事情并未就此平息。戴以悔婚为名将金氏告上法庭,并假造书约,称此前张家已将两女分别许给其二子,法厅便将二女判给了戴富有,戴家欲择期迎亲。金氏称婚期当天将以命争之。二女对金氏说,其父已故,弟尚年幼,若母亲再有不幸,幼弟将无人照看,“是重女罪也”,并称她们二人自有操持。1916年4月18日晚,二女仰药自尽,长女立姑17岁,次女春姑14岁。
刘道原向以不畏权势,敢于直言著称。“二烈女”自尽后,他挺身而出,穿着孝服,手拿招魂幡,在警厅对面的东浮桥头,大骂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引起舆论大哗。张写道:“郡中名流既表章其事,吾张氏同族在津者初未闻,知及是相告语。”即天津士绅进行了诸多吊唁活动后,在津的南皮张氏族人亦获知此事。
该事宜掀起巨大舆论风潮,乃至后来被搬上舞台,多与“二烈女”自尽后社会上为她们举办的一系列吊唁活动有关。当时有诸多文化名人和政客为之书写纪念文本,个中后人解读和剖析较多者,乃王国维所作《张小帆中丞索咏南皮张氏二烈女诗》。这首长诗的产生,是张曾敭积极运作的结果。
王国维在民国文人中地位爱崇,要让其作诗绝非易事。罗振玉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上海识得王国维之才后,二人“即相伴相偕”近30载。1916年12月31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劳丈书来……并徵公题《张氏二烈女诗》,《事略》一纸奉寄。此书来已多时,弟置抽屉中,忘奉达,祈速藻为求。此乃张小帆中丞所托,张女,中丞家人也。拟鸠诸作合刊之也。”“劳丈”指劳乃宣,“张小帆中丞”即张曾敭。因此,张为请王作诗,颇费周折:他先找与自己交好的劳乃宣,将《事略》附上。罗振玉曾称他与劳乃宣两家乃世代之交,故张通过劳乃宣找罗振玉,也是事出有因。罗振玉与王国维交好,罗请王作诗,也就不是十分困难了。1917年1月10日,王复函罗:“张烈女诗是一好题目,唯作长篇则颇费时日,短篇则无从见好,且看诗思如何,或请乙老作之。”上述罗信写于农历尾月初七,王在收到信的第二天便回,可见不雅观堂甚觉“二烈女”事确实是“一个好题目”。信中提及的“乙老”指沈曾植。后罗并未再找沈,王应允作了长诗。
1920年6月7日,吸取信王:“张小帅托存问,渠催张烈女诗已数次,千祈迅寄。”王6月20日复信:“筱帆中丞所索张烈女诗,至前日始就别纸录出,祈转交。此纸恐不可用,尚拟续写。”24日,吸取函王:“顷奉示,及咏烈女诗,拜悉,遂即将诗稿交渊静中丞不误。”罗请王作诗的第一封信写于1916年12月31日,信中提及劳乃宣信“来已多时,弟置抽屉中,忘奉达”,即张请托韶光还要往前推。时隔多年,社会上关于“二烈女”的谈论早已平息,但以其故事原型改编的戏剧在津门再次造成不小轰动。张往事重提,敦促王“二烈女”长诗事,足见他对此事的看重。王诗中“中丞教作烈女歌,五年宿诺嗟蹉跎”一句,便指长诗拖欠太久,有报歉之意。
张托人请王国维为“二烈女”作诗,是他欲将此事留存后世的明证。正是“二烈女”自尽背后所蕴含的道德和气节,让张为之出山。“二烈女”被居津张氏族人获知后多有来吊唁者。此外,“二烈女”殡葬时轰动了全体天津,张也有类似记述:“迨举殡,道察看犹豫者为之流涕。”“二烈女”在张等人的推波助澜下,终成一广受社会关注的公共事宜,并被授予诸多意义。下面要谈论的几则碑文,便是这些意义的详细载体。
张除力请王国维作长诗以兹纪念“二烈女”外,他亦为此事写下了《南皮张氏二烈女碑记》,有谓:“孟子言,舍生取义,庄生亦云,去世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呜呼!
晚晚世衰道丧,其能秉义自守,不以去世生易操者,复几人哉?故吾于两烈女之事尤深悼焉。”即时下“世衰道丧”的社会风气,让张对“二烈女”的德行更感钦佩。“世衰”指代民国以来秩序的突变,而所“丧”之“道”便是传统道德。“二烈女”成为公共事宜后,有人想让“二烈女”魂归故里,但“郡人则欲留此,以励末俗”。张此处的“以励末俗”与开头“世衰道丧”形成呼应。其已将“二烈女”归为重振社会风气的象征,碑文云:
秉彝之好,天赋所均。蒹葭萑苇,乃擢性真。皎皎二贞,受形全归。在艰弥励,执业不回。末俗之乖,彝伦攸。天地易位,人神恫怒。荐绅济济,踧踖罔措。威惕利谄,失落其故步。岂谓弱质,能扶人纪。劲标疾风,澄逾止水。取义成仁,一息千祀。在晋尹氏,唐则二窦。媭媚赴节,永垂世宙。抗志前辉,晚近罕觏。风激懦顽,闻者兴起。保此艰贞,招魂故里。钻石缀辞,以诏无止。
南皮张氏双烈女碑
前已述及,张与僚友交游时,少有笔墨留存,这并不表示他对民国政权没有自己的意见,上述碑文便是贰心中积蓄想法的表露。张在末了写道:“吾独怪混乱之世,利欲斗进,荡弃廉隅,辱人贱行之尤臧获所不屑,为全球靡然,不以为耻。而捐生就义,皭然不滓,乃在委巷之弱女子,岂非天理民彜之仅存?有心世道者,所急欲阐扬以维风教者哉。”在张看来,“利欲斗进”的浊世让“二烈女”不得不以一去世来保全名节。华世奎所撰《南皮张氏双烈女庙碑》中亦有相同的表述:“藐尔诸孤,竟亢吾宗。春冰虎尾,介竹贞松,闷馨宫墙之东。嗟有此二烈兮,乾坤虽否,而吾道不穷。”“乾坤虽否,而吾道不穷”便是张为“二烈女”之事多方奔忙的根结所在。他欲藉“二烈女”推崇的,是包括贞洁不雅观在内的传统道德,即在他看来依旧存续且对世风拥有教养功用的“吾道”。
张碑文写就后,立于南皮城文庙东侧建的“双烈女祠”中,后毁于“文化大革命”,我们现在看到的碑文是《南皮县志》抄录的。徐世昌所撰《南皮张氏双烈女碑》,大概于1922年前后立于天津河北公园(今河北区中山路中山公园)内,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倒。1984年,河北区公民政府为保护文物,将此碑重新竖起,筑亭掩护之。于是,民国期间轰动天津的“二烈女”事宜,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
无疑,“二烈女”在张等人的努力下,成为形塑和承载集体影象的载体,祠堂、公园等公共空间,可为之供应存续的场所。而“二烈女”这一事宜及为之立碑者想表达的内涵,在这些载体和空间中得到再次强化。由“二烈女”事宜所衍生出碑文、长诗等,皆具有象征性,可视作各种形式的“纪念碑”。纪念碑总力争使某人物、某事宜或某制度不朽。“二烈女”以一去世来践行的贞洁不雅观,与张等多方奔忙呼号建立起来的纪念碑所表达的理念,有很大的差异与不同。前者为保名节,避免母亲和幼弟为人所累。而张等在民国肇建、新旧交替之际竖起的诸种纪念碑,则是清遗民欲藉“二烈女”之去世,与现存政权进行一次文化抗争,进而唤起他们所认可的道德和文化。质言之,在一系列纪念碑中,作为事宜本事儿的“二烈女”本体逐渐失落语。这彷佛是近代中国女性节烈行为成为"大众年夜众事宜后,无法避免的文化征象。
综上所述,“二烈女”之以是能在津门引起广泛关注,有两方面缘故原由。其一,其南皮张氏的身份,张氏家族在此地有巨大势力。其二,张曾敭等清遗民的推动。烈女之事涌现后,张曾敭等忽觉前朝遗风仍在,加上“二烈女”系张氏族人,故乘势摇旗叫嚣。总之,张在古稀之年为“二烈女“奔忙,足见他对此事的关注。在此过程中,他感想熏染到了一种融入个中的身份认同,即便这种认同的范围并不广阔。通过该事宜,张一方面是让其族人业绩永昭后世,但更多是借此表达其对传统道德的认同与坚持。
身后的评说
1921年2月14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奉告了张的去世讯:“新正二日,筱帆中丞委化,老成凋落,可为哀悼。”罗振玉之孙罗继祖在该信下按语称:“公曾告我,张曾敭中丞之殁,乃新正二日,家人令其孙女陪其玩,有顷,女孙忽拜别。家人问之,说爷爷睡着了,即是无疾而终。”下文拟综合剖析墓志铭、挽辞、史籍等多种文本,以不雅观察张曾敭去世之后,人们藉纪念张所透露的繁芜内涵。
张去世前写了几行遗言,颇能反应他的一些心绪:“丧,与易宁戚,专事浮文,昔贤所戒。况我为亡国大臣,尤[更]应贬损,除以朝服敛外,殡葬统统比照庶人,不得沿用旧式,不得发讣开吊,尤其不准上报。如或不遵,即是不孝。”张的遗言寄托着其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在希望丧事从简、恪守儒家义理的同时,更因其为亡国之臣,哀求穿着清朝官服入葬,便是他对清室忠心的明显表露,也是对其遗民身份的末了一次展示。另,遗言强调不准上报,似让其子张愿等人勿上奏宣统帝。而遗民去世后上陈溥仪的紧张目的之一,是请谥号。
谥号是官员去世后生平功过的评价,多由朝廷赐予,然清遗民的谥号与曩昔多有不同。溥仪写道:“为了去世后一个谥号,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里跑,或者从迢遥的地方寄奏折来。”溥仪此语自是身在深宫,不知谥号在遗民心中的地位。历朝遗民多以不仕二姓的忠德践行其志,而在宣统帝尚居紫禁城,小朝廷仍存的条件下,在一些清室遗臣眼中,若能得到谥号,便是对其身份的认可。此外,若他们能获谥号,便解释朝廷仍在,清室未亡,有一丝抱残守缺的意味。
闻得张去世的后,劳乃宣给张宗子张愿写信:“我朝旧臣可请谥号于皇室,是否入告?予谥何字?”后劳再次致信张愿:“一是尊大人无疾而终,可称全福,悲之,亦羡之。治命诸不举动,自应屈服。惟弟前函所陈请谥号于我皇室一节,不识有无遗训制止?如无不许之命,似以议请为宣,愚见如此,望再与同道诸先辈商之。”劳让张愿为张曾敭请谥号,意在使张曾敭留名后世。比较劳乃宣,王照的建议更加详细且细化。其信云:
目前要事有三:一曰史传,二曰易名,三曰入祠。今非奉旨宣付史馆时期,宜先作祖传,秉笔之人不在文名之高下,不在交情之厚薄,必择脾气心术与老人契者为之,如蒋艺圃者可也。祖传推敲至当,缮为二册。一册径送清史馆,一册即函托赵次山或表玨生奏呈宣统帝,而谥可定矣。史馆有删而无改,而谥必括生平之行谊。苟祖传确当,则史传易名,二者皆无误矣。春秋葬称谥礼云:“日月有时,将葬矣,请以是易其名者。”此在葬以前可详慎为之,勿以匆遽,致有不当。谥定而后题柩,而后成主,停柩义园之日,家中暂奉非正式之木主可耳。先哲祠可入名臣,可入忠义,然村落夫公定,无须领徐总统之诺,世俗之态可厌,必须以此意达之。值年同乡,且此事亦不忋旧例,殁后三十年始入祠,以恩怨两无,方显公道也。光宣以来,诸公入祠之速,人情薄而急于市恩,不敷增重,故此事无须汲汲。老人于照有师道,用敢竭诚参末议,如此是否有当,祈采择之。
劳乃宣与王照二人希望张愿等人积极运作,以为其父争得声名。但张曾敭并未得到谥号。陈宝琛在张曾敭的墓志铭中写道:“遗疏入,上震悼,手书‘清风亮节’四字,并赐白金五百治丧。”据陈记述,张之去世彷佛得到宣统帝的高度关注和惋惜,事实上并非如此。罗振玉和王国维的书信对此事有所表露。3月21日,吸取信王:“弟本欲入都,由于小帅处请弢庵太傅题主,命弟襄题,此事毕,乃能启行。俟盛氏乞恩事有眉目(乃乞赏匾额,非谥事。谥事又经打消,此刻但有稍缓,其详容面告。江苏教诲会发电,缓步文内务府,此电已登各报,想已知之。小帅之谥,亦因此不成,弢老固请,仅赏清风亮节二匾)。”可见,只管有溥仪视为“灵魂”的陈宝琛为张力请谥号,却并未如愿。另据张瑛齐所撰《祖叔祖小帆中丞公传》:“事闻,钦赐‘清风亮节’四字,以褒荣之。”因此,张未获谥号,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墓志铭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撰者根据去世者经历进行的再创造,其功用看似仅记录逝者平生,实则更为宏阔。陈宝琛为张撰写的墓志铭,紧张呈现了他的家族背景、出生及在特定时间内的为宦经历。然墓志铭中所呈现的事实本身只是大略地被利用,从而实现言辞的“自我表达”,即墓志铭本身实则“包含了一种潜能”。陈通过墓志铭的写作,欲为张勾勒出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像,进而达成其心中对张的隐喻式理解。陈所撰墓志铭,将张塑造为一个浮沉官场、能力出众的官员。如提及秋瑾案时写道:“公檄捕鞫实置诸法,彼党先恐专横,不效则慑,不复敢谋浙,而当事人中言,调公江苏,旋复移山西。公乃连疏乞退,三上始得请。”事实上,张黯然离开浙江,个华夏因颇为繁芜。陈所谓“当事人中言”,似有张蒙冤的痕迹,这或许更靠近张彼时的心境,却与事实相去甚远。后张去意已决,不愿为官,连续上奏请辞,清廷准其开缺。陈所言张乞退时“三上始得请”,欲为其塑造清廷惜其才而挽留的环境。如此,刻在张的墓碑之上的,是一个效忠职守的干练能臣。
张去世后,劳乃宣撰写了《张渊静总宪挽辞》。劳首先追忆了他与张相识相知的情意,及张在官场跌宕浮沉,直至黯然离场的落寞。他写道:“南皮御史多夙缘,登科同岁生同年。我绾铜墨宰君土,君搏节钺临吾天。臭味交孚畹兰契,行藏互砺严松坚。皖江畴著□奇变,朴缄远在之江岸。默尔诛锄堂赛儿,钱塘潮势安然奠。新纶移指西山西,辞荣寂寞人海栖。”张卸任浙抚后心中多有不愿,“辞荣寂寞人海栖”一句,盖是对张彼时心境的解读。接着,劳忆及他们二人在涞水隐居时不问世事,互为知音的岁月:“我膺鹤书诣丹阙,铜驼陌上相提携。铜驼一旦卧荆棘,釜山麓下偕扶犁。禾麻南亩连阡陌,鸡黍东轩忘主客。膝下琳琅研简编,闺中参昂论刀尺。鼎湖携手泣遗吊,飞飞劳燕乍西东。”清室覆亡后,张、劳二人以遗臣自居,“东轩”用典陶渊明诗“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忘主客”用典清初诗僧成鹫诗“相逢忘主客,何处是归来”。劳连续写道:
君吟丁字沽头月,我咏田横岛畔风。寞渊日起思波遍,君掌鸟台我司宪。转眼华胥一梦空,遥天清泪挥如霰。江山举目又三春,谁是神州戮刀人。海滨腾兴新亭恸,尚复何心恋软尘。传来噩耗沧溟远,初闻涕泗衣裳满。俯仰□区转羡君,一瞑不视天真返。与君交谊今所稀,远希元白无差池。去世生契阔有同调,允宜执手长因依。岂料乐天三度别,寝门先竟哭微之。题诗且作平生语,为问墓穴知不知?
劳乃宣
1913年11月,劳乃宣移居青岛,“君吟丁字沽头月”一句便是他和张分隔两地、遥寄思恋的景况写照。在劳乃宣笔下,张无疑是一位真正的隐士。劳所写挽辞,并不重在经历之铺陈,而在于这些经历触动了他若何的感怀。此时距他和张避居涞水已过去了十年,如今知音已逝,他也去日无多了。1921年7月21日,劳以微疾卒于青岛寓所。这两位“登科同岁生同年”的心腹之交,终相会道山。遗民词多寄寓其政治和文化理念,以建构和巩固他们的遗民身份,保存文化影象。劳所撰挽词亦有此种功用。他将张归入历代遗民群体,便是对其晚年纪月至为崇高的评价。8月3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韧丈已作古,在逝者诚无所憾,然今年张小帅、沈封老及韧丈,逝者已三人,我辈正自尴尬耳。”“张小帅”即张曾敭。遗民不是一种职业,只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才会涌现的称号,且不可世袭。看到身边的遗民不断逝去,罗等在世者或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前已叙及,张去世后,王照建议张愿将张曾敭业绩整理后送入清史馆,以强化张的声名。总体来看,《清史稿》对张的书写环绕其仕宦经历展开。传文首先讲述张出身正途及入翰林院的经历,接着以张处理的几次政务为例展现其政绩。紧张有永顺府任内募勇剿匪、福建盐法道时严守规章、广西布政使期间张罗庚子赔款、山西巡抚任内清剿枭匪和浙江巡抚任内处理盐枭吴家正。其次陈述张在沈家本实行法律改革时上奏反对,认为“治乱国用重典,犹惧不胜,骤改从轻,何以为治?此他省或可行,而浙独难行者也”。传文提及他与秋瑾案的关系时写道:“秋瑾者,浙江女生言革命者也,留学日本,归为绍兴大通学校西席,阴谋乱。曾敭遣兵至校捕之,得其左验,论重辟,党人大哗。调抚江苏,俄调山西,托病归。”若据《清史稿》,张无疑是一位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且仕宦经历非常丰富的官员。
另,《清史稿》将周馥、杨士骧、陆元鼎、张曾敭、冯煦五人放在一起阐述,表明他们具有类似的特性。在传文末了写道:“光绪初,督抚权重,及其末年,中心集权,复多设法令以管束之,吏治不可言矣。锡良强直负重,安内攘外,颇有建树。馥谙练,士骧通敏,元鼎办交涉,曾敭论法律,并能持正,煦善治赈,与荒政相终始……锡良初疏谏集权,枢廷转相胁迫。及事变起,大势所趋,皆一如所言,世尤服其先见云。”作者强调锡良等五人的治绩及性情,而为官多年的张,竟以“论法律,并能持正”被提及。换言之,因张辗转各地为官时并无过多政绩可供颂扬,却在沈家本实行法律改革时发出非凡议论,被《清史稿》撰写者视为其稍显独特,且值得记叙的业绩。撰者如此陈述张的生平,亦是认同其作为的表现。总之,陈宝琛、劳乃宣等人通过墓志铭、挽辞等文本,巩固了张的遗民身份。而其业绩终极被写入《清史稿》,使张的遗民身份得以固化和定型。
结语
作为因秋瑾案而开缺的封疆大吏,张曾敭卸任后的复出传闻彰显著时期正处于鼎革之际,革命亦以摧枯拉朽之势动摇着清廷统治的根基。辛亥革命后,张选择做一个阔别政事的遗臣。他晚年表现较为激烈的行为,是动用个人关系网络让王国维为“二烈女”作诗,自己也留下了纪念文本。少见遗民诗词留存的张,在象征传统节烈行为的事宜中奔忙呼号,践行其所认同的道德与文化。在此过程中,他更多是欲为所坚守的道德文化作一次轻声叫嚣。可以说,张虽身处风起云涌的清末民初,但也仅是一个影响甚微、阔别政事的清室遗臣,一个平淡生活的普通个体。张去世后,生前同寅与后人为塑造其身后声名多方努力,诉诸多种纪念文本。无论这些文本所述内容客不雅观与否,但其所欲呈现的张,是浮沉官场多年、坚守传统道德的旧臣。
论者认为,清遗民虽对民国政治持批驳态度,但有些人亦在赈灾救援等社会事务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以是对该群体的评价不应以大略的“遗老遗少”一语所概括。与罗振玉等人不同的是,张曾敭没有参与清遗民组织的社会事务,亦未卷入到图谋复辟等活动中。他一以贯之地坚持作一个普通的清遗民,期间少有显著的思想变革。质言之,在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的竞赛中,张力争守住自己心中的那方避难所。盖在鱼龙殽杂的清遗民群体中,他仅是默默无闻效忠清室的个体生命,也可算作近代中国由“天下”到“国家”的转向中,传统思想顽强留存的例证。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10期,作者许飞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