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伪存真与去粗求精——以武威碑志中的伪刻、翻刻与精拓为例
摘 要:出土碑志文献是近年来中古史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工具,一定程度上推动着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有效利用这类文献的条件便是要辨其真伪,才能担保研究的准确性。本文即以我们在整理武威碑志过程中碰着的伪刻、翻刻等情形进行举例剖析,结合古人有关碑拓辨伪的研究成果,谈谈体会,以期引起干系研究者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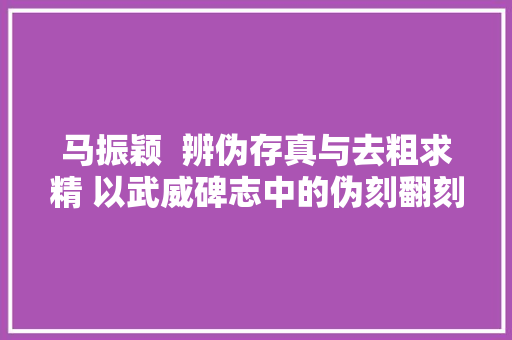
关键词:墓志;伪刻;翻刻;北魏
# 阅读勾引
一、《北魏晋德墓志》凿改自《北魏王昌墓志》
二、《北魏源模墓志》的两种翻刻本
三、《隋段模墓志》与《唐孟运墓志》的新旧拓本举例
四、余论
自民国至今,中古期间的碑志层出不穷,特殊是近三十年来,随着考古发掘事情的进展及城市根本举动步伐的推进加之部分盗掘,据梶山智史[1]、气贺泽保规[2]等学者的统计,魏晋隋唐墓志的出土数量,已逾万方。当然还有一定数量的出土墓志,目前尚未公布。在利用这部分碑志材料进行研究的一个很主要的条件,便是首先要对这些碑志的真伪进行鉴别,弄清其来源及收藏状况,只有在确定其为真品的情形下,再对其进行研究,方能担保研究的准确性而不至于被误导。
碑志的伪刻、翻刻问题,历来是研治金石学的专家学者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特殊是清末民国初年,由于尊碑卑帖风气的盛行,石本收藏云起,翻刻作伪大量涌现。当时翻刻伪刻品种之多,质量之精,在中国石刻史上可谓空前绝后[3]。清末以来有些金石学书本,如黄立猷《石刻名汇》、陆增祥《八琼室金石祛伪》、方若、王壮弘《弥补校碑随笔(修订本)》、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马子云《石本鉴定浅说》、仲威《中国碑拓鉴别图典》等诸书对伪刻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与剖断。此外,近年来不少学者对魏晋隋唐期间的伪志加以仔细甄别,也呈现出一定成果,例如江岚《历代碑刻辨伪研究综述》[4]、赵海丽《北朝墓志文献研究》[5]、马立军《北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与〈元理墓志〉辨伪——兼谈北朝墓志著录中的伪刻问题》[6]、王昕《河南新见陶潜墓志辨伪》[7]、梁春胜《魏晋南北朝石刻辨伪十例》[8]、何俊芳《新见五方伪刻北魏墓志辨释》[9]、刘琴丽《三方北朝墓志辨伪——再论北朝墓志著录中的伪刻问题》[10]等。据不完备统计,目前已创造的魏晋南北朝期间伪志已近二百方。刘灿辉在《洛阳北魏墓志的作伪、考辨与鉴别》中提到北魏伪刻墓志的不良影响,紧张表示在三方面:导致学者中招,引发学术混乱;收藏者不断上当,丢失精力钱财;志文编造内容被引用转述,扭曲历史原形[11]。而针对当下金石学的这种状况,更哀求我们要具备一定的鉴别真假的能力,正如蔡先金等所说:“当下我们对新出土的墓志一定要采纳谨严态度,用科学方法剖析辨别其真伪,然后方可公布于众。只有如此,古代墓志才能真正彰显其历史代价、科学代价、艺术代价,而避免赝品鱼目混珠,稠浊视听。”[12]
我们在搜集整理汉唐武威碑志的干系材料时,也创造有伪刻、翻刻及新旧拓天职歧的情形,对付这部分碑刻,采纳谨慎态度进行鉴别,伪刻未收,翻刻予以解释,新旧拓本择其佳者进行录文。本文即以我们在整理武威碑志过程中碰着的上述情形进行举例剖析,结合古人有关碑拓辨伪的研究,谈谈研究体会。
一、《北魏晋德墓志》凿改自《北魏王昌墓志》
《北魏晋德墓志》坊间流传有拓片,据云为高平博物馆所藏,正方形,边长30厘米,砖志,首题“魏故威远将军凉州长史晋君墓志铭”(图1),现已出版的金石学著作中未见刊布。
图1 北魏晋德墓志(伪刻拓片)
《北魏王昌墓志》,1929年河南洛阳城东北太仓村落出土。志石为正方形,边长45厘米。志文共18行,满行18字,正书。洛阳市文物事情队藏有拓本(图2)。
图2 北魏王昌墓志(原石拓片)
有浩瀚书本著录该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一九、《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册、《北魏墓志百种》《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4册等书,皆有图版著录;《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全北魏西魏东魏文补遗》等书有录文著录。特殊是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魏威远将军凉州长史长乐侯王昌墓志。熙平元年三月十七日。民国十八年农历六月营庄村落人于太仓村落地内掘得。”[13]更为其真实性增长了依据。
为明辨真伪,现参照拓片,将二志全文照录于下:
魏故威远将军凉州长史晋君墓志铭
君讳德,字金贵,上党高平县长平村落夫也。君幼节居丧,孝闵宗国,童幽袭爵,誉播才训。年十有三,起身中散。抽贤之举,歼此名德。春秋卅七,延昌四年十仲春廿六日卒于凉州。熙平元年三月十七日窆于长平北芒之山。
——《北魏晋德墓志》
魏故威远将军凉州长史长乐侯王君墓志铭
君讳昌,字天兴,太原祁县崇高乡吉千里人也。魏故使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幽州刺史汝南庄公之孙,散骑常侍、中书监、行家尚书、使持节、镇东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长乐定公之子。玉根肇于子晋,金枚光于太原,弈叶冠华,领袖当世。君禀日月之辉,含川岳之曜。孝敬之道,雍穆于闺庭;礼让之德,显英于邦国。敖游仁义之林,栖迟文藻之泽。远气冷落,叔度无以比其量;雅怀沉毅,文饶未足[夺]齐操。君幼节居丧,孝闵宗国,童齿袭爵,誉播才训。年十有三,起身中散,抽贤之举,转员外散骑侍郎,寻加襄威将军。冠缨东省,蹈礼斯处,遂除威远将军、凉州长史。届时未旬,歼此名德,春秋卅七,延昌四年十仲春廿六日卒于凉州。熙平元年三月十七日窆于洛阳北芒之山。乃作铭曰:
崑丘英绪,丹陵妙枝。唯君诞载,缀萼云池。桂落秋月,兰雕上日。贞躯难往,刊铭芳质。
——《北魏王昌墓志》
通过比对《北魏晋德墓志》(以下简称《晋志》)与《北魏王昌墓志》(以下简称《王志》)的原文录文、拓片图版等干系信息,我们创造,前者显然是仿自后者,且作伪的痕迹非常明显,紧张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该志的出土韶光、地点不明确。《晋志》不见有出土时地的记载,据云为高平博物馆收藏,但是根据我们查找《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高平市卷》,该书上编现存石刻部分,只收录一方北魏墓志,为《魏故襄威将军积射将军郭君(翻)志铭》,韶光为北魏正光二年(521)。[14]咨询干系事情职员,也称未见此志。因此其真实性不免令人疑惑。而王昌墓志的出土韶光、地点明确,收藏情形也著录清楚。
第二,该志的首题系剜改自《王志》。《晋志》首题“魏故威远将军凉州长史晋君墓志铭”;《王志》首题“魏故威远将军凉州长史长乐侯王君墓志铭”。与《王志》比较,前者删去“长乐侯”三字,又将《王志》正文中“玉根肇于子晋”中的“晋”字挪到此处,移花接木,形成新的首题。类似的情形还有多处。
第三,该志的正文内容与《王志》多有雷同。《晋志》正笔墨数较少,且未记述志主的家族世系,颇有疑点,而在描述志主诞辰常平常,也只是寥寥数语,语句不甚连贯,有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觉得。又《晋志》中除了志主的名姓及籍贯、葬地,其他的如“幼节居丧,孝闵宗国,童幽袭爵,誉播才训。年十有三,起身中散。抽贤之举,歼此名德”“延昌四年十仲春廿六日卒于凉州”等字句,完备照搬自《王志》。《晋志》称志主“字金贵”,“金”字采自《王志》的第6行倒数第5字,“贵”字采自《王志》第2行倒数第7字。
第四,该志志文未载晋德的详细仕宦情形。除了首题中提到晋德为“威远将军、凉州长史”外,志文中仅载“年十有三,起身中散”,然后又记“卒于凉州”,期间对付中散之后的任官情形,《晋志》却无丝毫记载,显然这是不符合当时的墓志书写习气的,而《王志》却清晰记载王昌在任中散之后,又历任员外散骑侍郎、襄威将军、威远将军、凉州长史等职,记载其仕宦履历详细。
第五,该志的字体仿自《王志》,却又略显粗糙。“君讳”“童”“三月十七”等字体,与《王志》无二。而“墓志铭”的“墓”字,《王志》中间部分为“曰”,《晋志》刻作“田”;“童齿袭爵”,《晋志》误刻作“童幽袭爵”,显然是仿刻时涌现的失落误,也成为辨伪的一个标志。《王志》无界格线,而《晋志》刻有界格线,类似田字格,且界格线多从笔墨正中穿过,这在北魏墓志中也是不多见的。很可能是作伪者为了刻写方便而刻画。
第六,该志的籍贯、葬地等地理信息系假造。《晋志》载志主为“上党高平县长平村落夫”,查《魏书·地形志》上党郡辖五县“屯留、宗子、壶关、寄氏、乐阳”[15],无高平县。山西的高平县,乃北魏永安中(528-529)中改长平县而置。志主葬于熙平元年,此时山西境内应无高平县。《晋志》载“窆于长平北芒之山”,北邙,即北邙山,又称邙山,在今河南洛阳市北。东汉及魏王侯公卿多葬于此。北魏期间长平境内不可能会有北邙山,明显系作伪者假造,而其不明地理知识,难免令人啼笑皆非。不过为我们辨伪供应了帮助。《晋志》所载的两处地理信息,显然与地理知识相悖,足以证伪。
第七,该志短缺铭词部分。北魏期间的墓志,大多首题、正文、铭词三部分完全,但是《晋志》不仅内容上严重不敷,未能反响作者的平生业绩,而且志文末了也没有铭词部分,令人十分费解。或许这是造伪者故意省略,但这正好暴露了这方墓志为伪志的又一疑点。
综上,我们认为《北魏晋德墓志》应该是仿照《北魏王昌墓志》而刻的一方伪志,并且作伪者缺少一定的历史、地理及书法知识,甚至在作伪过程中显现出诸多硬伤,客不雅观上为我们辨别其为伪志创造了条件。
二、《北魏源模墓志》的两种翻刻本
马子云在《石本鉴定浅说》中提到,“碑拓的赝品有两种:一种是翻刻,一是假造。翻刻,是因原石真本稀少而宝贵,故翻刻后拓出拓本,再做成旧式以欺人。假造,是无原石拓本,而凭空根据某碑志或帖上某人书法,再摘一段古人文章或诗词,二者结合刻成以欺人。”[16]赵超的《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增订本)》也称:“所谓翻刻(或重刻),是指原来的石刻现在仍旧存在,而后人依据石刻拓本仿照原样重新刻一件新的碑石,这类石刻常常会与原来的古代石刻混同。”[17]对翻刻本的鉴别,在没有见到原石的条件下,须要对拓本所表现出的诸多细节进行剖析解读。我们在搜集武威干系碑志时就碰着过翻刻的情形,今举《北魏源模墓志》为例。
《北魏源模墓志》,永安元年(528)十一月八日葬。据云2005年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出土,石旋归洛阳李氏。志文共20行,满行21字,正书。关于这方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以下简称《秦晋豫》)第1册第32页[18]、《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以下简称《七朝》)编号29[19]及宫万瑜《邙洛近年出土冯聿、源模、张懋三方北魏墓志略考》[20](以下简称宫文)都有图版(图3、图4、图5)著录,但图版均不完备相同,此外殷宪《<源模墓志>书迹以及志文所及北魏源氏的几个干系问题》[21](以下简称殷文)也有干系研究。
图3《七朝》所收源模墓志拓片
图4 宫文所收《源模墓志》拓片
图5《秦晋豫》所收墓志拓片
关于此志的出土韶光,目前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秦晋豫》所记“2005年春,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出土”[22];一种为殷文所称“2002年得拓,石出洛阳”[23]。如果按照殷宪所说,则《源模墓志》的出土韶光或在2002年及以前。此志的收藏地点,紧张有三种说法,一种是《秦晋豫》所说“旋归洛阳李氏”;殷文所说“藏于私氏”;宫文所说“现藏千唐志斋博物馆”。但查千唐志斋博物馆藏石目录及讯问干系事情职员,可以确定此志未被该馆收藏,可知志石仍藏于私人手中,至于是否为洛阳李氏,目前不得而知。
为便于更直不雅观地理解这三种拓本的差异,现将诸书所收录的拓本展示如下:
这三方墓志拓片的尺寸,各不相同。《七朝》记:高56厘米、宽51厘米;《秦晋豫》记:高50.5厘米、宽51厘米;宫文记:高55厘米、宽52厘米。而对照墓志拓片,很明显可以看出宫文所刊拓片,在旁边界格线以外还有空余,且宽度的尺寸明显不同于其余两志,此为疑点之一。收藏地点,宫文称现藏千唐志斋博物馆,而此说有误,拓片来源不明,此为疑点之二。宫文所刊拓片,石花不自然,有明显点凿痕迹,且全体石面都有分布,此为疑点之三。宫文所刊拓片,界格线不清晰,仅有直线无横线,此为疑点之四。宫文所刊拓片,整体字迹懦弱,形神有失落,此为疑点之五。至于详细字形上的细微差别,详见后文。
《七朝》与《秦晋豫》所收拓片,乍一看十分相似,若同出一石,如果不仔细辨别,很难创造二者的差异。先说二者的相似之处:二志都有横竖界格线,且比较清晰;二志字体相同,有范例的魏碑体字意;二志刊布的韶光相同,《七朝》与《秦晋豫》均出版于2012年,据志石的出土韶光当不会太久。
当然,二者也有一些细微差别:1.石花不同。《秦晋豫》拓片左起第2行上数第1、2字间,有竖形石花;《七朝》拓本无。《七朝》拓片左起第2行,与左起第4行、左起第8行的末了一字左下角处,均有石花,《秦晋豫》拓本无。2.尺寸不同。《七朝》载拓片高56厘米,《秦晋豫》称拓片高50.5厘米,二者相差5.5厘米,差距如此之大,恐非丈量失落误。3.边角不同。《七朝》拓片左上角、右上角的残损程度与《秦晋豫》不同。4.部分字迹不同。如《秦晋豫》拓片右起第1行“魏”字,左下角有“乚”,《七朝》拓本无;《七朝》拓片右起第1行“铭”字左半“金”部第一横不连,《秦晋豫》此处微连。为更直不雅观理解三种拓本详细字形上的细微差别,特绘制下表(表1)。
经由我们剖析后认为,《七朝》所收《源模墓志》拓片为真,别的二者为翻刻,宫文所刊拓片,翻刻痕迹明显,易辨别;《秦晋豫》所收,也有细微的翻刻痕迹,仔细区分,还是可以鉴别出的。
三、《隋段模墓志》与《唐孟运墓志》的新旧拓本举例
仲威根据石本的拓制年代将石本分为唐拓、宋拓、元拓、明拓、清拓、乾嘉拓、嘉道拓、清末拓、民国拓、旧拓、近拓。他认为清末民初的拓本应该也归入“旧拓”的范畴,民国往后的拓本可称为“稍旧拓”,20世纪80年代往后的拓本则成为“近拓”。2000年往后的拓本成为“新拓”[24]。我们在整理武威干系碑志时,也会碰着拓制年代不同的拓片,除了个别的宋拓以外,紧张是民国拓本和近拓本的差异。下面要举到的例子便是如此。
《隋段模墓志》,大业六年(610)十仲春五日葬,1923年河南洛阳出土,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志盖篆题“段君墓志”,今佚。志文共21行,满行22字,正书。《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以下简称《北图》)第10册、《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以下简称《洛阳卷》)第1册、《隋代墓志铭汇考》第4册、《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菁华》(以下简称《辽博》)等书有图版著录。《芒洛冢墓遗文四编》《满洲金石志别录》《全隋文补遗》等有录文著录。《石刻题跋索引(增订本)》《六朝墓志检要(修订本)》《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等也有著录。
据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隋仪[同]大将军府参军事段模墓志,大业六年十仲春五日。民国十二年,洛阳城北凤凰台南数里处出土。”[25]可知该志的出土韶光为1923年,此后不久被武进陶兰泉收藏,1936年之前流落沈阳[26],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关于该志,目前可以见到的拓片紧张有三种:1.民国初拓本。如《北图》藏段模墓志拓片(图6),便是陶兰泉收藏时所拓,韶光为上世纪20年代旁边。《集释》与《洛阳卷》所收,与《北图》所收拓片无二,拓制韶光当相距不久。2.哈佛藏民国拓本(图7)。此拓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拓制年代为民国期间,但从拓片来看,此时志石右上角短缺一部分,因此该拓片的拓制韶光当晚于《北图》藏拓。3.辽宁省博近拓(图8)。《辽博》所藏段模墓志的拓制韶光,书中没有提及。其时间我们推测该当是建国后所拓,由于《辽博》所刊拓片,不仅右上角缺角,而且志石的上部中间位置及下部旁边处,共有三处类似搬运中造成的石面破损的痕迹,特殊是上部的痕迹,已经造成原石志文的损伤,因此其拓片的制作韶光明显靠后。为便于不雅观察,我们将《隋段模墓志》的这三种拓片展示于后。
图6 《北图》藏拓
图7 哈佛藏拓
图8 《辽博》藏拓
《唐孟运墓志》,仪凤二年(677)正月九日葬。河南洛阳出土,现藏洛阳古代艺术馆。志盖顶面楷书“唐故孟府君之墓志铭”。志文共19行,满行19字,正书。《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16册、《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以下简称《唐附考》)第9册、《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6册有图版著录。《唐代墓志汇编》仪凤003、《全唐文新编》第21册、《全唐文补遗》第4辑等有录文著录。
关于该志,目前可以见到的拓片紧张有两种:1.北图拓本(图9)。《北图》称此本系原北平图书馆旧藏。当为民国期间的拓本。《洛阳卷》所收与《北图》同,当为同一幅拓片。2.中研院拓本(图10)。《唐附考》所刊的为中研院史语所藏拓,拓制韶光该当也是民国期间。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收藏有该志的拓片,[27]目前未见图版刊布。由于该志在民国期间出土时即已断裂为两块,因此目前所能见到的这方墓志的拓片,都会看到有一条很明显的缝隙。
图9《北图》藏拓
图10《唐附考》藏拓
但是,比拟上述这两种拓片,可以直不雅观看出二者的显著差异——中研院藏拓左半断裂处的拓制水平要高于北图拓本,而北图藏拓断裂处这一竖行及阁下竖行的前半部分都未拓出笔墨。此外,中研院拓本的石花痕迹明显少于北图拓本。按理说二者同为民国期间拓本,应该差别不大,但是很明显,这是由于不同拓工的拓印水平所导致的。当然,北图藏拓也有一定优点,比如志石的四周拓的比较清晰,特殊是最上面一行笔墨与最下面一行笔墨,根据北图拓片我们可以比较轻松地释读。二者各有优缺陷,因此在整理录文时,还需相互参照进行释读。
四、余论
前面列举了我们在整理武威碑志过程中碰着的伪志、翻刻、新旧拓本的干系情形,为更准确地著录整理干系碑志供应借鉴。关于伪志、翻刻的形成缘故原由,不少金石学者都表达了自己的不雅观点,在此结合切身体会,谈一点意见。
伪志《北魏晋德墓志》的作伪者采纳翻刻加改动的作法,用原出土于洛阳的《北魏王昌墓志》拓片作为底本,按照它的样式重刻一石,除了志主的姓名、籍贯等,其他内容均照搬原石。至于志主的姓名、籍贯,则是选取原石中的字进行调换,乃碑刻作伪中的移花接木之术。这方伪志的形成缘故原由,我们推测紧张有以下几点:一、因王昌墓志原石已佚,仅存拓片,作伪者正是捉住这一点,制作伪志,鱼目混珠。二、山西出土的北朝期间的墓志,有以青砖为质地者,作伪者所选取的刻石材料正是砖质,以表示地域特色。三、凉州是河西走廊的重镇,出土的有关凉州的墓志历来为研究历史者特殊是研究西北史地者所重视,而志主的“凉州长史”身份更易被研究者所关注。四、作伪者谎称该志为公立博物馆所藏,市情难得一见,给其披上一层华美的外衣,极易误导初入石本领域的干系职员。五、北朝墓志价格每每高于其他期间的墓志,作伪者能获取更大利润。
《北魏源模墓志》的翻刻品,除了我们上文所举的例子,可能还有其他例证,据云有将该墓志翻刻于两块石头上者,笔墨只字未改,但因未见拓片,暂不作谈论。这方墓志的翻刻品形成的最紧张缘故原由便是原石藏于私人手中,市情上仅有极少数拓本流利,导致物以稀为贵,作伪者依据原石拓片进行仿造,以牟取一定利润。当然,源氏家族为北朝期间西平大族,涌现不少在历史上有过记载的人物,如源模之兄《北魏源延伯墓志》的刊布,为研究北魏源氏家族供应了宝贵的文献材料。源模墓志对付补充北魏源氏家族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代价,如宫万瑜、殷宪等均撰文研究,增长了学界对该志的关注程度。此外,北朝期间的少数民族墓志历来是伪志、翻刻的重灾区,在以往的碑志类图集如《石刻名汇》《弥补校碑随笔(修订本)》《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石本鉴定》等中多有记载,如《弥补校碑随笔(修订本)》所记载的北魏天安丙午八月《处士源嘉墓志》便是一方北朝源氏家族的伪志,[28]且被多书著录。
经考古发掘或公开刊布的魏晋隋唐墓志,绝大多数为真品,极少有伪志。而民间飘泊的来源不明的墓志,可能存在部分伪志,在利用时要加以辨别。对出土碑志进行录文时,在无法得见原石,而有多书著录同一碑志的情形下,要选取精拓进行录文。一样平常来讲,年代越靠前的拓片,保存的内容更为详细,对付新近出土的碑志,在拓片的选择上要比较拓工水平高低。当然,旧拓与新拓比较勘,不同书中的拓片相对照,对付担保录文的准确性同样具有一定帮助,而这正为我们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一定根本。
参考注释
[1][日]梶山智史編《北朝隋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東京:汲古書院,2013年。
[2][日]氣賀澤保規編《新編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東京:汲古書院,2017年。
[3]仲威《石本鉴定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4] 江岚《历代碑刻辨伪研究综述》,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5]赵海丽《北朝墓志文献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6]马立军《北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与〈元理墓志〉辨伪——兼谈北朝墓志著录中的伪刻问题》,《江汉考古》2010年第2期,第92-94页。
[7]王昕《河南新见陶潜墓志辨伪》,《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第70-75页。
[8]梁春胜《魏晋南北朝石刻辨伪十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笔墨研究中央网站,2012年11月22日,原文网址:http://www.fdgwz.org.cn/Web/Show/1964。
[9]何俊芳《新见五方伪刻北魏墓志辨释》,《许昌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7-11页。
[10]刘琴丽《三方北朝墓志辨伪——再论北朝墓志著录中的伪刻问题》,《文献》2019年第2期,第14-24页。
[11]刘灿辉《洛阳北魏墓志的作伪、考辨与鉴别》,《中国书法》2017年第20期,第56-64页。
[12]蔡先金、赵海丽《<显祖嫔侯骨氏墓志铭>辨伪》,《中国书法》2007年第4期,第98-101页。
[13]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洛阳:大华书报社,1941年,第21页。
[14]刘泽民总主编,常书铭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高平市卷》,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5页。
[15][北齐]魏收撰《魏书》卷160上《地形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7页。
[16]马子云《石本鉴定浅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第90页。
[17]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729页。
[18]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19]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9页。
[20]宫万瑜《邙洛近年出土冯聿、源模、张懋三方北魏墓志略考》,《中原文物》2012年第5期,第74-78页。
[21]殷宪《<源模墓志>书迹以及志文所及北魏源氏的几个干系问题》,收入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第七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54-267页;又收入氏著《北魏平城书迹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54-471页。
[22]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第32页。
[23]殷宪《<源模墓志>书迹以及志文所及北魏源氏的几个干系问题》,收入氏著《北魏平城书迹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54页。
[24]仲威《石本鉴定概论》,第36-37页。
[25]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第59页。
[26]罗福颐的《满洲金石志别录》收录这方墓志,解释当时墓志已流落沈阳,此书的成书韶光为1936年,因此墓志流落沈阳的韶光当在1936年之前。
[27]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胡海帆、汤燕、陶诚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16页。
[28][清]方若;王壮弘弥补《弥补校碑随笔(修订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418页。
本文原载《敦煌学辑刊》2022年第1期,全文转载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22年第5期,引用/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Summer Coming!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