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晚,由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理的“名人大讲堂”第二期在四川省图书馆开讲,著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郦波,开启了一场名为《义重锦官城——杜甫与成都 儒家与中原》的人文讲座。他从杜甫的三首作品入手,带领不雅观众走入杜甫的内心,走入大唐由盛转衰的时期,也走入中原文明与儒家精神之中。
《春夜喜雨》:探求大自然的生命力量
首次在成都讲杜甫的郦波,选择了一首关于成都的诗歌开场,令人意外的是,既不是为天下寒士呼号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不是描述锦江春色的《江畔独步寻花》,而是我们曾在教材里学到的《春夜喜雨》。
乾元二年(759),杜甫携家眷辗转入蜀。在朋侪的帮助下,浣花溪畔的草堂于次年年底建成。上元二年(761)春,是杜甫入住草堂后的第一个春天,一场恰如其时的春雨,将他的喜悦之情推向极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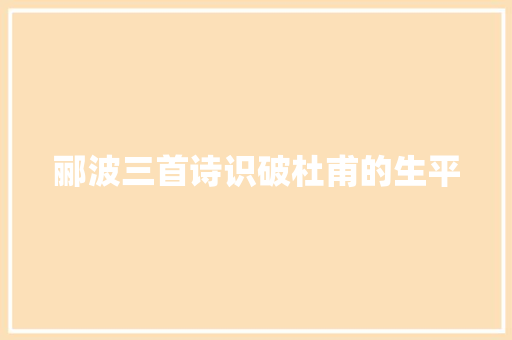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个中最主要的是‘节’字,这里指立春往后的雨水节气。雨水节气有三候,“一候獭祭鱼,二候鸿雁来,三候草木萌动”,代表着一种勃勃活气。“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彷佛是一场通人性的雨,白天大家要干农活,等到农人睡了,它才开始。但便是这样‘潜’入夜的雨,杜甫仍旧能听到声音,解释他的心已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静到了极处。“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杜甫走出房间,看到四周已经一片漆黑,只有稍远处的渔船还亮着点点火光,小雨来,鱼儿出,此时正是渔民们劳碌的时候。垦植的农人已经睡下,江上捕鱼的渔民才开始事情,解释人与自然自有一套和谐的相处之道。“晓看云湿处,花重锦官城”,很多人以为锦官城代指成都,实在不然,三国期间,主管蜀锦的官员住在少城,因此锦官城最初指成都的少城,后来才逐渐衍生为全体成都。杜甫草堂与少城恰好隔浣花溪而对,因此杜甫从溪边望去,看到的正是少城的繁花似锦。
随着郦波老师的讲述,不雅观众们仿佛看到一千多年前的春夜,斜风小雨,江火船明,浣花溪畔一位老者正独自溜达,欣喜地感想熏染这场春雨带来的滋润津润。
“这首诗题为《春夜喜雨》,诗中实在共有‘四喜’。第一,当然是‘时节之喜’。第二,杜甫为什么到成都来?公元759年,关辅大旱,极度缺粮,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的职位,西去秦州,后几经辗转入蜀。因此,杜甫对这场春雨有着分外的感情。第三喜便是‘草堂之喜’,对杜甫来说,这栋‘众筹’而来的小小茅屋,是他生命中灵魂的一个主要归宿。第四喜实在是他的期待,上调入京的好朋友严武能够回到成都。这个欲望在当年年底就实现了。”
看到这里,《春夜喜雨》彷佛都在尽情诉说墨客的喜悦之情,实在不然,要真正理解这首诗,还要放眼杜甫全体人生轨迹,我们可以从其另两首诗中寻得一些端倪。
《望岳》:杜甫的人生根基
在绝大多数杜诗选集中,排在第一首的都是《望岳》,不是由于这首诗写得最好,而是由于这是杜甫流传下来最早的作品。实在,杜甫生平写过三首《望岳》,他望过南岳衡山,望过西岳西岳,但大部分人都只知道东岳泰山。那时的他青春恰好,对人生、对空想都充满期待,出息一片光明。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杜工部的第一首诗,居然是用一个散文式的疑问句开篇。‘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泰山能将阴阳区分、昏晓盘据,解释它是阴阳的法则,而阴阳代表玄门,乃中国文化之本。景物写到极致了,开始回到自己的人生。‘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19岁游吴越,23岁参加科考落榜,搁到本日一把鼻涕一把泪,杜甫却无所谓。你以为他都是穷挫的形象,实在他也曾经青春昂扬。”
通读全诗,彷佛都是景物描写和内心情绪,实在,诗中还利用了一个典故——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儒家讲究家国天下,从孔子、孟子到杜甫,始终秉持这个信念。“他后来写的西岳西岳、南岳衡山为什么不为人熟知,由于这首诗是杜甫人生的根基,他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标杆。”
《登岳阳楼》:无法超越的民气抱负
大历三年(768),思乡心切的杜甫从夔州乘舟出峡,沿江陵、公安一起流落,到岳阳后,登上憧憬已久的岳阳楼,面对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感慨万千,写下著名的《登岳阳楼》。此时,间隔他生命的闭幕只有不到两年的韶光,这首诗险些可以说是杜甫末了的悲壮。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墨客以客不雅观、沉着的口吻讲述自己登楼的过程。“吴楚东南坼”,吴、楚分别指代三国时的吴国与春秋时的楚国,代表着深邃的韶光,东南则是空间,坼是周人占卜时甲骨的裂纹,此句与下句“乾坤昼夜浮”相呼应,一笔写尽了神州动荡的局势。“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此时的杜甫孤独地在江上流落流落,而当年一起写诗唱和的朋友们大多已经离世,他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伤悲,流下泪来。可这泪水是为谁而流?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吐蕃入侵,长安危急,百姓又将陷入无休止的战火之中,墨客的眼泪不仅是为自己而流,更是为大唐百姓而流。
“极沉着,极伟大,又回到极平实,极深远,无法超越,这才是真正在内涵上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老杜总是在自己很惨的时候,从自己的命运,由己及人,本能地去忧念天下苍生,这便是中华文化的窍门所在。老杜在24岁时找到的这根精神支柱,支撑了他整整生平。”
杜甫生平都在贯彻儒家“仁者爱人”的理念,“但是‘爱人’是须要能力和聪慧的,要有内心源源不断的滋养。以是现在转头看《春夜喜雨》,最主要的字不是那个‘喜’,而是那个‘润’,润物细无声。流落失落所的老杜内心欢畅,在巨大的黑夜的沉着里,他听到了统统,看到了统统,识破了统统,欣喜中有一种武断。老杜这么伟大,是什么滋养了他呢?成都滋养了他,四川滋养了他,中原滋养了他,儒家滋养了他,他反过来反哺天下。”
活动结束后,对郦波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采访——
第一读者:“安史之乱”改变了很多墨客的命运,当然也包括杜甫,其“三吏”“三别”等名作都是在这段韶光写下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诗史”的盛名也造诣于这段历史。那我们来做个小小的假设,如果没有这场战役,杜甫在文学史上还能取得如此伟大的造诣吗?
郦波:很多人说历史不能假设,我倒认为历史该当多假设,学历史不是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要以史为鉴,才能看到规律。清代学者赵翼曾写过“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安史之乱”让一个民族处于阵痛之中,痛楚出墨客、精彩的人。虽然我们都喜好追求快乐,但是太浅薄的快乐,没有真正的内涵和代价,伟大的的灵魂都是痛并快乐着。
对杜甫来说,命运之痛、家国之痛实在是其余一种文学的滋养,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肯定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杜甫。但是,纵然没有这场战役,杜甫也终将成为一个伟大的杜甫,由于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走在一条精确的道路上,向着一个伟大的方向提高。(读者报·第一读者 董小玥)
11月19日的郦波《义重锦官城——杜甫与成都 儒家与中原》讲座,读者报轩直播派出了直播团队,并通过“第一读者”客户端进行了现场直播,让更多没能亲临讲座现场的读者同样受到了郦波的演讲传染,同样感想熏染到了杜甫的伟大。(来源|第一读者客户端 作者|董小玥)
温馨提示:如想不雅观看郦波《义重锦官城——杜甫与成都 儒家与中原》讲座的现场视频,请请关注“第一读者”客户端《轩直播》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