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江南》,唐教坊曲名。据《乐府杂录》,此词别号《谢秋娘》,系唐李德裕为亡姬谢秋娘作。别号《望江南》、《梦江南》等。至晚唐、五代成为词牌名。分单调、双调两体。单调二十七字,双凋五十四字,皆平韵。
杨慎《词品》:白乐天改法曲为《忆江南》。其词曰:“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二叠云:“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三叠云:“江南忆,其次忆吴宫。”见乐府。
近藤元粹《白乐天诗集》:诗馀上乘。
《忆江南·江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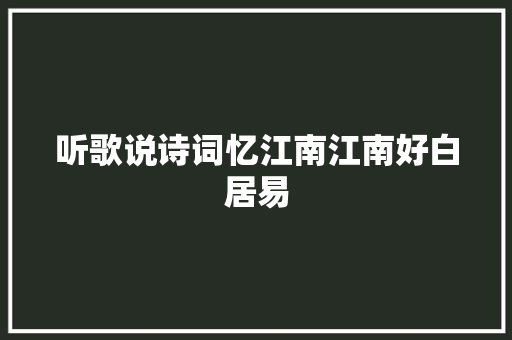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忆江南·江南忆》(一)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忆江南·江南忆》(二)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
吴酒一杯春竹叶,
吴娃双舞醉芙蓉。
早晚复相逢!
白居易曾任杭州刺史两年,后又任苏州刺史一年有余,以是说“风景旧曾谙”,解释那江南风景之“好”不是听人说的,而是当年亲自感想熏染到的、体验过的,因而在自己的审美意识里留下了难忘的影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十余年间,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
全词五句。一开口即赞颂“江南好!
”直抒胸臆。正由于“好”,才不能不“忆”。他“旧曾谙”的江南风景是这样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日出”、“春来”,采取了互文的写法。在这里,因同色相烘染而提高了色彩的通亮度,因异色相映衬而加强了色彩的光鲜性。作者把“花”和“日”联系起来,为的是同色烘染;又把“花”和“江”联系起来,为的是异色相映衬。江花红,江水绿,二者互为背景。于是红者更红,“红胜火”;绿者更绿,“绿如蓝”。
杜甫写景,长于着色。如“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上苍”诸句,都明丽如画。而异色相映衬的手腕,显然起了主要浸染。白居易彷佛故意学习,如“落日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诸联,都因映衬手腕的利用而得到了色彩光鲜的效果。至于“日出”、“春来”两句,更在师承古人的根本上有所创新,吸取各种颜料,兼用烘染、映衬手腕而交替综错,又济之以贴切的比喻,从而构成了阔大的图景。不仅色彩绚丽,耀人眼目;而且层次丰富,耐人遐想。
“旧曾谙”三字还解释了一个更主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追忆江南的作者却在洛阳,洛阳的春天来得晚。“花寒
白居易(772~846),听歌说诗词:《长恨歌》(白居易三个版本演绎经典),听歌说诗词:《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唐时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诗措辞普通,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和元稹并称“元白”,和刘禹锡并称“刘白”。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