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骏
吴宓师长西席是我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奠基人,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他对文化学、历史学、佛学、儒学、中国文学,都有深刻的研究。“早在解放前几十年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即已列有专门词条”评介他①,他可称得起是天下性文化名人。笔者认为,他还是一位精彩的戏剧家。他创作了《陕西梦传奇》、《沧桑艳传奇》等戏曲,至今尚不为人把稳,也没有几个人论述过吴宓的戏曲创作。这里,笔者做一点初探,以求抛砖引玉,望别人更深入地研究它们。
《陕西梦传奇》只有“第一出·梦扰”,写一位青巾儒服的小生,自称“俺乃泾阳吴生是也”,因“国事日非.危急渐启。我陕西虽地处僻隅,亦难号称太平,碧天阴霾,惊俄鹫之欲下;黑酣醉梦,哀秦庭之无人”。吴生遂“与潜龙诸君组织一《陕西杂志》,欲凭笔墨,开通民智;敢借报纸,警觉醉心”。不过办杂志谈何随意马虎,由于缺人才,又乏资金,只出了一期,《陕西杂志》即告短命。因之吴生好梦难圆,夜不成寐,困扰难解。该传奇用《齐破阵》、《声声慢》、《驻马听》、《水调歌头》、《针线箱》、《尾声》六阕加科白组成,叶“寒山”、“桓欢”、“先天”、“廉纤”韵,全曲“-an” 韵到底。
《陕西梦传奇》刻画了一个肚量胸襟壮志、才华出众的青年,他“遣诗怀空赋三百句,听锦瑟不弹五十弦”,力求用杂志广布佳作名篇,但“那堪南柯乍醒,被横枕残。始知半夜经营,都在缥缈虚无间,仍是皎皎明光,影照窗前”。②作者所写因经济窘迫而出版成泡影、幽美诗文难以问世的困境,具有极大的范例性,对付知识分子说来,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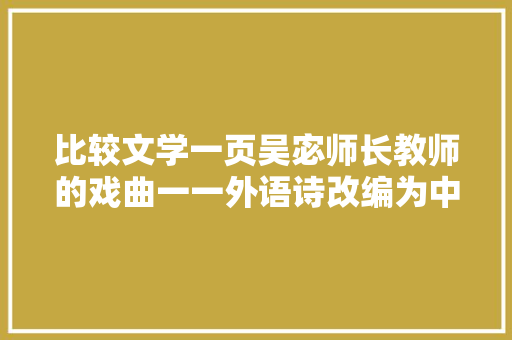
这出戏,没有动作,没有外部冲突。它是一出独角戏,由吴生一人从头贯到底。如果用“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的标准来看,《陕西梦传奇》是吴生的内心冲突,是主不雅观报国为民的欲望和发展文化的心意同客不雅观上无钱难办事的抵牾。这出生理剧,不能用外来的话剧或芭蕾舞哑剧的形式表现,只有用多重抒怀曲与独白粘合的中国戏曲形式,最为贴切,个中《水调歌头》吟曰:“杂思萦愁曲,展卷向案端。那厢精帙巨册.忽映我眼帘。这是陕西旧稿。曾费多少很多多少心血,经营臻完备。泪痕湿锦字,墨花舞素笺。(到今日呵!
)奇迹空、岁月度、故纸残,寸衷明镜,何处常来一念牵。人有成功失落败,事有破灭培植,强必古所难。勿堕十年志,且扬万里鞭。” 抒怀诗之构成在于形象的自我揭示。戏剧中的独白与独唱,其功用不在叙事即描述不雅观形象,而是人物将自己的内在冲突、内心天下展示给不雅观众。这里,一曲《水调歌头》,前半片既写“杂思”、“愁曲”、“泪痕”,又写“那厢”、“这是”、“曾费”,主客不雅观领悟,忆事、写景、抒怀化为一体;后半片则直抒胸臆,抒发面对困难现实、不坠青云之志的刚毅倔强。在《针钱箱》一曲中,表述自己身处“百二重关河凄黯,金瓯残缺力难挽”的形势中,尤要“警遒笔待将民梦唤,(使)自由文明残酷。填海苦志效精卫,感时血泪化杜鹃。勤奋勉、(待它年)重失落雄关,莫误儒冠。”使得吴生这一形象更为之立体化了。它没有儿女情长,却是壮志凌云。
《陕西梦传奇》安排简练,科白精当,曲调深奥深厚,情意隽永。尤其在笔墨上,它遣词化句柔韧灵巧,对仗严整,用事引典丰富准确,韵律平仄颇谙规矩。这部传奇,创作在宣统二年,当时吴宓只有17岁,“未冠束发,及龄受书,尚难通士之称,方肄中学之业。”剧中所写纯系自传与同表兄办杂志的经历。拿当今一样平常同龄少年相较,不谈古文本色与文学教化,仅以志向情怀而言,吴生也是值得有些中学生效仿的。缪越在《读吴雨僧兄诗集》(1927)中说吴宓是“才华骏发,情意纯挚,嘉禾秀出,颖竖群伦,大雅之才,美矣茂矣”。这适于吴宓全部诗作。也可用来夸奖王勃式的少年在戏曲创作上的才情。
《沧桑艳传奇》最初揭橥于1913年到1914年的《益智杂志》第1卷第3期至第2卷第4期。这部《传奇》取材美国墨客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 1807~1882)的长诗《伊芳吉琳》(1847)。吴宓说他是在翻译,但除了首出《传概》开场的《蝶恋花》一曲系直译原文之外,其他与其说是改编,不如说是创作。原诗分高下两部,每部各有5章。吴宓师长西席把序曲改为《传概》,尾声改为《余文》,加上每一章为一出,共拟写12出戏,但“仅成四出而止,终未能续”。
朗费罗(吴译朗法罗,即剧中首出的亨利长卿)的《伊芳吉琳》,写的是历史上实有的一场战役。加拿大东南方新苏格兰有一个阿卡迪奥村落(吴译阿克地村落),该地距魁北克近,原为法国殖民地,1713年法国被英国打败,遂割阿卡迪奥村落给英国。但村落民不服,1755年 9月4昼夜英国统帅温斯洛(吴译温士龙)以“公民暗附法国”为由,抄没全村落。“公民均着于三日内发往南方属省,分别安插,各觅生业,所有该村落田屋财产,尽数充公”。长诗以此战役为背景,描写少女伊芳吉琳(吴译曼珠林,或称曼殊娘)与其未婚夫加布里尔(吴译格布儿,或称格布郎)死活离去,分散后各自流浪,受尽苦痛,只是伊芳吉琳在加布里尔临终前才得与之会晤,原诗缠绵悱恻,哀艳动人。但对战役本身只做背景与起因,并未详尽描写,吴宓在《传奇》中按别的书上供应的历史材料,写出了第3出《寺警》。原诗第1章是描写阿卡迪奥村落的景象风习的,并无戏剧性,吴宓却用《楔游》作第1出,记男女主人公同时登场,加以先容,虽然这有违古代传奇的常规,却也符合西方男女交卸的风习。
《沧桑艳传奇》之前,吴宓师长西席写了一篇颇不短的《叙言》。这联《叙言》实是吴宓评价《伊芳吉琳》的论文,也是他有关比较文学之主见。吴宓拿《伊芳吉琳》与《桃花扇》比较较,说《桃花扇》》是“从来传奇中最上之作”,而朗费罗写100年前“缠绵之情,丽以哀艳之辞……此与《桃花扇》同其用意,同其构造,故亦蔚为雄文,其足以动人”。吴宓认为《伊芳吉琳》“此情奇,其文亦奇”,但是从媒介学角度看“我国今日之习西文者,每不究其幽美之特点,惟以粗解略通为能。一由其初心系借文以通事,而非专意于文学;二由于习西文者其年限非甚长,其程度非甚高,于彼中秘奥一时未能尽窥全豹;三则由其于本国文学素少研究,故文学之不雅观念殊浅,一旦得宝贝珠玉而不能辨其非瓦砾也。由是之故,外国文学之传于我者殊鲜。” 这些话,对本日的翻译学,也是至理名言。由是,吴宓识《伊芳吉琳》的奇文“其构思,其用笔,其遣词,胥与我有天然符合之处。……是篇以其体例论,有起有结,文区二部,部为三章。固与我国传奇之体无稍出入。至以其文论,尤属高尚其意,弯曲其笔,瑰玮其词。即在我国,亦难多得。……至于属词之富丽,隶事之精切,声律韵调之流畅合拍,则非深通其文者,未能言其妙也。”吴宓高度评价朗费罗的文采,更讴歌此奇文所传达的奇情。墨客笔下的女主人公“忧患风霜,奔波终生,而天涯海角,不断痴情,魂魄悠悠,形之梦寐。无如事与心违,机为人误,遂致黄泉碧落,难觅情郎。而鬓发苍苍,已催人老,于是由悲生乐,缘悔而悟,光明心地,不复容纤尘微芥扰其间,至是而曼殊娘者,乃真如射姑仙子,遗世独立,不食人间烟火气矣。”吴宓在传此奇情时,更把稳时期之变迁,“非仅为一二有情人作不平之痛也。《沧桑艳》之作,为传沧桑,而非写艳。”个别男女为情而生、为情而去世,“堕泪成血、望夫化石,三生魂断,行在神伤”,它可悯可悲,但不是极至之情。极至之情,是人生不幸,沧桑陵谷之感:“国破家亡、宗庙为夷、社稷为墟,田庐室墓,付之灰烬,父母戚族流亡转徙,不知其所。己身亦遭流放、飘泊终生,含辛茹苦。茫茫大地,无可托足,而乃风雨天涯,偶一回顾,城廓公民,尽向何方?山川林木,依然犹是,而神州故土,已陆沉不知多少年矣。”吴宓带一种前清遗少式的感伤,在他不满20岁之际,从《伊芳吉琳》看出《桃花扇》般沧桑之痛泪。他倒不是对民国不满或守旧于满清,而是用翻译、创作以警世,“使劫灰不深于中原,愁云早散乎中天。”
吴宓师长西席传《伊芳吉琳》的奇情奇文,不是僵去世地直译原诗,而是改编成戏曲。戏曲改编,历来精良者都是创作。《哈姆莱特》的人文主义精神.因此前同名剧所没有的;《浮士德》把300年资产阶级文明史缩影于永不知足的真善美探索者身上,也是任何写卖灵魂给妖怪的老博士的故事所不可能具备的。吴宓的《伊芳吉琳》,或用其故事梗概与诗情,按中国的民族情调、民族艺术形式、民族风格,另行做创造,措辞、典故、服装、动作全是中国化了的。个中的《传概》、《寺警》两出,与原诗大相径庭,纯为吴宓的构思与创作。
《传概》依原诗的序曲,但吴宓师长西席“更以己意.增删补缀而成”。《沧桑艳》一开场,副末儒服扮亨利长卿上,开口唱《蝶恋花》:“苍莽松林千年迈,败叶残蛩,潢地鸣愁恼。陵谷劫残人不到,高山流水哭昏晓。商妇弦绝伶工杳,片羽只鳞,往事传来少。今我重临蓬莱岛,原野凄迷空秋草”,四句定场诗“人有千年梦.天无半日云。风雨添新景.江山识旧闻”之后,自报家门:“老夫美国文豪亨利长卿是也。东山巨家,南国词客,幼娴文字,蚤擅声华,倚马成诗,登高能赋,屈平哀艳,宋玉风骚,兼而有之。……”本出以四阕《甘州歌》与《小桃红》、《尾声》构成。末端吟四句“格布郎魂断杨柳岸,阿克村落劫残陵谷变。曼殊娘贞化望夫山,亨长卿曲传沧桑艳”停止。《传概》通贯“萧豪”韵,概述全剧梗概,铺陈全剧情调。朗费罗是美国浪漫主义墨客,写早于他100年的故事,不乏凄艳感伤之情。吴宓少年气盛,也富浪漫气质,想象感情丰富,二合自然契合。吴宓家学深厚,精通古典,后留学美国,随白璧德学新人文主义,对马勒伯之古典主义、拜伦之浪漫主义均爱好。他后来传西方精神,却又不附和口语文,都与他既是浪漫主义者、又是古典主义者的抵牾干系。他的许多高足回顾说他,外面死板严明,内心激情亲切浪漫。这正如他的戏曲,写的是外国浪漫故事.而偏用明清传奇的古雅形式与文言文.这大致是一向的。
《沧桑艳传奇》只写了4出,首出《传概》如上述;第1出《禊游》改原诗第1章写景为男女主人公远足相遇、恋爱;第2出《联婚写双方》父母为儿女订婚;第3出《寺警》是根据历史补写英军侵入,阿卡迪奥村落被抄没。吴宓写出的,只及朗费罗原诗的1/3。从已揭橥部分可以看出:
l.吴宓师长西席写戏曲是面对现实,有感而发的,而非作无病呻吟。他与表兄吴文豹创《陕西杂志》,成3期稿,由西安公益书局印行,但只出了第1期(吴宓在上面揭橥反响日俄战役的小说《军国民》),因经费不敷,杂志短命。对此事,激动17岁的少年,因写《陕西梦传奇》。在清华学堂读书时,适逢辛亥革命与第一次天下大战爆发。辛亥革命名曰建立民国,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未成功,反而军阀混战,风云惨澹、得失落旧风。接着欧战风起,吴宓写《哀青岛》以伤国土沦丧。此时创作《沧桑艳传奇》,反对战乱,企求安居乐业,也是情理中事。
2.吴宓的戏曲,个中心不在个人得失落与恩怨,也不在男女艳情,而是忧国忧民,对不能通过杂志传播自由文明、因殖民主义而使村落成废墟、公民流落失落所而怨恨哀伤,表现的是一种力求社会进步的思想。
3.吴宓的戏曲,虽是少年之作,有不成熟之处。或许有人对娃娃的习作不以为然,实在忽略不得的有几点:(l)吴宓的国学底子深厚,诗词曲创作的水平颇是不低。如果不说是17岁、20岁的年青人写的,仅看笔墨功夫、学问功底,本日的戏剧大师们也不会不关注的。(2)吴宓的外文功底更不可忽略。朗费罗是美国19世纪的浪漫派大师,他取材历史的长诗,知识丰富,措辞精美,其词汇量之大,遣词造句之灵巧,口碑载道,是一样平常英语功底浅的人不易读的。吴宓不但节制了诗篇,而且研究了历史,而尤甚者是改编创作成中国戏曲。既不失落原作精神与故事轮廓,又写成民族风格、民族气概的艺术,很是难能名贵。
4吴宓的戏曲发自内心,与其平生感想熏染干系。《陕西梦传奇》有自传性自不待言。《沧桑艳传奇》在吴宓心中总是长期萦绕的一种情结。姚文青《石友吴宓师长西席轶事》中说吴宓师长西席在1972年抄给他一首《鹊桥仙·怀念海伦》曰:“去世埋长侧(邹兰芳),生离偶遇(陈心一),独君(毛彦文)全断(知于1949年到美,1957年已入天主教而已)。爱君深亦负君多,孰知晓(一作谁解得)吾情最恋?碧空难翥(不能乘飞机去),黄泉莫透(不能穿地球中央,直达美洲),此世何缘重见?天涯飘泊曼殊娘,望故国沧桑几换!
”③词的末二句正是《沧桑艳传奇》或《伊芳吉琳》的延续。
5.吴宓是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指他最早在美国哈佛大学专习比较文学,最早在清华大学开设《中西诗之比较》课程。实在,远在民初他尚未出国时,创作的《沧桑艳传奇》便是很卓越的比较文学实践,《传奇》的《叙言》便是一篇很好的比较文学论文。在关于五四之前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上,常推崇梁启超、鲁迅,但他们当时有论述,而缺少比较文学实践。林纾的翻译实践很丰富,可是他并不懂外文,只靠别人口述大意,由他去铺陈写作。而从《沧桑艳传奇》及其《叙言》看,吴宓师长西席既述而且作,既译又改编,且有发展创作,并且是高水平的。因此,可以在中国近代的比较文学历史上,大书一笔。
[注]
①③《回顾吴宓师长西席》,陕西公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44页。
②《吴宓诗集》,中华书局1935年版,《卷末》第1—2页。
刊于《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
又为《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版收入。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事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事理事、陕西省高档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培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前辈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前辈西席等,享受国务院分外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天下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天下文学真髓》、《泰西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天下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当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墨客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天下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