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连:《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文言语气词非口语说》一文中,笔者认为,春秋战国开始在书面语中涌现,并很快广泛利用的语气词,并非出自当时群众口语,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种有别于一样平常笔墨的书面语符号。把“之乎者也”等文言语气词当作古代群众口语词,是没有任何文献根据的,是在西方措辞理论影响下产生的一个莫大误解。这一误解导致我们在认识古代措辞、社会、文学等文明发展史时,产生了持续串缺点。
浏览此文,给我的觉得是“拍桌赞叹”!
但接下来,没想到的是,竟然还有那么多的反对者。可见,质疑、创新,是多么的不易啊!
但爱因斯坦为什么伟大,正好正是其在更大范围内的宇宙尺度上,对牛顿力学的改动和创新,方才得到了巨大的学术成功和历史地位!
牛顿力学只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近似和特例而已!
说得普通点,爱因斯坦格局更大了!
汉字是文化的活化石,中国古代的诸多文化信息在汉字字形中就有表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无形传承者,亦是文化传播的无形纽带。武断文化自傲,紧张的一条便是坚信古代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传承性、延续性。
从甲骨措辞的传承性来解读孟著的可靠性和合理性,该当是我们该做的一项极故意义的事情。作为业余的笔墨爱好者,学术素养确实肤浅,但只要实事求是,就该当“畅所欲言、言无不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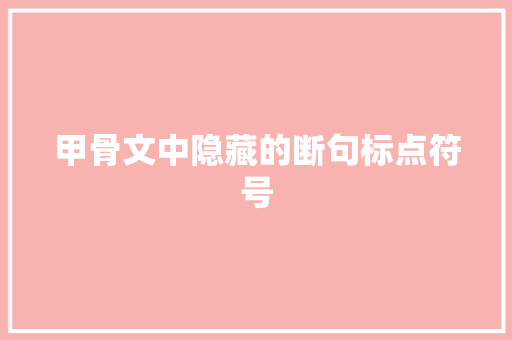
我们在研究文言文(包括甲骨文、金文等)的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即:笔墨是记录措辞的。不管是“之乎者也”,还是当代的标点符号,那都是为了尽可能完全、真实地还原我们的口头措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才产生了“之乎者也”,以及舶来品“当代标点符号”。
反复阅读孟昭连:《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文言语气词非口语说》,创造孟昭连师长西席,大概是师长西席非措辞学专业的缘故吧,其对甲骨文的引用可谓一笔带过。
摘录如下:1有的研究者认为,甲骨文、金文中涌现的几种钩识符号,实在便是最早的标点。此说有一定道理,但这些符号只是偶尔涌现,全部甲骨文、金文中才涌现了有限的几次,完备不成体系,根本不敷以解决议确定句问题,更别说办理音调问题了。
2书面语中除了持续串有读音的口语词汇之外,还必须利用某种符号,使笔墨有所停顿并提示音调的变革,以使阅读者在还原为口语时,更靠近真实。笔墨产生之初,这种哀求还不是那么强烈,由于此时的笔墨还不是大众化的互换工具,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甲骨文是卜人们用以占卜的工具,金文大多用在礼器上,这些笔墨都不是让大众阅读的,而且一样平常字数较少,以是句读的须要还不是那么急迫。
3甲骨文“短缺语气词并非故意省略造成的,而是反响了当时口语的现实”,意味着语气词在上古口语中并不存在。
但迄今为止,甲骨文乃是中国最早的、成熟的古代笔墨系统,可谓是文言文的鼻祖。轻微有点文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甲骨(金)文那是标准的书面措辞,在甲骨(金)文中,虽然没有所谓的“之乎者也”,但作为文言文必不可少的文言虚词,那是比比皆是啊!
如:隹(惟)、其、叀(惠)等。初步统计《甲骨文合集》等涉“叀(即惠)”卜辞达到4044例;涉“隹(惟)”卜辞1913例;涉“其”卜辞10231例。这些词语在甲骨文中的紧张浸染,实在便是孟昭连先生长西席所谓的“标点符号”,“紧张功能是断句”。其例证不胜列举。
范例的“利簋”,其铭文:武王征商惟甲子朝……,该句中的惟,显然是起“断句”浸染的。将“惟”改为“句号”,即:武王征商。甲子朝……文通字顺。
“何尊”,铭文:
唯王初顿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祼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谒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唯小子亡戠视于公氏,有彬于天,彻命敬享哉!惠王恭德欲天,临我不敏。"王咸谒何,赐贝卅朋,用作
(未识)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上述几个“惟(惠)”字,均起到标明几个段落的浸染。即:
唯王初顿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祼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谒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
唯小子亡戠视于公氏,有彬于天,彻命敬享哉!
惠王恭德欲天,临我不敏。"王咸谒何,赐贝卅朋,用作
公宝尊彝。
唯王五祀。
甲骨文中的例子:
1. 鼎(貞)隹(唯)(憂) 一《合集》122
将上句中的“隹(唯)”,改为冒号,即:
鼎(貞):(憂) 一
2. 王占曰其隹(唯)戎其隹(唯)庚《合集》151
将上句中“曰”后的的“其”改为冒号,第一个“隹(唯)”改为引号;“戎”后的“其”改为分号,第二个“其”后的“隹(唯)”改为引号,即:
王占曰:“戎”;“庚”。
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可见,甲骨(金)文中的其、惟、惠等,就相称于起断句浸染的标点符号。这一点毫无疑问可言。
由于很多人并没有阅读过孟著,现摘录其部分内容及读者的评论,以飨读者。
(文言语气词)紧张功能是断句,与当代标点符号类似
笔墨产生之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产生了双向转化的关系。口语转化为书面语的目的是记录与传播,阅读则是通过书面语还原口语;按照一样平常原则,还原得愈真实愈好。但口语与书面语是两种完备不同的表达系统,前者是用持续串有停顿、有音调变革的声音表达意思;后者是用持续串有读音的有形符号表达意思。由于载体的不同,当口语转化为书面语时,原有的语音变革不见了,音调的轻重缓急难以呈现。要想尽可能真实地表现口语,书面语中除了持续串有读音的口语词汇之外,还必须利用某种符号,使笔墨有所停顿并提示音调的变革,以使阅读者在还原为口语时,更靠近真实。笔墨产生之初,这种哀求还不是那么强烈,由于此时的笔墨还不是大众化的互换工具,只是少数人的专利。甲骨文是卜人们用以占卜的工具,金文大多用在礼器上,这些笔墨都不是让大众阅读的,而且一样平常字数较少,以是句读的须要还不是那么急迫。有的研究者指出,春秋期间百字旁边的铭文在十篇以上,但无一例语气词,就反响了这种状况。但竹简成为书写工具后,笔墨的功用改变了,因书写材料得之随意马虎,笔墨便逐渐成为社会大众的阅读物。此时,句读的须要也就应运而生了。“之乎者也”之类句末语气词,正是为填补书面语的停顿与语气这两个欠缺而产生的。
当代的标点(引进自西方),其浸染有二:一是表示在此处停顿,二是指示它前面的那个实词的音调。
有的研究者认为,甲骨文、金文中涌现的几种钩识符号,实在便是最早的标点。此说有一定道理,但这些符号只是偶尔涌现,全部甲骨文、金文中才涌现了有限的几次,完备不成体系,根本不敷以解决议确定句问题,更别说办理音调问题了。
“之乎者也”既然仅是一种标点符号,它们起到的也只是指示浸染,当然不必读出声音来,就像当代的标点符号也不能发音一样。
真正的缘故原由是,古人读书时这些语气词并不发声,而著文引书又多是背诵,于是落笔成文时语气词在引文也就不会涌现。
今人阅读古代经典时语气词也是发声的,那么这种征象始于何时呢? 为什么本来不发声后来又发声了呢? 笔者认为是随着语气提示符号逐渐转化为语气词而涌现的。
甲骨文“短缺语气词并非故意省略造成的,而是反响了当时口语的现实”,意味着语气词在上古口语中并不存在。
李士金:文言虚词研究的创新之作——评孟昭连著《之乎者也非口语论》
本书剖析先哲成果多精辟独到之见,多发古人所未发。如磋商孔子名言“辞达而已矣”之“辞”意,实事求是,令人线人一新。孔子所说之“辞”非一样平常词语之意,而是分外之“辞”,即许慎所云“意内言外”之“词”,此“辞”利用恰当与否,关系文章表达思想感情效果,“辞达”“修辞立其诚”,均是要人们恰当地利用“辞”。古人中为“辞”而“辞”的作者不少,否则,孔子无必要呼吁“辞达而已矣”。笔墨创造是根据人类口头措辞而来,起初用口语表达自己思想感情,把所见所思所闻说出,互相交流、沟通,然后根据口语造出相应笔墨,记录人类文明进化成果。然而,由于汉语单音节的特色,以口语表达思想情绪,尚有语气神态音调抑扬高下之不同,以是书面语单靠实字记录社会人生内容很难准确表达丰富繁芜之思想感情,故必须用分外之“辞”来赞助与口语对应之笔墨,以加强表达效果,表示社会人事之深微杳渺,表示人们生理之细微差异。《墨子》所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正是此意。本书还旁征博引先哲文籍,通过对“辞”诸多异名的剖析,论述“辞”之非口语实质,并且以“辞非口语”来阐明历代文人感叹“虚字难用”的缘故原由,通情达理,极有说服力。正由于“辞”非口语,故先秦经典利用起来时有错乱,后世如司马迁、韩愈、苏东坡等大家,亦不乏利用缺点的问题。“辞”作为“语助”广泛利用于古人书面语中,读书人朗读背诵诗词文章,一定会影响其口语表达状态。某些知识分子虽然满口之乎者也,但不会改变“辞”非口语的实质特色。
本书论述考证极为抽象之问题,最大特点因此大量事实讲话,许多个案考证,细节生动,引人入胜。从古代口语之稽核到文言虚词之“爆发”与迅速“消逝”,从“辞”之实质非口语到文言虚词的产生,从“辞”之繁荣与“言外”不雅观念的消亡,再到“辞”的加减与更换,直至第七章磋商古人修辞为文之法,既充满生动形象而又准确的事实与数据,又环绕核心论题,加以全面系统而又深入辩证的剖析论证,可谓一“辞”极乎天人之际,万象归于本体之理。如论述《春秋》及三传中之语气词问题,就用精确的统计数据,相互比较,在比拟中创造问题,办理问题。例如作者不但创造“春秋战国书面语中的常用语气词如乎、也、矣、者、焉等,《春秋》中竟一个都没有”,这种措辞征象,两千五百年来没有受到学界把稳。作者对这种征象进行了细致剖析,认为《春秋》没有语气词有三种可能:一、因文体缘故原由,或作者故意省略。二、本来有,但在流传过程中被人删掉,或传抄时漏掉。三、原文本来就没有,由于那时口语中并没有语气词。本书详细稽核论证,打消前两种可能性,证明只有第三种可能:那时口语中没有语气词,《春秋》是据实记录之书面语,较多地保留了口语之原貌。《春秋》中没有语气词,《尚书》中语气词亦极为罕见,既不是文体缘故原由,更非在流传过程中被后学删除,只是由于当时口语中没有后来盛行的书面语气词。《春秋》原文只有一万六千余字,记载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间二百多年鲁国历史,其笔墨之简练不言而喻。随着生产力水平和不断提高,笔墨不断进化,社会上利用笔墨者不断增多,所表达的之社会生活内容愈益繁芜深广,文言书面语之“辞”便被文人发明(假借)出来,越来越多地利用于书面笔墨中。然作为一种非口语成份,利用之多少、如何利用因人而已,很难达到完备统一,故涌现《春秋》三传“修辞”之迥然差异。显然,相对付有的学者所谓春秋战国的口语语法“尚未固定”的不雅观点,孟教授的这个阐明更具说服力。
再如,对文言虚字“也”的剖析极为细致深入,“也”是文言中利用率最高之语气词,一样平常措辞学家说它具有“多功能”,可以表达多种语气。本书比较剖析稽核《诗经》《礼记》《老子》《左传》《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颜氏家训》《马说》等大量古代文籍资料,比较剖析论证,创造“也”只是一个纯挚的断句符号,并无语气功能。对柳宗元、朱熹、陈骙、卢以纬、袁仁林、马建忠、王力、向熹等人干系论述,辩证剖析,肯定其得,否定其失落,态度公允。随着时期变革,后世学者对付“也”字修辞功能的认识并分歧一,涌现认知上的偏差,许多时候处于模糊状态,使得“也”字在后世文人的笔下,不但有起先之“断句”功能,且有了表达语气之意义。然在《春秋》三传时期,“也”字只是作为“断句”符号,其功能相称纯挚。
本书稽核《晋史》引用《世说新语》用减字法和换字法,因《世说新语》是古代纪实条记“小说”,比较真实地反响了当时口语状况,以是虚词较少,《晋史》引用时为符合书面文言规范,便作了相应改动,其紧张方法便是增加文言虚词。《新唐书》删削《旧唐书》如法炮制,“基本原则便是文言代口语”。宋祁生造文言词汇,许多形象事实触目惊心,通过本书剖析,可知玩弄笔墨游戏不良学风文风自古已然。宋祁生造之一千六百余词汇,多不合理,只有“杀人灭口”“自食其言”等少数几个词被当代人所继续利用。本书揭示出诸如此类的措辞征象,并加以全新的阐释,其典范意义远远超越一样平常学者想象,盖因其所引证之文籍资料,具有范例性、代表性、示范性,可让读者得意之、领悟之、想象之,言有尽而意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