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1045-1105年)在宋代文苑的地位,论诗文,与张耒、晁补之、秦不雅观同游苏轼门下,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在“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造诣高,是江西诗派的创始人,后人将他与苏轼合称“苏黄”。论书法,黄庭坚与苏、米(芾)、蔡(襄)同列四大家。《宋史·黄庭坚传》称他“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
宋代书法,超越了唐代“尚法”,开“尚意”之风。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序》说:“以张怀瓘《画品断》,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利害也。”照此,逸品还没有资格列入等格。因其“不拘常法”。张怀瓘的《书断》也同《画品断》一样,将书法分为神、妙、能三品,没有“逸品”之说。
[宋] 黄庭坚/李白《秋浦歌》并跋(局部)/17.2×30.4cm×58/拓本/见《海山仙馆藏真续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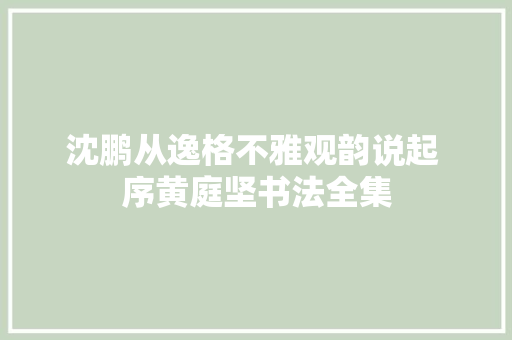
到了唐末宋初,《益都名画录》的作者黄休复,自绘精于图画者58人,批驳四格,一反前说,于神、妙、能三格之前冠以“逸格”。曰:
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周遭,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模范,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
至此,张怀瓘的“不拘常法”得到提升,不入格的逸品一跃登上最高品位。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正合逸品宗旨。到了清代,恽南田将逸品简括为“纯是天真,非拟议可到”。逸品的提出,开拓、更新了审美境界,为文人字画起了前导浸染,在字画史上,有划时期的意义。苏轼的《枯木竹石图》、《黄州寒食帖》,米芾的米点山水,小楷《大行皇太后挽词》,蔡襄的某些书函,都可以看作有异唐人审都雅的逸品代表作。苏轼于王安石书法亦称其“得无法之法”。
书法宋四家,都善行楷,唯独黄庭坚行、楷之外更善于草书,黄庭坚草书的造诣使他于苏、米、蔡之外,独树一帜,在书史上的地位进入新的高度。按宋初风气,文尚韩愈,诗宗杜甫,书法师颜真卿。在学颜这一点上,四家都无例外,后来各抒个性,形成自家面貌,也首创了宋代书法多元化的格局。黄庭坚学书,服膺《瘗鹤铭》,认为大字无以过之,草书直接管益于怀素、杨凝式,但《瘗鹤铭》的影响不止于楷书。草书不但是楷书的简化、迅捷,还有特定的审美理念,且最能表示个性。黄草长于中锋立定,侧锋取势,大开大合,纵横争执而无不快意,特殊善于对动态的节制,共性中有个性,仍保留着本人楷书中宫紧收向外拓展的特色。“比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黄庭坚曾用来自譬作诗,借以形容他的草书也颇有味,可以理解为“用尽力气,不离故处”,笔法的普遍性规律“无往不复,无垂不缩”,也可以扩展到草书的章法。比之唐代张旭、怀素,黄庭坚的原创性有异古人、后启来者,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图注:[宋]黄庭坚/史翊正墓志铭稿/33.5×65.3cm/纸本/1098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早在魏晋时期,已随玄学兴起关注到“意”,以此弘扬个性存在,摆脱儒家思想束缚。在宋代,“尚意”书风不是大略地摈弃“法”,而是授予“法”以较低层次的美学意义。评价字画在崇尚逸格,推许尚意的大环境下,黄庭倔强调“不雅观韵”、“以韵为主”,这又与唐代的“先不雅观神采”有别。“神”相对付“形”,欣赏过程中“神采”夺人眼目,精光外射。“韵”属别一境界,它游离于“形”“神”之间、之外,有余味,经得起逐步地细细品味。“韵”的审都雅与禅宗思想的出世精神密切干系,导向对人生的超脱,对儒家“道”的背叛。苏轼虽然没有像黄庭坚那样突出“韵”为独立的审美范畴,但是他对禅宗的参悟,对“无法之法”的主见,对“萧散”、“简远”、“清新”的推崇,实质上与倡导“韵”的精神同等。
不雅观赏与创作,从两个方向达到基本同等的认识,然而态度不全同。黄庭坚论书的深刻见地,既有禅宗思想影响,还有丰富的创作履历作根本。他与苏轼以至历代所有的大家一样,力主学习必须刻苦。“笔冢、墨池”的精神绝不可少。但都主见学书贵在通其意,遗貌取神,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在苏东坡为“我书意造本无法”,在黄则为“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不雅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纸笔,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无法是相对的,无法—有法—无法,是辩证过程。无法既指书法的普遍规律,也指作书的详细方法。无法在尚意书风的审美理念中有着分外的意义:有法即无法,故意即无意,此中仍与禅宗理念相通。
倘把“无意”推到极点,便没有任何刻意追求,不会对书法存任何欲念。黄庭坚的名句“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也容许以说是儒家入世思想的表白,斩钉截铁地否认“随人作计”,不甘“后(于)人”,提出“自成一家”的目标。虽然苏、米、蔡诸公都以不同的路子成家,比较之下,苏轼更看重“顿悟”;米芾通过“集古字”别开生面,转益多师达十余家。不断地自我肯定与否定是大艺术家一定的经历。然而宋四家中明确标立“自成一家”者,以黄庭坚最自觉。足见其胆略自大。有了这样的目标,黄庭坚不断完善自我,早期学周越,后来恨“抖擞俗气不得脱”,觉周“劲而病韵”,遂改初衷,又曾自评元祐间字“用笔不知擒纵,故字中无笔”,接下来指出:“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岂易言哉。”笔法为书法之本,历代大书家无不为追求笔法下最大功夫,又各以笔法的分外性自主门庭。笔法最纯挚也最丰富,看似大略单纯实在最难。从初学者到宗匠,从真品佳作到赝品仿制,但看笔法“基因”可以了然。还是黄庭坚说得好:“古人工书无它异,但能用笔耳。”米芾回禀御问所谓“勒字”、“排字”、“描字”、“画字”、“刷字”等等,无非指各家笔法个性特异,不必过分拘泥每个词语的详细含义。黄庭坚指张旭、颜真卿、王羲之、怀素、索靖诸家笔法互异,而又“同是一笔,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与能者争衡后世不朽,则与书艺工史辈同功矣。”此处“与能者争衡”,实在是心手不一,没有达到相忘的程度。“争衡”必“故意”,忘却自我,失落去自我,于是降落了书法的代价。
作为草书宗师的黄庭坚,在“自成一家”的创造性运思中得到的真知,值得负责领会。纵然面对书圣,也非抛弃真我马首是瞻。他在跋《兰亭》中说:
《兰亭序草》,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复不雅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摹写或失落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会其妙处尔。
《兰亭》虽是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以为准。……不善学者,即贤人之过而学之,故蔽于一曲,现代学《兰亭》者多此也。
学长处,会妙处,要在“各存之以心”。有了“自成一家始逼真”的年夜志必定不轻易放弃自我,直至不盲从圣者,以“自我”的态度取舍交融。这里涉及到了详细的方法,而原创与临摹则是一对避不开的抵牾:
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着迷,乃到妙处。唯存心不杂,乃是着迷要路。
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不雅观之着迷,则下笔时随人意。
以上事理与方法,适用诸体,而于草书有更强的针对性。临摹是学书公认的主要方法,然不能僵化,须长于领会神韵。“张古人书于壁间”,办法很详细,但是有用,由于这样做随意马虎得古人书之全神,与古人优游神交,取形更得神韵于形似之上。“草书妙处,须学者得意,然学久乃当知之。”唯有“得意”的东西才真正属于自己,才有自家面貌。
图注:[宋]/黄庭坚/致公蕴知县尺牍/30.4×43.5cm/纸本/109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崇尚逸格写意,倡导文人风范,直至以魏晋风姿为楷式,黄庭坚对“俗”的批驳成为其书学中一个不可忽略的亮点。请看:
学书必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其书乃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话已说到这等地步。哪怕笔墨比得上钟繇、王羲之,如若短缺道义、学问、性灵、理法,仍旧还是“俗”,而“俗”是最不可救药的。黄庭坚的忌俗、厌俗、鄙俗精神,散布在他的书论中,强烈地反响出对士大夫态度、对传统道义、对审都雅念的坚持。“俗”,与“韵”、“逸”直接对立,方枘圆凿。“俗”必定失落去真我。所谓“自成一家”者,我们不必认为凡学书必须大家卓然成家,不必误解为凡“自我”统统皆好,主要的是从人文态度尊重个性,发扬自我意识,真正做到这点,也必定能够尊重别人,吸取他人长处,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米芾也是一个竭力排俗的人,对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都有激烈批评。对此,或容许以看作是出于宋代尚意对唐代尚法的背叛态度,也包含老米个性使然。米芾反俗同时喜好一个“趣”字;黄庭坚在尚意、不雅观韵、反俗的同时,发扬了自己的书学不雅观,个中包括对“拙”切实其实定,“凡书要拙多于巧”。“拙”与“巧”的辩证关系最早发源《老子》,但在后来的艺文批评中对拙、巧有了新解。与黄庭坚同时期的陈师道《后山诗话》提出“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肯定了“拙”的美学意义,并且也没有忘却对“俗”的鞭笞。可见同代人思想相互影响之深。到了明末清初,傅山“四宁四毋”之说继续和发挥了古人思想,傅山对“俗媚”的斥责达到了空前激烈的地步,扩展到对社会政治的态度。循着这条路线,我们可以加深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解。
自黄庭坚千年而后,出版了五卷本《黄庭坚书法全集》。黄庭坚生前说过,他的多少见地须待数十百年后才被人理解。虽然历史上的地位早被公认,但认识的深度、评价的角度随韶光推移不断变革。
黄庭坚生前万没有预见到,千年后的一位同里,以十数年如一日的精神,怀着巨大激情亲切,全力整理、发掘先祖遗作,厘订考证,坚持不懈地作系统研究。这位中年人叫黄君。他把环绕黄庭坚的研究奇迹当作学习黄庭坚的过程,写诗、作字、撰文,连同黄庭坚的孝悌之心一并成为学习榜样。2008年,黄君书法集出版,诗词界前辈刘征以“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为题评价:“黄君甫及中年而才艺大展。”“墨韵诗声,相融相济,其益两收,其乐无穷。”“超人之成果显示超人之精力,超人之精力显示超人之勤奋,超人之勤奋显示超人之才华,令人惊叹。”“君无暴躁之气,有执著之功,于浮云飞絮到处飘舞之中,其特立独行如此。”评价至诚至高。
黄君编《黄庭坚书法全集》,积蓄多年,先是四卷本《黄庭坚研究论文选》问世,还出版黄庭坚书法专著,组织黄庭坚研究学术研讨会,进而为《全集》不舍昼夜,全力以赴。翻读此书清样,我以为“全”是黄君追求的主要目标。
此书力求网罗天下,做成佳构。循此,将年夜师置于历史的环境中,作全面系统的稽核。《全集》包含的“辞吐辑录”“历代评论辑录”以及约五十万字的“书法年谱”、“作品考析”、“书法评传”,集资料性与学术性,求实精神与历史眼力于一体。《全集》把传世作品分为真迹、临摹之作、托名书和伪作四大类。黄庭坚传世之作多数没熟年款,作品系年难定,而黄君早有专著《山谷书法钩沉录》就一系列作品作了专门的考证,有许多见地独抒胸臆。关于《草书千字文》刻本,编者认定为黄氏早期之作,而墨迹本《行楷千字文》则为后人伪托。六卷本《历代千字文墨宝》(吉林美术出版社)也认墨迹本《行楷千字文》为“无名氏仿黄庭坚”。此作品里的一个“玄”字末了少一“点”而略显挖除的痕迹,此中玄机大概值得讲求。从学书的态度看,无论何时都要取法乎上,名碑剧迹,经由历史考验值得反复临习,纵然不甚有名的墨迹、拓本,只要真有艺术代价也不宜任意弃置而必取其所长。该书乃至把托名书与伪迹分开,认为“托名书”或出于对被托名者的尊敬(略如岳飞《还我河山》《前后出师表》),不必纯以伪作视之,这又是一种文化眼力。该书将黄庭坚书法区分真迹、临摹、托名、伪作四大类,抱着许多苦心。但是无论为着考据或临池,识别真伪和区分利害都是最主要的。历史上任何一位大家,如果撇开其代表性的精品,肯定大为逊色,失落去了存在的根基。确认大家历史地位,紧张看代表作品。倘若辨别不严,鱼龙殽杂,便会模糊大家形象乃至误导。《兰亭》论辨引起广泛关注,主要缘故原由在《兰亭》分外地位,又因其分外地位增加许多疑窦。黄君主编这套全集,充满激情亲切,他不掩饰笼罩自己的偏爱。偏爱当然有别于偏执。偏爱在艺术欣赏与创作中不可避免,意味着独到的视角、独特的追求,学术上表现为学者的个性。由此,偏爱之心乃至很可爱。黄君将心目中尊敬的先祖列为“千年书史第一家”,也解释他的胆略,敢于直抒自家识见,言人之所未言。这当中是否也受了“自成一家始逼真”的精神的感召呢?
应黄君和出版社的激情亲切约请,为本书作序。我与黄君交流了对黄庭坚书法的认识,也包括对当今书法发展状况的一些意见。书法须要人文关怀,书法的持续发展,不能没有原创精神与精英意识,要有一批有识见的实干者奉献一木一石。研究书法史为着启迪当代,历史上精彩艺术家具有榜样的力量,书法本体意义不因时空转移而丢失。深入阐释某一个案的代价会超出“这一个”本身。以黄庭坚研究为例便可解释。这里也要提到本书编委会许多专家包括水赉佑编《黄庭坚书法史料集》的贡献。看黄君主编的《黄庭坚书法全集》,看许多古代书法史论资料的发掘研究,会加强我们当代书法发展的自觉意识,无愧先人并有启来者。
本文选自《中国字画》杂志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