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像)
扯的有点远,不过,困境实在是文学家必经的修炼,但不是所有经由这个修炼的人都可以成为大文学家,在这个修炼过程中,能出造诣的只有那些具有思想性的人,才会成为不被困境打垮的少数青史留名之人。
实在,唐代还有一位被后世称为“诗豪”的大墨客刘禹锡,他生平活了七十一岁,风华正茂的二十多年全在贬谪之中度过。但刘禹锡之以是没有被打垮,个中的主要缘故原由是由于他是一位思想性极强的哲学家(有人可能不服,但刘禹锡的确写过哲学著作叫《天论》,乃至还有一点唯物主义思想。),如果不是具备这种哲理思想和乐不雅观的人生态度,估计刘禹锡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文学造诣。
刘禹锡的诗作中,最具备哲学思想的一首,也是传诵最广的一首诗是本日我们要读的这首《乌衣巷》,全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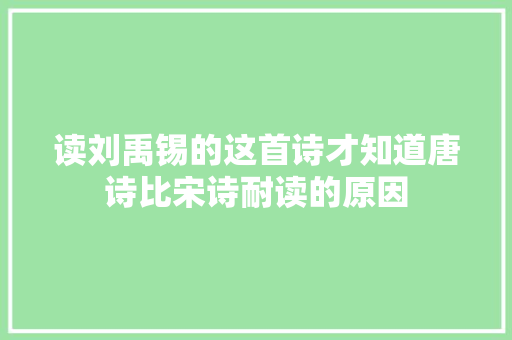
(诗词书法)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凡百姓家。
要读懂这首诗,必需要理解乌衣巷的来历。乌衣巷现在还有,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秦淮河上文德桥旁的南岸,地处役夫庙秦淮风光带的核心地带,它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古巷。乌衣巷的历史最早要上溯到三国期间,那个时候乌衣巷是吴国防守石头城(也便是南京)的部队营房所在地,当时军士为了跟其他部队差异,都穿着玄色制服,故以“乌衣”为巷名(也有一说:说晋时王、谢两族子弟善著黑衣,私下认为这种说法不确;还有一说是有传说性子的,说是有个人叫王榭,他海船失落事之后误入乌衣国,娶妻生子,后返回中土,遂把自己居住地改称为“乌衣巷”,我们也认为不确,我们选择认可南京市地名委员会的说法,如下图)。
(”乌衣巷“的由来)
三国东吴黄龙元年(即229年),孙权称帝,定国号“吴”,史称东吴,其时这时吴国才正式开始,便是这一年的秋日,孙权将都城从武昌(今湖北鄂州)迁到南京,取“建功立业”之意,将秣陵改为“建业”。后来西晋灭吴,建业被改称“建邺”(灭国历史前面文章写到过了),西晋灭亡后,东晋政权立都面京,又改称“建康”,东晋的实权大臣王导就住在乌衣巷,再后来这里便成为王、谢等豪门大族的住宅区(相称于豪门住宅区)。东晋能顺利重组政权,使晋王朝得以再延,紧张得力于王导的谋划和周旋,以王导为代表的王氏家族和以谢安为代表的谢氏家庭都居住在孙吴乌衣营旧址,这时“乌衣巷”的名称已经很响亮了。
(王导雕像)
所谓的王、谢,指的是两个名人及他所代表的家族。王是王导及其家族,他辅佐创立了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谢指谢安,谢安指挥著名的“淝水之战”,这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以少胜多战例,晋军以八万军力打败符秦百万大军。后来王、谢家族人才辈出,书法史上的“书圣”王羲之与其余两位大书法家王献之、王洵都是王氏一族的后人;中国山水诗派的鼻祖谢灵运,后来的大墨客谢惠连、谢朓,都是谢氏一族的后人。王、谢二族是范例的中国式贵族,他们居住的乌衣巷因此也非常有名。
(谢安雕像)
可叹的是,这么有名的乌衣巷,到了唐代,由于战役的缘故原由完备沦为废墟,废墟得到重修之后,就成了民居,这里再也不是豪门居住地,而成了普通老百姓的寓所。
朱雀桥横跨秦淮河,是通往乌衣巷的必经之路,所说旧日这座桥上装饰的两只铜雀的重楼便是东晋的谢安所建。
现在的乌衣巷是1997年,秦淮区公民政府规复重修的,新生的乌衣巷挖掘、展示乌衣巷源远流长的历史,重修了具有民族风格的王、谢古居纪念馆。历经千年的沧桑,如今的乌衣巷虽已不复昔日的繁华,没有豪门士族的衣冠汇聚,但却多了许多游人探访历史的踪迹,成了人文荟萃的旅游胜地。
(现在的乌衣巷)
来看原诗: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实在这两句有“文章本天成”的身分,比如“朱雀桥”与“乌衣巷”天然对偶,刘禹锡做了“偶得之”的那只“妙手”。朱雀桥边生有草和花,显然这是一个活气盎然的春天,但为了加深诗意,墨客在这个草和花前面加了“野”字,一方面解释这里的草和花是没有人管理的,是野生的;另一方面通过“野”来形容这里的荒凉和冷落。朱雀桥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华已经不再,只余下了野草侵道,野花乱开。一天中有那么多韶光点,为什么墨客选择了傍晚?是由于斜阳的残照更适宜表达日薄西山的惨淡,斜阳一出,衣冠来往、车马鼎沸的乌衣巷完备带入了寂寥、惨淡的氛围之中,用“野”,用“夕阳”用“斜”,都是为了产生比拟。这几个字都值得细心体会。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凡百姓家。”听说白居易读到这两句时“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他实在无法言喻对这两句的惊叹。为什么呢?由于依照上面两句的铺垫,墨客可以转入议论,发点嗟叹了,比如宋人孙元晏的“古迹荒基好叹嗟,满川吟景只烟霞。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顾令人忆谢家。”(《乌衣巷》)再比如宋人罗必元“乌衣池馆一时新,晋宋齐梁旧主人。无处可寻王谢宅,落花啼鸟秣陵春。”(《乌衣巷》)。但刘禹锡不这样,他仍旧写景,他不说理,他把目光转向了巷口飞来飞去的燕子。宋诗和唐诗的差别我们之前说过,宋人爱讲理,不管什么诗,都要转出一个道理来,唐诗不这样,唐诗要说的,都在事物的描写之中,不硬性贯注灌注给人观点,以是唐诗比宋诗耐读。难怪有人说唐诗是“大风吹屁股,凉气透膀胱”,而宋诗是“坡陡尿流急,坑深屎落迟”,这两句话可能有点糙,但话糙理不糙。刘禹锡的这一首只是个例子,他比那两个宋人的同名诗,高明多了。
(刘禹锡的《乌衣巷》诗意)
实在就算寿命再长的燕子,也不可能活过几百年,现在在百姓家里筑巢垒窝的燕子肯定不是几百年前的飞行在王、谢两族屋前的老燕,这种文学想象显示了刘禹锡超人的艺术匠心,燕子还是燕子,但此间的主人早已变换,乌衣巷的繁荣早已不再的观点层叠加深,今昔比拟被强化了。全诗看似没有一句是用来讲道理,但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番道理是在读者脑海里自己天生的。
朝代更迭,兴衰变迁都是再正常不过的道理,但也是再呆板不过的道理,刘禹锡把这样的情景写在了一首画一样平常的诗里,或许,饱经坎坷的刘禹锡早已识破了人情道理,识破了衰与荣的变换,把繁芜的道理说大略已经不易,更何况,他说的这样美,”诗豪“之名,名不虚传。
(【唐诗闲读】之99,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