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略》的打算代价
《三略》问世之后,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光武帝诏书中引用《三略》内容,解释《三略》在东汉初年已经广为流传。东汉末年陈琳在《武军赋》中已经将《三略》与《孙子》、《吴子》、《六韬》相提并论。唐朝初年魏征将《三略》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做为帝王治国安邦的参考。宋代元丰年间,《三略》被列为“武经”之一,从此取得了兵学经典的地位。历代学者为它作注和阐说的大概多。据统计,从南北朝期间开始,经唐宋到清末,为该书作注、讲授的就多达60多家。 对付《三略》的代价,许多学者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南宋著名学者晁公武说,《三略》其书,“论用兵机权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生易去世,国可以存易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三略》说:“其大旨出于黄老,务在沈几不雅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仇敌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每每用之。”这些评语,都准确地指出了《三略》的军事学术代价和打算实用代价。这也正是《三略》之所以为历代浩瀚政治家、军事家所高度推许的缘故原由所在。 由于揭示出了治国方略、用兵韬略的一些普遍规律,《三略》不仅在海内受到推崇,在国外也产生了相称影响。唐朝年间,《三略》传入日本。日本的战国时期,《三略》与《六韬》一起被定为武校的紧张教科书,并产生了林道春的《黄石公三略评判》、《三略讲义私考》,山冢义炬的《三略备考》,山鹿高祐的《三略要证》,喜多村落政方的《三略便义》等。同时,《三略》在朝鲜等国家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三略》的不朽代价。就商战而言,《三略》最具有启示意义的,是八个字:“为国之道,恃贤与民。”贤,讲得是重用人才;民,讲得是争取民心。
中略
主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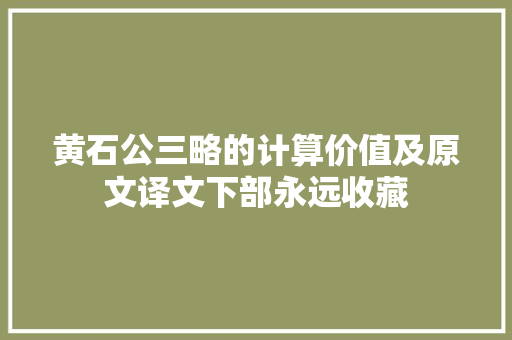
本篇自己概括是“差德行,审权变”,和上略一样强调以人为本,以德服人,但本篇紧张特点是在用人上提到了“权变”,便是要以个人不同的特点而加以利用,虽然王者以德治人,但利用人时完备可以不考虑这一点,只要其能为我所用就可以了。本篇提出了“谲奇”和“阴谋”这些用人的策略。
原文
夫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①,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群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以是然。故使者不待礼赏;有功,美而无害。王者②,制人以道,降心折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霸者③,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
《军势》④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
《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去世;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军势》曰:“无使辩士⑤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军势》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休咎。”《军势》曰:“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去世,智者不为暗主谋。”
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落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
故圣王御世,不雅观盛衰,度得失落,而为之制;故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⑥。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诛伐。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谋,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
贤人体天,贤者法地,智者师古。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夫高鸟去世,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其心。夫人众一合而不可卒离,威权一与而不可卒移。还师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是谓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论驳也⑦。存社稷罗英雄者,“中略”之势⑧也;故世主秘焉。
注释
①帝者:指传说中的五帝,说法不一。
②王:指三王,即夏、商、周三代的创始人夏禹、商汤、周武王(一说将周文王、周武王并为一王)。
③霸:指春秋五霸,说法不一。
④《军势》:古代兵书,已失落传。
⑤辩士:能言善辩的人。
⑥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方伯,商、周时一方诸侯之长。
⑦驳:杂。
⑧势:威力。
译文
三皇不须要任何辞吐,教养便流布四海,以是天下的人不知道该归功于谁。五帝效法天地运行,增设言教,制订政令,天下因此太平。君臣之间,相互推让功劳。四海之内,教养顺利实现,庶民百姓却不知个中的缘故原由。以是,利用臣属不需依赖礼法和奖赏,就能做到君臣和美无间。三王用道德管理民众,使民众心悦诚服。三王制订法规,以防衰败,天下诸侯按时朝觐,天子的法度实施不废。虽然有了武备,但并没有战役的祸患。君主不疑惑臣属,臣属也不疑惑君主。国家稳定,君位巩固。大臣应时功成身退,君臣之间也能和蔼相处而无猜疑。五霸用权谋统御士,以信赖结交士,靠奖赏利用士。失落去信赖,士就会疏远了。短缺奖赏,士便不会用命了。
《军势》上说:出兵作战,重在将帅有专断指挥之权。军队的进退如果都受君主掌握,是很难打胜仗的。
《军势》上说:对智者、勇者、贪者、愚者的利用方法各有不同。有智谋的人喜好建功立业,年夜胆的人喜好实现自己的志向,贪财的人追求利禄,愚鲁的人不惜性命。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来利用他们,这便是用人的奇妙权谋。《军势》上说:不要让能说会道的人评论辩论仇敌的长处,由于这样会惑乱民气。不要用仁厚的人管理财务,由于他会曲从于下属的哀求而摧残浪费蹂躏钱财。《军势》上说:军中要禁绝巫祝,不准他们为将士们预测休咎。《军势》上说:利用侠义之士不能靠钱财。以是,义士是不会替不仁不义的人去卖命的,明智的人是不会替昏聩的君主出谋划策的。
君主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大臣就会背叛;君主不能没有威势,没有威势就会损失权力。大臣不能没有道德,没有道德就无法辅佐君主;大臣也不能没有威势,没有威势国家就会衰弱。但是大臣威势过了头则会害了自己。
以是圣明的君王管理天下,不雅观察世道的盛衰,衡量人事的得失落,然后制订典章制度。以是诸侯辖二军,方伯辖三军,天子辖六军。世道乱了,叛逆便产生了。天子的德泽枯竭了,诸侯之间的缔盟赌咒、相互攻伐也就涌现了。诸侯之间,半斤八两,谁也没有办法降服对手,于是便争相延揽英雄豪杰,与之同好同恶,然后再利用权谋。以是,不运谋划划,是没有办法决嫌定疑的;不诡诈出奇,是没有办法破奸平寇的;不秘密谋划,是没有办法取获胜利的。
贤人能够体察天之道,贤人能够取法地之理,智者能够以古为师。以是,《三略》一书,是为衰微的时期而作的。《上略》设置礼赏,辨识奸雄,揭示成败之理。《中略》区分德行,明察权变。《下略》陈述道德,稽核安危,解释残害贤人的罪过。以是,君主深通《上略》,就可以任用贤士、制服仇敌了。君主深通《中略》,便可以驾御将帅,统领兵众了。君主深通《下略》,就可以明辨兴衰的根源,熟知治国的纲纪了。人臣深通《中略》,就可以造诣功业,保全身家。
高飞的鸟儿去世完了,良弓就该收起来了。敌对的国家灭亡了,谋臣就该消灭了。所谓的消灭,并不是消灭他们的肉体,而是要削弱他们的威势,剥夺他们的权力。在朝廷上给他封赏,给他人臣中最高的爵位,以此来表彰他的功劳。封给他中原肥沃的地皮,以使他的家中富有。赏给他美女珍玩,使贰心境愉悦。军队一旦编成,是无法仓促终结的。兵权一经付与,是无法立时收回的。战役结束,将帅班师,对付君主来说,这是死活存亡的关键时候。以是,要以封爵为名削弱他的实力,要以封土为名剥夺他的兵权。这便是霸者统御将帅的方略。因此,霸者的行为,是驳杂而不纯的。保全国家,收罗英雄,便是《中略》所论的权变。历代做君主的,对此都是秘而不宣的。
下略
主旨
本篇依旧强调德对付国家的主要性,并指出为王者管理国家要尊于道,道与德二者相辅相成,只有这两者得到很好的统一,那国家的安危就可预知,只有道与德行于天下,那贼人贤士就会自动现其身,只要贤士皆能归附,则王者就无敌天下。
原文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①,则贤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贤人所归,则六条约②。求贤以德,致圣以道。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征。贤人之政,降人以体;贤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会,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落其和。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
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③过制,虽成必败。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
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故早起夜寐,礼之制也;讨贼报仇,义之决也;恻隐之心,仁之发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落其所,道之化也。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于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落,则令弗成;令弗成,则政不正;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
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因此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祐,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疑定惑还,国乃可安。一令逆,则百令失落;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使怨治怨,是谓逆天;使仇治仇,其祸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犯上者尊,贪鄙者富,虽有圣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诛,贪鄙者拘,则化行而众恶消。
明净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不雅观其以是而致焉。致明净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夫贤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虽穷,不处亡国之位;虽贫,不食乱邦之禄。潜名抱道者,时至而动,则极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则建殊绝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扬于后世。
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④,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以是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落水而去世。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落道。
豪杰⑤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杀生在君,国乃可安;四民用灵,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贤臣内,则邪臣外;邪臣内,则贤臣毙。内外失落宜,祸乱传世。大臣疑主⑥,众奸集聚;臣当君尊,高下乃昏,君当臣处,高下失落序。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隽誉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
注释
①昆虫:虫类的统称,这里可理解为世间万物。
②六合:天地四方曰六合。
③造作过剩:造作,指建造宫室园囿之类。过剩:超过标准。
④爝火:火把。
⑤豪杰:汉代利用这个词有时带有贬义。
⑥疑:通“拟”,比拟。
译文
能够拯救天下倾危的,就能得到天下的安宁;能够解除天下忧患的,就能够享受天下的快乐;能够补救国家灾害的,就能够得到天下的幸福。以是,恩典膏泽遍及于百姓,贤人就会归附他;恩典膏泽遍及于万物,贤人就会归附他。贤人归附的,国家就能壮大;贤人归附的,天下就能统一。使贤人归附要用“德”,使贤人归附要用“道”。贤人拜别,国家就要衰弱了;贤人拜别,国家就要混乱了。衰弱是通向危险的阶梯,混乱是即将灭亡的征兆。贤人执政,能使人从行动上服从;贤人执政,能使人从内心里屈服。从行动上服从,便可以开始创业了;从内心里屈服,才可以善始善终。使人从行动上服从靠的是礼教,使人从内心里屈服靠的是乐教。所谓的乐教,并非指金、石、丝、竹,而是使人们喜好自己的家庭,喜好自己的宗族,喜好自己的职业,喜好自己的城邑,喜好国家的政令,喜好社会的伦理道德。这样管理民众,然后再制作音乐来熏陶人们的情操,使社会不失落和谐。以是有道德的君主,是用音乐来使天下快乐;没有道德的君主,是用音乐来使自己快乐。使天下快乐的,国家便会长治久安;使自己快乐的,不久便会亡国。
不修内政而向外扩展的,劳而无功;不事扩展而修明内政的,逸而有成。实施与民生息的政策,民众渴望报答君主,国家就会涌现许多忠义之臣;实施劳民伤财的政策,民众心中抱怨君主,国家就会涌现许多怨恨之民。以是说,热衷于扩展领土的,内政一定荒废;尽力于扩充德行的,国家就会壮大。能保全自己本来所有的。国家就会安然;一味垂涎别人所有的,国家就会残破。统治残酷暴虐,世世代代都要受害。事情超过了限度,纵然一时成功,终极也难免失落败。不正己而君子者其势拂逆,先正己而后君子才顺乎常理。行为拂逆是招致祸乱的根源,顺乎常理是国家安定的关键。
道、德、仁、义、礼,五者是一个整体。道是人们所应遵照的,德是人们从道中所得到的,仁是人们所亲近的,义是人们所应做的,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五条缺一不可。以是,起居有节,是礼的约束;讨贼报仇,是义的决议确定;怜悯之心,是仁的发轫;修己安人,是德的路子;使人均平,各得其所,是道的教养。
君主下达给臣下的指示叫“命”,书写在竹帛上叫“令”,实行命令叫“政”。“命”有失落误,“令”就不能实行。“令”不实行,“政”便涌现偏差。“政”有偏差,治国之“道”便不能通畅。“道”不通畅,奸邪之臣便会得势。奸邪之臣得势,君主的威信就要受到危害。
千里之外去聘请贤人,路途十分迢遥;招引不肖之徒,路途却十分近便。以是,英明的君主总是舍弃身边的不肖之徒,不远千里寻求贤人。因此,能够保全功业,爱崇贤人,臣下也能尽心竭力。弃置一个贤人,浩瀚的贤人便会引退了;奖赏一个恶人,浩瀚的恶人便会蜂拥而至。贤人得到保护,恶人受随处分,就会国家安定,群贤毕至。民众都对政令怀有疑虑,国家就不会得到安定;民众都对政令困惑不解,社会就不会得到管理。疑虑消逝,困惑解除,国家才会安宁。一项政令违背民意,其他政令也就无法实行;一项恶政得到履行,无数恶果也就从此结下。以是,对顺民要履行仁政,对刁民要严加惩处,这样,政令就会畅通无阻,人无怨言了。用民众所怨恨的政令去管理怀有怨气的民众,叫做违背天道;用民众所仇恨的政令去管理怀有仇恨的民众,灾害将无法挽救。管理民众要依赖贫富均平,贫富均平要依赖政治清明。这样,民众便会各得其所,天下也就安宁了。犯上的人反而更加崇高,贪鄙的人反而更加富有,虽然有圣明的君王,也无法把国家管理好。犯上的受到惩办,贪鄙的受到拘禁,这样教养才能得到实行,各种邪恶也就自然销匿。
风致高尚的人,是无法用爵禄收买的;讲究节操的人,是无法用威刑屈从的。以是圣明的君主搜聚贤人,必须根据他们的志趣来吸取。吸取风致高尚的人,要讲究礼节;吸取崇尚节操的人,要依赖道义。这样,贤士便可以聘到,君主的英名也可以保全了。贤人君子能够明察兴衰的根源,通达成败的端倪,洞悉治乱的关键,懂得去就的时节。虽然贫乏,也不会梦想将亡之国的高位:虽然贫苦,也不会苟取衰乱之邦的厚禄。隐姓埋名、肚量胸襟经邦治国之道的人,机遇到来后一旦行动,便可以位极人臣。君主的志向一旦与自己相投,便可以建立绝世的功绩,以是,他的道术高明,美名流芳千古。
圣明的君主进行战役,并不是出于喜好,而是用来诛灭残暴,讨伐叛乱。用正义讨伐不义,就像决开江河之水去淹灭小小的火炬一样,就彷佛在无底的深渊阁下去推下一个风雨飘摇的人一样,其胜利是一定的。圣明的君主之以是安静从容而不急于进兵,是不愿造成过多的职员和物质损耗。战役是不吉祥的东西,天道是厌恶战役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进行战役,才是顺乎天道的。人和天道的关系,就像鱼与水一样。鱼得到水便可以生存,失落去水肯定要去世亡。以是,君子们常常是心存敬畏,一刻也不敢背离天道。
专权跋扈的大臣执政,国君的威望就会受到侵害。生杀大权操于其手,国君的权势也就衰竭了。专权跋扈之臣俯首从命,国家才能长久。生杀之权操于国君,国家才能安定。百姓贫乏,国家就没有储备。百姓富余,国家才会安乐。重用贤臣,奸臣就会被排斥在外了。重用奸臣,贤臣就会被置于去世地了。亲疏不当,祸乱就会延传到后世了。大臣自比君主,众奸就会乘机聚拢。人臣享有君主那样的尊贵,君臣名分就会昏昧不明。君主沦为臣子那样的地位,高下秩序就会颠倒混乱。侵害贤人的,祸患会殃及子孙三代。埋没贤人的,自身就会遭到报应。妒忌贤人的,名誉就不会保全。举荐贤人的,子孙后代都会沾恩于他的善行。以是君子总是热心于推举贤人,因而隽誉显扬。对一个人有好处,对一百个人有害处,民众就会离开城邑。对一个人有好处,对一万个人有害处,全国就会民气离散。除掉一个人而有利于一百个人,人们就会感慕他的恩典膏泽。除掉一个人而有利于一万个人,政治就不会发生混乱了。
图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