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侯府当了十年的丫鬟,只因小姐丢了一支桃花簪,我便被逐出了府。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我本都要放下与侯府的恩恩怨怨。
不承想,一昼夜里,侯府小姐竟狼狈地跪在了我的面前,哀求我收留她。
她被夫家休弃了。天地之大,无处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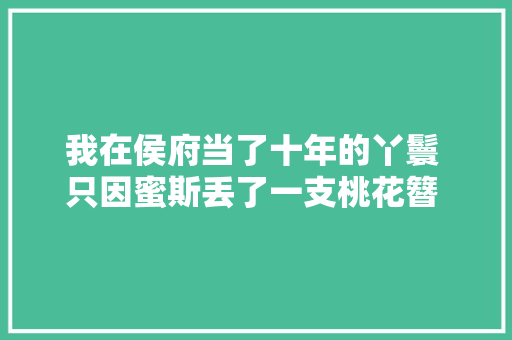
如今,我成了她唯一可投奔的人。
我十一岁那年,我娘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
而在这之前,我爹已经亲手溺死了四个女婴。
我这迟来的弟弟被爹娘寄予厚望,乃至以为寒酸的家境配不上他们金贵的儿子,逼着我卖身为婢,进了定远侯府。
我背着一个小包裹离了家,里面只有两块饼子和一套换洗的衣物。
高门大屋,庭院深深,一待便是十年。
我奉养的主子是侯府的四小姐,比我小六岁。四小姐虽是庶出,但她的生母徐氏有倾城之姿,深得侯爷喜好。她也随着沾了光,衣食用度都是最好的。
那时四小姐年幼,天真烂漫,纯挚到有些发傻。她很依赖我,一口一个「宝儿姐」喊着,常与我同吃同住,令其他丫鬟眼红。
宝儿,是她给我取的名字。我原来的名字叫赵枣夭,音同早夭。我的生身父母一度认为我占了他们生儿子的「份额」,殷切地盼着我赶紧短命。
我在侯府不愁吃穿,还攒了一笔银子。
顺便一提,这些年,我一分钱都没便宜我爹娘。
我爹来闹过。但我买通了府里的一位人高马大的仆人大哥,让他带着棍子把我爹堵在了巷子里,放了一通狠话。
我爹欺软怕硬,被这熊一样的仆人大哥吓破了胆,自此再也没找过我的麻烦,权当我去世了。
在侯府的日子曾经很快乐,令我一度忽略了在这深宅大院中,最经不起考量的便是民气。
四小姐十五岁那年,侯爷给她定了一门亲事,许下了梁尚书家的二公子。
四小姐好奇这位梁二公子的长相,派我打听其行踪许久,终于成功安排了一场「偶遇」。
梁二公子生得仪表堂堂,温和儒雅。与四小姐相见恨晚,互诉衷肠后,送了她一支「桃花簪」。
那簪子不是什么奇异物,我在西巷的首饰铺子里瞧见过。
可少女怀春,无处话相思。四小姐把这「桃花簪」看得比命重,每天握着簪子对镜偷笑。
结果没多久,「桃花簪」不见了,四小姐认定是我偷的,赏了我三十大板。
我被当众褪下裤子,趴在了长凳上。板子实打实地落下,像是用刀背拍打案板上的肉馅,发出一道道闷响。
小姐坐在屋内,侧身对着我,阳光照不进屋内,她的双手藏在桌下的阴影里,抖得厉害。
我俩之间只隔着一道门槛,却如隔天堑。
那天我没认罪,也没求饶,生挨了十几板子后昏了过去。
四小姐到底没忍心打去世我,让仆人们停了手,但此事终归传得不太好听。
末了,侯府的长公子做主,把我逐出了府。四小姐给了我一百两银子,又补偿般地消了我的奴籍,还了我自由身。
我算是因祸得福。带着一身的伤和满满当当的银子,来到了遂州的安然镇,开了个茶楼。
一晃五年过去了,侯府中的各类,已成前尘往事。那些个笑过的、哭过的日子,也逐渐褪了色,恍若黄粱一梦。
然而一天夜里,我刚关了店门,忽然听得门外有人唤我的名字。
扒着门缝一看,白惨惨的月光下,一女子牢牢抱着包裹,浑身湿漉漉的,活像个水鬼。
她高了,瘦了,发髻飞散,衣衫上满是泥点子,再无往昔的风光。
可我仍一眼认出,她便是我看着终年夜的侯府四小姐,卫宁瑶。
2
卫宁瑶似是怕极了,一直东张西望,颤颤巍巍地喊着:「宝儿,宝儿,求你开开门,救救我……」
万籁俱寂,她的声音在空荡的大街上显得格外清晰。我的手搭在房门上,心跳如雷,迟迟没有打开门扉。
我本以为自己早就释然了,然而如今再见卫宁瑶,回顾骤然如潮水涌上心头,压得我喘不过气。
依旧是一人在屋内,一人在屋外,只不过哭的人变成了她。
她很快脱了力,顺着门一点点跪了下来,断断续续地抽泣着,像极了快要断气的猫崽子。
我终于忍不住打开了门,高高在上地看着她,喉间哽着千言万语,却一句都说不出口,只默默让出了一条路,示意她进屋。
烛时间暗,我与她对坐桌前。她仍在颤动,抓着包裹的手用力到指节泛白。良久后,她溘然掩面失落声痛哭,颠三倒四地说:
「宝儿,我被休了,他们都要我去世……」
我从她破碎的话语中拼凑出了原委。
在我离府后的第二年,她如愿嫁给了梁二公子为妻,还带上了身边的丫鬟碧桃当陪嫁。
然而,没多久,碧桃就爬上了梁二公子的床,还有了身孕。卫宁瑶再气恼,也根本挡不住碧桃母凭子贵,一步步被抬成了妾室。
于是她急迫地想要个孩子,喝了一碗又一碗的苦药汤子,软硬兼施地想让梁二公子多留在她的房里。
可她的肚子迟迟没有动静。
时日一长,梁二公子到底厌倦了她,揭下了谦谦君子的假面,露出了贪色薄情的真面孔。一个又一个新人进了府,个个有姿色有手段,哄得梁公子心花怒放,将正妻抛之脑后。
更雪上加霜的是,她的婆母也愈发看不上她。一是她无所出,二是她性子懦弱,镇不了后宅。
婆母将梁二公子沉迷美色,荒废学业全怪在了她身上,隔三岔五就要敲打她。
卫宁瑶忧郁无助,想与人倾诉,却后知后觉地创造,身边早无可用之人。
她的外家,定远侯府,成了她末了的靠山。
然而,半年前,噩耗传来,卫宁瑶的生母徐姨娘与马仆有染,被侯爷捉奸在床。
侯爷大怒之下,命人将其乱棍打去世。
卫宁瑶得闻此事时,徐姨娘已经成了乱葬岗里的一捧枯骨。
紧随其后的,是梁家的一纸休书。
她嫁入梁家五年,临了如丧家之犬被踢出了府门,连细软都没来得及整顿,只带走了几件旧首饰。
定远侯府不要她这个「丢人现眼」的女儿,扔给她一条白绫,让她自行了断。
可她才二十岁啊,她还不想去世。
于是她逃了,用了末了的傍身钱,一起磕磕绊绊地找到了这座小镇,来投奔我。
我听到此,只默默端来了一盘糕点,看她迫不及待地抓起塞进嘴里,终于问出了口:
「为什么是我?」
3
为什么是我呢?
为什么你会来投奔我?为什么你认定我会留下你?
为什么你以为,那支桃花簪是我偷的?
卫宁瑶愣住了,嘴里含着糕点,怎么都咽不下去,眼泪大颗地砸在桌上,声泪俱下地后悔道: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该带着你的,不该是碧桃,该是你的,我怕你跟我抢二郎,才……」
她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当年徐姨娘属意让我当卫宁瑶的陪嫁丫鬟。在徐姨娘看来,我是侯府中为数不多真情实意护着她女儿的人,入了梁家,也会成为卫宁瑶的左膀右臂。
可碧桃趁机嚼舌头,说是我的样子容貌不赖,还岁数大,心眼多,都能哄得挑剔的大夫民气花怒放,全然不顾大夫人跟徐姨娘一向不对付,怕不是要跟主子争宠。
这话在卫宁瑶心里埋下了疙瘩。于是她瞒着我,带上碧桃,又偷偷私会了梁二公子一次,想探探口风。
岂料梁二公子溘然问了句,一贯随着她的那个高个子小丫鬟哪儿去了。
卫宁瑶如临大敌,回到府中茶饭不想,旁边接管不了我与她共侍一夫。
在她看来,我定然是借着传信的机会,跟梁公子眉来眼去了。她一向待我不薄,我却背叛了她,令人不齿。
于是她想了个「高招」,那便是曲解我偷了东西。只要我有了污点,就再也没资格当她的陪嫁丫鬟,登梁家的高门。
「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卫宁瑶泣不成声,「我不知道三十板子会打去世人,我也不知道长兄他会执意将你赶出府去……」
我良久无言,只以为荒诞极了。
不知道,好一个不知道。
我在挨那顿板子的时候,一贯在想究竟是谁陷害了我。我疑惑了很多人,唯独不愿意相信这是卫宁瑶的「杀威棒」。
可等我被逐出侯府,卫宁瑶又追上来塞给我银票以及我的身契时,我就明白了。她早就知道我是冤枉的,她心中有愧。
十年啊,我们朝夕相伴整十年。她是我的主子,我的小姐,也是我的命根子、眼珠子。
我看着她终年夜,把她捧在手心里小心呵护着。她会在我生病时落泪,会在旁人苛责我时义愤填膺。她还会甜滋滋地喊我「宝儿姐」,与我亲密无间地坐在石阶上分一块点心,雷雨夜时抱着我的胳膊甜睡,有什么好东西都会第一个想到我。
她像是上天给我的恩赐,令我无法自抑地从她身上谋寻「家人」的影子。
我曾对她推心置腹,我能绝不犹豫地为她去去世。
结果到头来,她为了一个只见过几面的男人,就弃了我?
你现在叫我怎么办?想着你已经由得很惨了,也算遭了报应了,然后与你重归于好,把你好生请进家来,连续当奉养你的小丫鬟?
怎么可能呢?
我若是这般轻而易举地体谅你了,我这条命就更轻贱了。仿佛我依旧是爹娘嘴里的「赔钱货」、活该早夭的杂草、被弃如敝屣的贱婢,配不上「宝儿」这个名字。
可,不是这样的,也不能是这样。我半生流落,却未曾行差踏错过半步,只图以至心换至心。
我不该被如此对待。
4
我只留了卫宁瑶一晚,天亮后给了她一些银子,让她自己讨活路去。
这几年不太平,陛下屡屡削藩,惹得各地频起叛乱。本日这个侯反了,来日诰日那个王又开始招兵买马了。
我为了打点各路英雄豪杰花光了积蓄,其实拿不出太多钱了。但倘若卫宁瑶能省着点花,找个浆洗之类的活,足够她过上大半年。
卫宁瑶抹着眼泪接下银子,形单影只地拜别,时时转头望一眼,见我始终没有挽留她的意思,落寞地加快了脚步,消逝在街口。
这时,我店里的伙计来了,一边擦着桌子,一边好奇地问:「掌柜的,那姑娘是您什么人啊?瞅着不像咱安然镇上的。」
我轻描淡写地说:「是我远房表妹,我与她并不熟络,给点钱丁宁了。」
实在我有些在意卫宁瑶是怎么找到我的,毕竟我只是在很多年前,无意中与她提了一嘴安然镇。
安然镇是我祖母的老家。幼时,我娘没有奶水,我爹又嫌我是个女儿,乃至不愿多看我一眼。是祖母用一勺勺米糊把我喂大,将我搂在怀里,哼着歌哄我入睡。
祖母是远嫁到北方的。她说,她出生在一个叫「安然镇」的南方小镇子上。安然镇原来很穷,但自打它被划进了武威将军沈成荫的食邑,就行了大运。
武威将军亲自带着百姓们种茶叶、修河渠,令家家户户足食丰衣。祖母年轻时最喜好做的事便是跟一群采茶女挎着茶篓,踏着歌,在山明水秀间取下染满晨露的新芽。
祖母操劳了一辈子,终极积劳成疾,早早去了,临了仍念叨着这回不去的故乡。
于是,我决定替她回到这里,开起茶楼。如若世上真有魂灵,但望清茗为魂引,故人入我梦。
卫宁瑶的到来像是吹落茶水中的树叶,我将它挑出,这事就可以掀篇了。
可我心里总忽忽悠悠的,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账算错了好几次,末了灰心地把算盘一扔,喝点小酒早早歇下了。
哪知灾患丛生,第二天一大早,我刚出门伸了个
须臾,马车停在了茶楼门前,一位身着青衫的公子下了马车,待我看清那公子脸庞,顿时如遭雷击,僵在了原地。
是定远侯府的长公子,卫元鸿。
四目相对,我已避无可避,不由紧张到额角冒汗。卫元鸿却沉着如初,不动声色地打量了我一瞬,轻声道:
「掌柜的,要一壶明前茶,一颗软松糖。」
我硬着头皮将他迎入屋中,张罗伙计赶紧去买软松糖。
卫元鸿靠窗坐定,摇着折扇,眸光始终钉在我的身上,抿唇似笑非笑。待我忙不迭地将茶水端了上来,他忽然问我:
「宝儿姐,你见过宁瑶了吧?」
5
我手指一抖,强稳下心神,为他斟茶:「四小姐吗?多年未见了。」
卫元鸿却笑出声来,语气颇为无奈:「你果真还是如此……罢了。」
说着他拿出一锭硕大的银子放在桌边,「拜托了。」
我看着那闪闪发光的银锭,顿感一个脑袋大成了俩。心想,这对卫氏兄妹可真是盯着我一人祸害啊!
我招谁惹谁了?
卫元鸿比我小两岁,可他天生聪慧,性子沉稳,提及话来慢条斯理,反倒像是我的长辈。
直到有一天,出了一桩「小事」。
那年,京都暴发了时疫,我为了防患于未然,煮了一大锅能散寒强体的草药汤,让卫宁瑶喝。
她嫌苦,被我追得满府跑,便是不喝,适值一脑袋撞上了有时途经的卫元鸿,吵着让他「评评理」。
哪知卫元鸿为了教导卫宁瑶忠言逆耳,直接拿过药碗,豪迈地一饮而尽。
卫宁瑶木鸡之呆,只能学着他的样子,又盛了一碗猛地灌进嘴里,苦得跺脚掉眼泪。
我急忙拿出一颗软松糖塞进她嘴里。这是她最喜好的糖果,我的袖子里时常备着几颗,一旦她闹小脾气,就拿糖果哄她愉快。
卫宁瑶吃了糖,终于伸展了眉头。我刚想夸她几句,就听卫元鸿溘然颤声说:
「宝儿……也给我一颗糖……」
然后不等我反应过来,他扶着树哇地吐了一地。
许是由于被我看到了尴尬的样子,从那时起,这位卫大公子在我面前不装了,时常随着卫宁瑶一起喊我「宝儿姐」,狐狸似的眯着眼,笑看我羞红脸。
可当初也是他执意要将我逐出府。哪怕大夫人都于心不忍,说我在侯府待了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依然命人把我扔了出去。
我其实想不通自己何时得罪了他。但不得不说,若不是他将我撵出府,我哪能过上如今的清闲日子?
「这银子我不能收。」我断然谢绝,「卫大人,无功不受禄。」
卫元鸿瞩目着我,眸光炯炯透着一抹怀念,令我浑身不清闲。
良久,他低叹一声:「罢了,能见到你,我就知足了。等我忙完公务,再来与你切磋……一件要事。」
说罢他起身拜别,桌上的茶分毫没动,杯中的茶叶随着屋外的马车远去声微微扭捏。
我发了好一阵子的呆,直到买糖的伙计回来,才意识到刚刚不是在做梦。
难不成,当初他是故意放我走的?
我坐下,就着茶水吃着软松糖,心想,若真是如此,我还欠卫元鸿一声感激。
哪知我这厢还没感慨完,就听我那伙计溘然说了句:
「哦对了,掌柜的,我刚买糖的时候,瞥见你表妹了!
她不知怎的跟布店的何掌柜起了争执,被打了好大一个嘴巴子,坐在地上嗷嗷哭。啧,可怜见的。」
我顿时被噎得咳嗽不止,好悬没丢了老命。
不是,这卫宁瑶刚来安然镇一天,就被人打了?
她是一种很随意马虎晦气的大小姐吗?
6
我起誓我只是好奇,想去凑个热闹。
等我拨开人群来到布店门前,布店的女掌柜正指着卫宁瑶骂得吐沫星子横飞。
「臭不要脸的狐媚子!
怕不是从哪个窑子出来的吧?跑我们安然镇勾引男人来了!
」
卫宁瑶坐在地上,脸上顶着个红彤彤的巴掌印,哭得梨花带雨,半天只憋出一句:「你,你含血喷人!
」
这女掌柜叫何莲,确实不是个讲理的人。她生得高大,干起活来是一把妙手。可惜天公不作美,她的右脸上有一大块青色胎记,令她成了许多男子和顽童口中的「青面夜叉」。
何掌柜的夫君是入赘的,名叫刘大。他俩只有一个女儿,随了何掌柜的姓,叫何小花,今年十二岁,被何掌柜宠若掌上明珠,早早送进了学堂。
然而,刘大却不是个循分的。他身材短小粗胖,平日里吊儿郎当还好色,瞥见个女的,眼珠子就黏在了人家身上,浑身高下透着邋遢。
可就这么个人厌狗嫌的男人,在何掌柜眼里竟成了「天仙」。她固执地以为,都是表面的女人在勾引她家夫君,跟只护崽的老母鸡似的,扑棱着翅膀敌视所有女子。
久而久之,没几个女人敢去她家布店买东西了。布店买卖不好,何掌柜就更加暴躁,街边的母狗都得被她踹一脚。
也便是说,卫宁瑶这是在全体镇子上,精确地找到了一家最不该沾边的,惹了一身骚。
何掌柜越骂越起劲,仿佛卫宁瑶真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然而我听了一耳朵,发觉卫宁瑶只是在布店门前站得久了些,问刘大布店招不招短工罢了。
围不雅观的百姓们议论纷纭,不乏有人露骨地对卫宁瑶评头论足。卫宁瑶无措地左顾右盼,状似想找人替她做证,神采惶恐。那些个吐沫星子像是一把刀,活剐了她这自幼被教导三从四德的大家闺秀。
终极,她绝望地一跃而起,冲着不远处的木头桩子一头撞了过去!
我看不下去了,挡在木头桩子前按住了她的脑袋,骂道:「不争气的蠢东西,想去世去世远些,别溅我一身血!
」
她猛地抬开始来,惨白的小脸迅速涨红,咧开嘴哇地哭了出来:「宝儿姐!
她,她……」
「闭嘴!
」我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哭哭哭,我的财气都要被你哭没了!
我怎么教的你?你全忘了?嗯?」
卫宁瑶当心翼翼地捂住了嘴,憋得一抽一抽。
我撸起袖子,冲着那正叉腰使横的何掌柜,一个箭步,抡圆胳膊,照着何掌柜那半张好脸扇了下去!
何掌柜被我打得「啊」的一声躺在了地上,左酡颜右脸青,当真是姹紫嫣红。
我活动了一下手腕,瞥向看傻了的卫宁瑶:「我再教你一次,这回你给我记住了。这世上没什么比活着更要紧的。倘若真活不下去了,也不能空手走。人来世上一趟,不是为了亏损的。先把仇人宰了,再到阎王爷那儿讨公道去!
」
尔后我清清嗓子,气运丹田,先指着缩在人群里的刘大骂道,「呸!
就你这种烂泥地里的矮倭瓜,歪嘴破痰盂,盛了二两尿倒是洒出来照照,别瞥见个女的就淌着哈喇子凑近乎,你配吗?!
」
然后对着跳起来想反击的何掌柜又是一巴掌,「瞎眼瞎心的傻老娘们儿,也就你把这歪瓜裂枣当成个宝!
天底下男人去世光啦?没男人活不了啦?养他有个屁用,养条狗还能看家护院呢!
养他只能丢人现眼!
」
我可不是想替卫宁瑶出头,而是忍何掌柜和刘大许久了。
前年我去他家布店买布,刘大竟趁着何掌柜不在,问我独守空房寂不寂寞,还想摸我的手,气得我抬脚踹得他满地滚。
哪知刘大事后倒打一耙,跟何掌柜说是我勾引他。何掌柜这没脑筋的跑来砸我的茶楼,我们两家的梁子也就这么结下了。
以是,择日不如撞日,来都来了,总得骂爽了再说!
7
我跟何掌柜打得昏天地暗,飞沙走石,无人敢拉架。刘大那个大窝囊废当起了缩头乌龟,而卫宁瑶这个小窝囊废只知捂着心口悲戚地喊:
「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宝儿姐姐……」
终极,这场战役以我揪下了何掌柜的一撮头发,她扯烂了我的袖子而告终。
衣服随时能重做,头发可得养上一年半载。
是我赢了!
我趾高气扬地得胜而归,卫宁瑶在我身后小步紧随着,一起跟到茶楼门前。
我诧异地转头问她:「你随着我做什么?」
她的大眼睛忽闪着,满是谄媚的意味:「赵掌柜,你缺不缺长工?我不要工钱,管吃住就行……」
我被气笑了:「你这种养尊处优的大小姐能做什么?」
她的眼眶又红了,可怜巴巴地哀求道:「宝儿姐,你行行好,留下我吧……我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又得罪了人,我怕他们陵暴我……宝儿姐,我给你当牛作马都行……」
她哭得我脑仁疼,堵住了所有谢绝的话。
我忽然想起了许多年前,侯府里养的一只猫。那是只黄色的小猫崽,被母猫抛弃在了侯府附近的巷子里,适值被散学归家的卫元鸿瞧见,抱回府养在了书房里。
岂料有一天,侯爷也不知发什么邪火,非说卫元鸿养猫是玩物丧志,趁他不在家,着人把猫丢了出去。
卫元鸿回来后也没多说什么。可有一次,我出门买东西时,无意中瞧见他在附近的小胡同里翻开杂物,小声「喵喵」叫着找猫。一举头与我对上了视线,顿时尴尬到涨红了脸。
可惜,他究竟没能找回小猫。当年冬日,我在侯府的后巷子里看到了小猫的尸体,它瘦骨嶙峋,身上还有被野狗啃食的痕迹。
我偷偷把小猫的尸体抱了回来。卫元鸿在书房外的大树下挖了个坑,把小猫葬了,还陪葬了一个藤球和一把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