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岭南画派“根正苗红”的传承者——父亲梁占峰为岭南画派花鸟画名家,父亲的老师黎葛民是高剑父、陈树人的同学好友。1981年她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又担当岭南画派纪念馆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
但她的作品与父亲梁占峰、师公黎葛民,乃至于其他岭南画派名家的面貌皆迥异,自有一种厚重、高华之美。归根到底,她传承的是岭南画派的改造精神,在“折中中西、交融古今”中,她特殊看重“以中为本”“以今为魂”。因此,早在1984年,她那幅让人线人一新的中国画作品《涛声》就夺得了第六届全国美展铜奖。之后,《桑田》又得到了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
近日,“美自然——梁如洁中国字画作品展”在佛山市石景宜刘紫英夫妻文化艺术馆举行。借此机会,深入理解了梁如洁的艺术进程。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 江粤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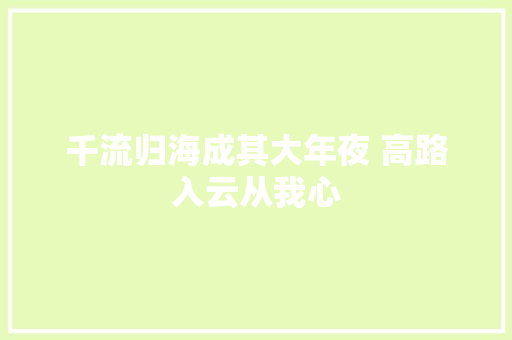
熔铸百家成自家面孔
由于家学渊源,梁如洁很早就知道怎么拿笔作花鸟画。在广州宝贤大街上小学,4年级时她成为学校的宣扬委员,卖力出墙报等文艺事情。但父亲并没有哀求她专注于画画,而是让她多读书,多写字,多聆听一些前辈们的互换。
“特殊是黎葛民师长西席,对我父亲就像对儿子一样。20世纪50年代我常常到他家去玩,常常听他和父亲发言,这种熏陶对我影响非常大,‘岭南画派’的变革精神早早就扎根在我的心中。”后来,梁如洁还曾主编过一本《黎葛民诗字画集》,对黎葛民生平的创作进行了梳理。
家里曾收留过父亲的一位文学老师。这位先生长西席长于刻蜡版,梁如洁每天放学回家都看得津津有味,并很快学会了刻宋体字。这让她1969年到肇庆市高要县插队时,顺利地当上了队里的宣扬员,也使得她后来有机会到县文化馆学习,得到了广州美术学院要来招生的信息,顺利报名。“由于有美术功底和文化根本,又有黎葛民师长西席的推举,1972年,我顺利回到广州上大学。”
在广州美院,梁如洁更是打下了坚实的学院派绘画根本,不仅学习了国画,还学了油画、水彩。毕业后,她被分配到肇庆影剧院当美工,1978年,她又如愿考取了杨之光师长西席的研究生,回到美院学习人物画,并得以留校在师范系任教。“这个系后来改为教诲系,现在叫教诲学院。我们当时属于创系的‘开荒牛’。我是教研组长,要安排各门课程。当时系里没有专业的花鸟画老师,我只好自己挺身而上。虽然过去也画过不少花鸟画,但毕竟研究生阶段紧张随着杨之光老师研究人物画,我还是要‘补课’——到图书馆临摹齐白石、吴昌硕、潘天寿等名家的作品,边教边学。”这些大师们的营养,逐渐渗入到梁如洁的作品中。
同时,教诲系有国画教研组、水彩教研组、工艺设计教研组,可谓最综合的系,梁如洁又是一个在审美上兼容并包的人,无论油画、版画、设计、拍照,她都喜好学习理解,并自然而然地接管到她的创作中。因此,她的花鸟画作品,迅速融入了版画觉得、平面构成的成分,让人面前一亮。
一开始便先声夺人的是创作于1984年的《涛声》。画面上,厚实刚劲的礁石组成强有力的主体,其上海鸥密密匝匝排列组合,却又灵动自然,如在侧耳聆听自然的潮汐、时期的回响,其内涵正与激荡南粤大地的改革浪潮相吻合。因此,这件作品成功入选当年的全国美展,并得到铜奖,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岭南新花鸟哲思为底
这创新的能力,来源于梁如洁综合的技法功底,更来源于她对艺术的认知,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她在传统文化上的深厚积淀。“父亲很早请教会我,画画是表达自己对天下、对万物、对生活的一种感悟,不是为了技法而技法。因此,虽然每一张画我都会用不同的技法,险些从不重复,但这都不是刻意为之的。只要有发自至心的深刻感悟,自然会竭尽所能去表现好主题。”
譬如,20世纪80年代末,梁如洁又创作了《桑田》,摘取了全国美展银奖。当时她带学生到南海、番禺、顺德一带写生。作为鱼米之乡,这里的桑基鱼塘很出名。在路基上,梁如洁看到了桑树萌芽,鲜嫩无比,她满心欢畅地走到桑田里面去。这才创造,桑基的土里面有很多白色的小贝壳,让她很惊奇。“我站起来眺望远方,开始思虑:贝壳是海里来的,广东一贯有围海造田的历史,几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生息,逐渐地大海就变成了桑田……我想了很多,才动笔作画。”这件作品,梁如洁将其命名为简洁的《桑田》二字,然后题上“在广东沿海的桑地上,不难创造那一个个带有历史印记的小贝壳”的素朴笔墨,并采取平面构成理念,将桑田设计成一排一排的海浪,使得画面更有冲击力。可以说,《桑田》构思很动人,内容又是从生活中来的,在平凡中彰显深刻,在全国美展中脱颖而出是一定的。
再后来,她的《新绿》也在全国美展中获奖,同样因此小见大,意韵悠长。这样的提取能力,则要归功于梁如洁深厚的国学功底,尤其是她对老子学说、《二十四诗品》等传统哲学、美学的钟爱。
以是,她画《跋涉者》,画的是一头劈面走来的大象,壮硕的身躯充满了勇往直前的力量。“这可以说是一种自况吧,在艺术道路上,我一贯都是一个跋涉者。”梁如洁笑道。
她画《大地》,也是为了见告儿子,画动物要有所寄托。那画面上的一对狮子卧在大地上,像两座山峰一样沉稳,目光武断,眺望远方。画上还题跋:“天地玄黄、日月盈虚,寒来暑往,阴阳化育。”更让人觉得到无限希望。
恰如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广州美术学院中国近当代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所说的,梁如洁的花鸟画是南方的,是具有岭南气质的新花鸟画。“她的作品虽大都起于对人生、社会、自然的触动和感悟,但进入创作却历经反复考虑推敲,务求意境隽永内涵深厚。她近年所作《木棉颂组画》《岭南佳果组画》《瑶池仙雀下春园·满园春》等,更明显表示了这一特色。明乎此,便可明白何以梁如洁的作品若隐若现透着某种哲理化内蕴。”
以书入画与以画入书
梁如洁在绘画上所达到的高度,还跟她的书法功底密不可分。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陶咏白曾谈到,梁如洁特有的“宁方勿圆”的个性化笔意形象,那刚毅刚烈、遒健的用笔,把碑学中“南帖为圆笔之宗,北碑为方笔之祖”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使画面具有雕塑感。“她画的果实或花朵,如她的柿子是方形的,不是圆形的,这表示了她的笔墨符号形成了个性化的措辞特色。”
从幼年开始拿起羊毫写字,几十年间,梁如洁在书法上的熬炼就一贯没断过:“最初临帖,父亲说颜肥柳瘦,女孩子先从柳公权开始吧,比较壮实。后来又打仗了各种石本,甲骨文、钟鼎文,什么都写。读到喜好的画论、书论,我就会选择得当的书体去抄录下来,这既是书法练习,对我的绘画也非常有帮助。”
在美术理论家、书法家孙克看来,梁如洁临习石本不仅根本好,而且很有悟性。“梁如洁临写的《石鼓文》不是还是描绘,只求形似,反之,她看重的是笔画的气势精神,厚重绵密,元气充足。《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也都下过功夫,逐渐形成她的书法金石阳刚之气浓厚。”
我们每每都说“以书入画”,而对付字画双修的梁如洁而言,也不妨说“以画入书”。正如她自己所强调的:“我是一名画家,画家最敏感的便是造型。以是我对各种书体的造型都非常敏感,临过的石本不会忘。在书法方面,我会非常看重构成、摆布、节奏。”
梁如洁曾以她个性化的笔墨自书一联曰:“千流归大海,高路入云端。”她在艺术道路上的探求,正可谓聚千流而成自我之大,出己心而得自我之高。这确乎也表示了岭南画派的精神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