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清晨。”清晨的韶光很宝贵。早上是人一天精力最兴旺的时候,人经由一个晚上的安歇后,大脑供氧充足,大脑这个时候的影象力是最好的!思维反应也够快,更助于巩固影象。
读书真是好习气,一定要坚持下去。
【钱】
不知道“抓周”这风尚是否遍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彷佛是个小金镑薯。我姑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彷佛我就很喜好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创造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六根清净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立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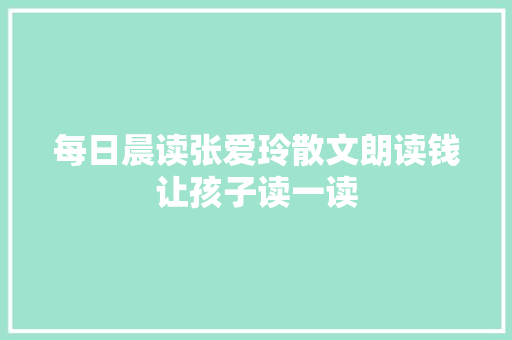
我喜好钱,由于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履历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由于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七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气,也就没有希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样平常,立在街沿上,期待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我没办法找他,由于总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顾中唯一的豪华的觉得。
平生第一次赢利,是在中学时期,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急速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绪。对付我,钱便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以为是应该为我所有的,由于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眠思梦想地操持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楚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备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空手发迹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以为个中的苍凉。
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十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负气罢?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大概由于这于我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够忘却小时候若何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西席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随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由于我一贯是用一种罗曼谛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俏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打仗,我四岁的时候她就放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以为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利令智昏磨难着,那些零散的尴尬,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苦虽苦一点,我喜好我的职业。“学成文身手,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用饭的,现在环境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店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至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宁愿要一个抽象的。
赚的钱虽不足用,我也还囤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总是没有销路的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由于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向五年前的回顾里去找寻灵感。于是我省下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囤到现在,在市情上瞥见有乔琪绒涌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便是这样充满了抵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罢?然而最近,一个卖菜的老头称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下子。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觉得。自己创造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彷佛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小墨留给大家末了的话:
做一个快乐的人,
对自己感到快乐,
展现真实的自我,
无论是对着镜子还是对着你的爱人。
愿你我心中有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