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归。
来入门,
怅欲悲。
盎中无斗米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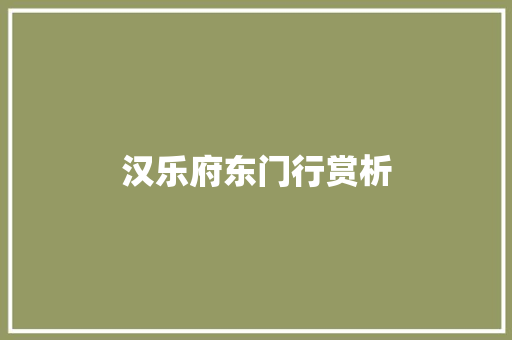
还视架上无悬衣。
舍中儿母牵衣啼:
“他家但愿富贵,
贱妾与君共哺糜。
上用仓浪天故,
下当用此黄口儿。
今非!
”
“咄!
行!
吾去为迟!
白发时下难久居!
”
这首诗的背景是东汉末年。当时,朝政腐败,宦官当权,富朱紫家都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而贫苦的百姓(可以是农人也可是城市贫民)却不得餍饫,饥荒之年乃至会发生人吃人的惨剧。贫苦的百姓被逼得走上反抗道路,时有暴动发生。《东门行》里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这是一首汉乐府民歌,同样不知作者姓名。其内容是写一位贫民被无衣无食的绝境所迫,不得不拔剑走上反抗道路。
还是阐明诗中的部分词语:1.东门行,乐府古辞名。2.东门,主人公所居之处的东城门。3.来入门,离开又回转家门。4.盎(àng),大肚子小口的陶器。5.还视,看看周围;还,即环,环抱。6.儿母,指孩子的母亲,即主人公的妻子。7.哺糜(bǔmí),吃粥。8.用,为了。9.仓浪天,仓浪,青色;仓浪天,即蓝色的天。10.今非,指丈夫这种冒险行为不对。11.咄(duō),指丈夫谢绝妻子的劝告而发出的斥责声。12.吾去为迟,我已经去晚了。13.白发时下:头上的白发时时地脱落。下,脱落。
现在,试用更好懂的口语翻译这首诗。
我刚才出东门后,
本来就没打算返回;
可我忍不住又进门看看,
结果更使我伤心而悲哀!
我环顾屋里:
米罐中没有粮食可以充饥,
衣架上没有衣服用来遮体。
于是,我拔剑再离开家门,
孩子的母亲拉住我的衣服哭啼。
她说:
“别人家只愿富贵,
我却甘心和你吃粥喝稀。
上有蓝色的天空,
下熟年幼的孩子。
你现在这样不对!
”
我愤怒地喝道:
“咄!
我去了!
现在走已经是迟!
我白发都脱落了,
这种苦日子,
实在难以熬下去!
”
末了,欣赏这首诗。
一.长于借助诗的形式写故事。
读了前面的口语翻译,可以看出《东门行》实在是在讲一个故事。而这种讲述,可以想象成采访的口气,也可以想象为故事中人物自己的口气。
如果是的口气,这个故事可以这样讲:有一个贫民由于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就拔剑要走上反抗的道路。可他的妻子哭着不让他这样,她拉住丈夫的衣襟哭着说道:“别人有钱就让他们有去吧,而我哪怕再苦的日子,也甘心与你在一起过下去!
你千万不能去走冒险的路啊!
”听了妻子的话,他却愤怒地甩掉她的手,狠狠地说:“你别说了!
我早就该当这样了,现在去都迟了!
苦日子把我的头发都折磨白了,一根根地掉了下来。我怎么还能再等下去?”
如果用故事中人物自己的口气,这个故事便是另一种讲法了:我家一贯过着无衣无食的苦日子,我实在忍受不了,决心拔剑冒险去!我的妻子看到我真的要走,就牢牢拉住我的衣襟哭喊着说:“你不能这样啊!
别人家怎么富贵,咱不去管;我们的日子再苦,我也甘心同你熬下去!
”我知道她非常痛楚,就伪装生气的样子,摆脱她的手,喝道:“咄!
闭嘴!
我受够了!
我的头发早白了,而且掉得不剩几根了。这日子还要熬到什么时候啊?”
这个故事,即利用最短的话讲起来也得不少字吧?可作者仅用了70多个字就写得比讲故事还要详细生动,还要有个性特色;而且既有阐述与描写,又有对话和表情。该当承认,其写作艺术比之诗文里手,也绝不逊色。
二.长于利用多种手腕揭示人物的生理活动与当时社会的阴郁。
一是利用富有表现力的动词。如“出”“顾”“入”“视”“拔”“去”这几个动词连用,可以看出,诗中的主人公先是出了门要走,本来是想不再回顾的,可是走了几步,又进得门来。这一“出”,一“顾”,一“入”,就生动地表现了主人公采纳铤而走险的无奈与犹豫。读之令人泪下!
后面接着又用了“视”“拔”“去”3个动词,解释当他又一次看到无衣无食、家徒四壁的惨状时,就不再犹豫,于是,表现出他毅然决然拔剑而去的决心!
至于后面所用的“牵”与“啼”两个动词,其笔力重抵千斤:不仅写出他们夫妻间深似海的恩爱,也写出了当时社会中底层百姓的痛楚生活,从而戳穿了统治者不顾民生的恶行。
二是长于利用比拟的修辞手腕。共有两处比拟:一处是主人公自己前后表现的比拟;另一处是主人公的表现与其妻子的表现的比拟。
先看第一处比拟。主人公开始是“出东门,不顾归”,这就见告读者,他原来是下了决心不打算归来的,但又不得不归来,解释他还是有所顾念的,他顾念确当然是妻子与儿女了。便是这个前后抵牾的行为向读者展现了主人公极其繁芜的生理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他是若何腾腾地走出去,但没走几步,却又呆立在门外不动了;此时他溘然犹豫了,不想走了,于是他又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可是,为什么末了又“拔剑东门去”呢?缘故原由不是他柔嫩寡断,而是“盎中无斗米储”与“架上无悬衣”的悲惨现实使他不得不末了下定决心,竟不顾妻子的牵衣而啼,毅然决然地离家而去。
至于另一处主人公的表现与其妻子的表现的比拟,其所揭示的人物的生理活动就更加繁芜了;这里不再赘述,请读者逐步体会。
三.长于利用“词语跳跃”与“戛然而止”的艺术手腕,为读者留有想象的余地。
1.“出东门,不顾归”与“来入门,怅欲悲”之间便是一个跳跃:既然出去不回来,怎么又进了门呢?这一跳跃,就给读者广阔的想象余地。
2.“白发时下难久居!
”这是主人公回答妻子的末了一句话。诗写到这里戛然而止;至于气的结局如何,作者只字未写。我们读过《陌上桑》,所用的手腕与这首诗完备相同。人们每每以英国作家莫泊桑的《项链》为例,解释文学作品不写结局的奥妙。可很少有人把稳到,这种写法我国的古人早已利用得出神入化了!
相信,有多少读者,这首诗的结局就会有多少。
总之,这首诗由于利用了“词语跳跃”与“戛然而止”的艺术手腕,结果给读者留下的空间太大太大了,这空间之大,至少可以容得下一篇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