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出自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句的意思是说,在朝廷做官就应该心系百姓;处在僻远的江湖间也不能忘却关注国家安危。当然,这句对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来说,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的领导干部无论处在何种位置,何种情状,都要忧国忧民,以公民为中央,有所作为。
一、忠臣范仲淹:万家忧乐到心头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被贬谪到邓州时所写。范仲淹应朋友滕子京之请,驰骋想象,熔铸万千忧乐于笔端,挥毫写就这篇千古名文,传诵天下。范仲淹在邓州关注民生,写诗云:“南阳风尚常苦耕,太守忧民敢不诚”。他在《邓州谢上表》中向天子表态道:“敢不孜孜于善,战战厥心,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上酬圣造,少罄臣诚。”后来,范仲淹因政绩突出,受百姓爱戴而蝉联邓州。可见其忠君与忠国爱民之心是同等的。
诗有诗眼,文有文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好是《岳阳楼记》的“文眼”所在。这是古代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风貌的最佳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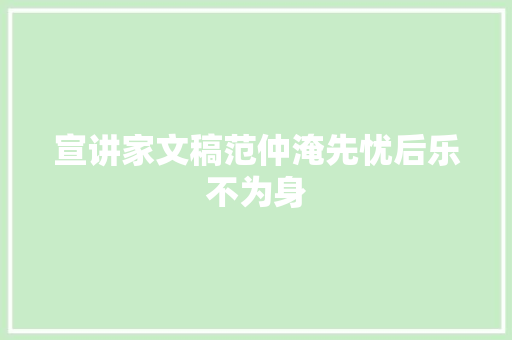
一样平常而言,类似于《岳阳楼记》的这种文章,不免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或者抒发“贫士失落职而志不平”“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之类的失落意心境。但让我们来看看范仲淹的格局与肚量胸襟。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开篇写道:“予不雅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候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不雅观也,古人之述备矣。”到这里,范仲淹奥妙打住,没有对岳阳楼进行过多描述。接着,他笔锋一转,迅即写人:“但是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再今后先是展示苦景:“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峰潜形,商旅弗成,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继而陪衬乐景,且看:“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高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拍浮,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登斯楼也,则有赏心悦目,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乐陶陶者矣。”这一悲一喜,揭示了迁客骚人对景生情、情随景迁、心为物役的心境。
一样平常的文人到此就止笔勾留了,至多再抒发一点个人感慨而已。范仲淹不然,他要卒章显志,探求自己与非凡的古仁人(即先贤大德之人)崇高精神境界的高度认同。于是,就有了以下这段千古不朽的笔墨:“嗟夫!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但是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噫!
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的言下之意是他所认同的“古仁人”不同于一样平常的迁客骚人。他们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为外物所旁边,犹如屈原对渔夫所言那样,“全球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楚辞·渔父》。古仁人之以是能够做到这样,是由于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落,忠君爱国、肚量胸襟天下,信念高远而武断。他们高居庙堂,身在朝廷,能够忧民之所忧,以百姓之心为心;他们一时被诬陷遭贬谪,却仍旧为朝政而忧虑。以是,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的胸襟与境界,何等开阔!
据记载,范仲淹出身孤贫,经由寒窗苦读,很早就为自己的人生进行了方案,“或为良相,或为良医”,要为天下人做事。欧阳修夸奖他“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可见,范仲淹“先忧后乐”精神,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其毕生追求的空想信念。宋儒朱熹评价说:“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
作者:梅敬忠 中共中心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本文节选自宣讲家网文稿《 梅敬忠:范仲淹“先忧后乐不为身” 》
查看完全内容请到宣讲家网(WWW.71.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