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王安石的《元日》诗:“炮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阵阵轰鸣的炮竹声中,旧的一年已经由去;和暖的东风吹来了新年,人们欢快地畅饮着新酿的屠苏酒。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他们都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桃符。
熊柏畦《宋八大家绝句选》:“这首诗既是句句写新年,也是句句写新法。两者结合得紧密桔切,天衣无缝,把元日的温暖光明景象,写得风起云涌,歌颂和肯定了实施新法的胜利和美好出息。”姚奠中《唐宋绝句选注析》:“用一‘换’字,即写出当时的风尚习气,更为读者开辟了新的诗意。揭示出新的代替旧的,进步的代替掉队的,历史发展的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
王安石这首诗充满欢畅和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是由于他当时正出任宰相,实行新法。王安石是北宋期间著名的改革家,他在任期间,正如面古人们把新的桃符代替旧的一样,拔除旧政,施行新政。王安石对新政充满信心,以是反响到诗中就分外爽朗。这首诗,正是赞颂新事物的出身犹如“东风送暖”那样充满活气;“曈曈日”照着“千门万户”,这不是平常的太阳,而是新生活的开始,变法带给百姓的是一片光明。结尾一句“总把新桃换旧符”,表现了墨客对变法胜利和公民生活改进的欣慰喜悦之情。个中含有深刻哲理,指出新生事物总是要取代没落事物的这一规律。
王安石的这首诗虽然谈的是改革给社会和百姓带来的变革,实在也揭示了过春节的真正意义,那便是要弃旧图新,以新的精神面貌来欢迎新的一年。在王安石看来,新的代替旧的,进步的代替掉队的,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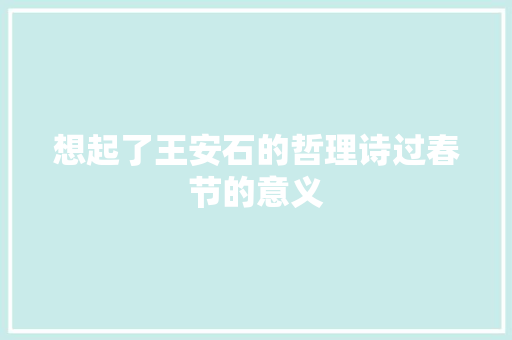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之以是安排在冬末春始,绝不是有时的。它见告人们,劳累了一年之后,经由一个冬天的安歇,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但新的一年不能只是重复上一年,必须要有新的改变,新的气候,新的发展。我们看看那些动植物,虽然也是“当春乃发生”,也有达尔文所说的进化,但它们的变革是非常缓慢的,而且多是量的重复。人则不一样,人的思想可以发生质的变革,社会通过改革也可以“新桃换旧符”。
改变也好,改革也好,创新也好,不可能没有阻力,不可能一点问题不出,不可能达到所有人的满意,怎么办?难道就不做了吗?鲁迅夸奖,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冒死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世间最难之事,非知,乃行也。”诚如马克思所言,对哲学家们来说,从思想天下降到现实天下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商鞅变法也好,王安石变法也好,戊戌变法也好,虽然都失落败了,但改革者的英名将永垂青史,他们或多或少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或给后人留下了可供借鉴的履历教训,比那些躺着不动、阻碍历史发展的人要强一百倍。(胡耀邦语)
我还想起了王安石的另一首哲理诗《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登飞来峰》本来只是一首登高诗,王安石没有过多地写登高之景,落笔重点在自己登临高处的所触所感,并且以一种极为诚挚的口吻见告了众人“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人生哲理,表现一个政治变革家拨云见日、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和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孔,只缘身在此山中”、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有异曲同工之妙,乃至比它们更具改革气势。
王安石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节制了精确的不雅观点和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征象看到实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以是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由于没有全面、客不雅观、精确的不雅观察、认识事物。
杜甫《望月》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达了墨客虽考场失落意,仍充满不怕困难,俯视统统的年夜志壮志和豪迈气概;“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表现的是墨客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碰着重重障碍的情形下,以武断果断的意志坚持贯彻实行新法。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不畏困难、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
从“为有暗香来”的《梅花》,到“东风送暖入屠苏”的《元日》,有“东风又绿江南岸”的《泊船瓜洲》,还有散文《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等……都是王安石的哲理诗文,表示了王安石的哲学思维水平是很高的,给人的启示也非常之深,真不愧是苏轼的恩师。
《礼记·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诚然如果有一天能够得到新的进步,就要一天一天都有新的进步,而且还要再连续每天有新的进步。。《康诰》也说:“勉励人弃旧图新。”《诗经》说:“周朝虽然是旧的国家,但却禀受了新的定命。”以是,君子无处不追求完善。这大概便是过春节对人的哀求吧?!
2024年2月 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