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这是宋代墨客翁森在《四季读书乐》中描述的意境。另有一首美国作家吉恩·福勒的诗是这样写的:“由于书本不仅是书本,它们是生活/是过去时期的中央——/是人们事情、生与去世的缘故原由/是他们生命的实质与精髓。”这两首诗都可视为难刁难书本一往情深的告白。不知诸君读后是引为同道、无动于衷、莫名其妙、嗤之以鼻,还是不以为然?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有这样一群人,书痴、书虫、书蠹、书迷、藏书家、猎书人,这一系列称谓都是在为他们画像,书在他们眼中绝不仅仅是一件印刷品,对他们来说,拥有一本心爱之书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得不说,爱书人的存在将我们的天下变得更加丰富、有趣、温暖。
随性而读的自由
人类文明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作家、学者,是我能想到的最纯粹的爱书人,而且个个阅读量惊人。比如,法国大作家安德烈·纪德,在他82年的生命长河中,读书险些是每一天必做的作业,《纪德读书日记》(商务印书馆出版)便是从他60年的日记中选译与读书干系的内容汇编而成。对书本发自内心的挚爱散布在日记中,随处可见,读者首先会惊叹于他的阅读范围极其宽广,不仅有《鲁宾逊漂流记》《约翰·克利斯朵夫》《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文学作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他乃至从头到尾读了三次,每首诗连续读两遍,而且包括宗教、哲学、科学等多方面的书本都在他的阅读范围。
纪德在日记中原汁原味地记录了所读书目、阅读心得,以及由此展开的思考与批驳。他在一百年前所记载的读书点滴,今日读来依然给人新鲜如昨的印象。1922年1月5日,他这样写道:“我事情顺遂的日子,便是那些我选读一位古典作家、选读那些所谓‘经典’作为一日之始的日子。一页就够了;乃至半页,只要我是在适宜的精神状态下读的。与其说是一定要在个中探求什么教益,还不如说是要探求一种‘调性’,以及一种调适,它使当下的努力变得适可而止,而又不会消解此刻的紧迫感。这也是我终了一日劳作时所希望采纳的办法。”显然,这份随兴而读的自由让纪德乐在个中,他一边享受经典作品带给自己的精神上的愉悦知足,一边沉浸个中涵养自己的创作能量,完美臻达一种丰沛充足的爱书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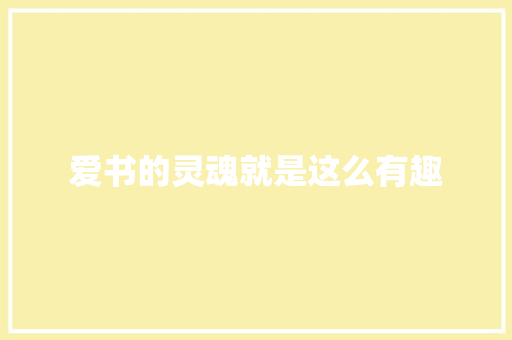
正所谓开卷有益,藏书致用。类似纪德这样把藏书、读书、写书合而为一的爱书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可以很随意马虎找到自己的东方知音。中华文化素有“敬惜字纸”的传统,耕读传家的祖训使藏书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书房或书斋在读书民气目中有着特殊神圣的文化意蕴,他们享受那种以书为壁、皓首穷经的庄严氛围。以南京大学40位学人书房为书写工具的《书房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颇能见证中国爱书人的藏书不雅观。纵不雅观40位南大学人的藏书,无一例外都呈现出书房东人的学术旨趣,霸占书本是为了研讨学问。譬如,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莫砺锋,从学生时期到古稀之年共利用过四个书房。顶天立地的书橱里塞满了他研学所需的全部书本和资料,个中与杜甫有关的图书霸占着重要位置,书房摆件中的两尊杜甫瓷像更是别有韵味。他就在这书山籍海之中完成了《杜甫评传》《唐宋诗论稿》等学术专著,竟至于忽略了要给书房起一个斋名,临时抱佛脚想到了“宁钝斋”。原来,教授父亲为其取名“砺锋”,是连同“莫”这个姓氏一并考虑的,意在希望他愚钝得福,切勿雕琢锋芒。他还自拟一副书房联:“青灯有味云影天光半亩水,白发多情霜晨月夕六朝山。”真是诗人清趣,足堪玩味。
君子爱书取之有道
“人永不厌倦在林中追逐”,这一句拉丁文古谚,用来描述爱书人对书的霸占之乐彷佛也是无比恰当。英国作家、报人威廉·罗伯茨在其著作《伦敦猎书客》(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有一篇长文《书痴面面不雅观》,以敏锐的视角和近乎独断的笔触,将爱书藏书之人划分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他写道:“一个人藏书的目的,要么是让自己在知识层面获益,要么便是纯粹出于炫耀铺张的虚荣心。”虽略显武断,却也不无道理。前文所述大作家纪德无疑属于前者,而后者常日把书视作待价而沽的收藏品。
不过,君子爱书,也应取之有道。威廉·罗伯茨曾阅历久致力于艺术品投资拍卖领域的资讯宣布,与伦敦顶尖的藏书人、书商以及拍卖行老板过从甚密,凭借其新闻的敏锐嗅觉,广泛包罗到大量与伦敦书界有关的第一手资料,他在《伦敦猎书客》中专辟一章《窃书者、借书者与竞价者》,绘声绘色地先容了许多关于偷书贼的传奇故事。
在罗伯茨看来,虽然偷书行为的潘多拉魔盒一旦开启,就会被认为是彻彻底底地误入歧途,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窃书贼却自带一种险些能使自己“饱受尊敬的古风”,从而减弱他们在道德律令面前遭受训斥的力度。书中写道,伦敦的大多数书商都曾有过和“窃书癖”的顾客打交道的经历。有一位精明的书商通过暗中不雅观察,不动声色地创造了“窃书癖”顾客,竟是颇具社会地位的老主顾Y师长西席,于是他默默地记下了每一次被“顺”走的书目及价格,待到某次Y师长西席又想故伎重演时,抓了个现行,让他乖乖付清了所有的书款。虽说Y师长西席后来再无颜面光顾这家书店,店主却仍旧坚持把新进书目邮寄给他,由于他相信这些书正是Y师长西席想要的书,而后者同样通过邮递办法,把这些书都买了回去。
为了得到一本好书不惜以身犯险,的确令人不可思议。藏书毕竟不同于收藏泉币、邮票、古旧家具,后者或多或少都与人类对金钱的希望沾上边,而藏书呢?用美国藏书家巴顿·伍德·柯里在其代表作《书林钓客》(商务印书馆出版)中的话来说:“破旧的古书与支离破碎的手稿残页向众人呈现出一种完备对立的货币代价不雅观,只有乱来孩童或白痴的那种戏法才能把这些褴褛的东西变成珍宝。”话虽如此,当一册装帧素雅的初版本佳品好书摆放在旧书店的橱窗里,当一份珍罕的作家手稿涌如今拍卖行的图录上,还是会让爱书者垂涎三尺,举牌争夺。
妙不可言的书缘
听说,相称一部分藏书家们在面对“你为什么喜好藏书?”的质询时,普遍的回应是:“没有缘故原由,便是喜好!
”钓鱼是讲求缘份的,一个好的契机会让你满载而归,爱书人与书结缘也需有机遇加持,个中掌故妙不可言。有一类藏书家可以说是“上帝的宠儿”,家学渊源使得他们从童年时期就浸润在浓厚的书喷鼻香氛围中,爱书的基因可谓熔铸在血液之中。有着“拍卖场上拿破仑”之称的美国有名古董书商A.S.W.罗森巴哈,便是这样一位被命运眷顾的幸运儿。在《猎书人的假日》(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中,他有一篇长文《谈旧书》,饶有兴趣地回顾起自己驰骋旧书天下的尘封往事。统统得益于他的舅舅摩西·波洛克,一家集出版和发卖于一体的二手书店的掌门人,并把书店办成了出版人、作家、藏书家的聚拢地,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他的外甥、少年书痴罗森巴哈乐不思蜀的伊甸园。“书店里那些僻静、蒙尘的角落是我所有童年回顾的中央,我可以为所欲为偷听大人讲话,流连其间。店里多了个到处乱翻故纸堆的小男孩,舅舅一开始是感到很烦的,可末了,拿给我看他从拍卖会和私人藏家那里入手的珍稀版本成了他的一大乐事。”在舅舅的精心栽培下,罗森巴哈的藏书“段位”有了突飞年夜进的提升,11岁时就在拍卖会上竞得人生的第一件藏品——一部插图版《列那狐》,落槌价24美元。可他只有一腔热血和瘪瘪的钱袋,主持拍卖的亨克尔斯师长西席哈哈大笑后破例许可他用零费钱分期付款。
爱书人的最高境界
如果爱书的尽头便是像罗森巴哈师长西席那样,拥有一间汗牛充栋的私人藏书室,个中不乏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古腾堡《圣经》、《爱丽丝漫游瑶池》手稿在内的稀世珍本,那么,这高不可攀的门槛足以让很多寒门诗人望洋兴叹。所幸,爱书的办法因人而异,各领风骚。记得有一次和陈子善教授谈天,他说一个爱书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便是自己动手写一本书。这让我想起日本明治大学的资深爱书人鹿岛茂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法国文学,由于常在神保町旧书街淘书,日久情深,索性写出一部《溜达神保町——日本旧书街通史》(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这部50万字的大书聚焦日本东京有着140余年历史的神保町旧书街,这里搜集了170多家旧书店,被誉为“天下第一旧书街”。其最初的形成,居然和附近的几所大学干系。学生们平常要为去牛肉火锅店聚餐而凑钱,索性把书卖给周边的旧书店,长此以往,逐步形成了旧书一条街的格局。读了鹿岛茂教授的这本旧书街通史,可进一步知晓,1913年的“神田大火”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曾让全体神保町损毁殆尽,其后的两次重修有如凤凰涅槃,不仅推动了日本旧书业的发展,更使其逐步具有天下级影响力。读书知人,读史阅世,这一段坎坷的旧书发展史,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书的命运牵连着藏书家的命运,书店的变迁折射出时期的变迁。工业革命中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得藏书步入黄金时期。金融危急来临之时,会加剧图书收藏市场的洗牌。互联网时期的到来也在开启新的赛道。潮起潮落,几经浮沉,书比人龟龄。爱书之人终将开悟,对待那些心神往之的珍本善本,“必须拥有”不过是一种偏执,“曾经我眼”才是一种永恒,变的是时期大潮中的人事代谢,不变的是对书的款款深情。还是华盛顿·欧文的一段话最能表达爱书人深藏心底的情愫:“当世俗的统统皆化作我们身边的浮渣,唯有这些(馆藏丰富的图书馆所带来的舒适感)才能留驻其永恒的代价。当好友之间终不免变得冷漠,当曾经亲密的交谈也如花般凋萎,留下枯燥乏味的客套,以及旧调重弹的话题,只有这些才能使往昔之欢愉不改其容颜,以那份永久不会欺骗希望、亦不会抛弃悲哀的友情,让快乐相伴于身。”
来源: 文申报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