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年,曾经在西安听过他的一堂课,课后互换的时候,一位专家曾经这样评价赵老师——别看他在课余是一个精廋的小老头,但是到了教室上,他频年夜多数年轻人还要精神。
当时我就在想,等到我七十岁的时候,我能否还能像赵老师一样精神矍铄,在自己喜好的奇迹上连续深钻呢?答案大概率是否定的。
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教书不过是我们谋生的工具,没有了教诲情怀的支撑,我们很难像那些前辈一样把这件事当成一项奇迹来做,更别说为止付出生平的努力了。
正如赵老师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大概不是中国语文“教得最好”的,但我敢说,我肯定是中国“最爱教”语文的。能够聆听赵老师这样的大咖的语文课,对中青年西席来说,不仅是视觉的饕餮盛宴,更是来自理念的巨大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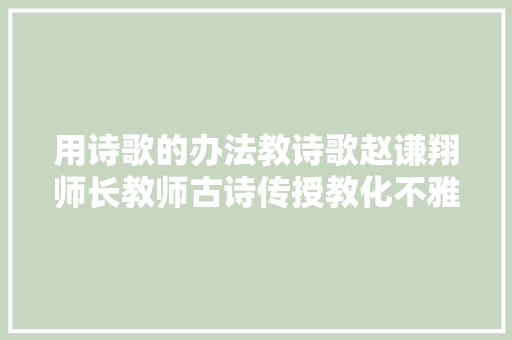
只是很可惜,由于现实的缘故原由,我只不雅观摩过赵老师的两节作文课,对我来说,多少是一种遗憾。
很幸运,本日再次听到了赵老师的古诗传授教化,对付从来不会古诗传授教化的我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霖。
由于赵老师的这节课,让我明白了,初中阶段的古诗传授教化该当是什么样子,更让我知道,古诗传授教化就该当用古诗本身的办法来教。
(图转网,如侵删。)
初中阶段的古诗传授教化,必须跳出“这一首”本身。
现行初中语文教材里面,除了《诗经二首》之外,所有的古代诗歌课目,都是四首起步,但是西席用书的建议,都是两课时。
常日情形下,一节课四十分钟,完成一首古诗的传授教化都还不足,更别说两首了。
听了赵老师的课,我终于明白,之以是会涌现这种情形,是由于我们被诗歌本身给局限住了,我们所关注的只是“这一首”,而不是“这一类”。
于是,学生随着我们一起读了三年的古诗,却依旧没有学会读古诗,如果试卷上涌现了课外的古诗篇目,他们立时就会不知所措。
赵老师的这节课,大致可以分成两个环节,第一环节“文体·音趣”,赵老师通过对四首古诗韵脚字的剖析,勾引学生明白了古体诗跟近体诗的差异与相互关系。
我想,有了这一课打底,往后全体初中的古诗学习,在文体和韵脚这一块,学生都不会犯难了。
简而言之,赵老师教的只是“这一课”(实在是半课,本课四首古诗,赵老师只选讲了两首),但是学生学到的却是“这一类”——诗歌。
如何实现中小学语文传授教化的衔接,一贯是很多语文老师头疼的问题,我想,赵老师的这一课,给我们做了极好的示范。
新课程标准几次再三强调“任务群”“群文阅读”之类的观点,我想,只要我们跳出“这一首”,开始关注“这一类”的时候,课程标准的精神也就得到了落实。
(图转网,如侵删。)
初中阶段的古诗传授教化,必须跳出“这一句”的框子。
现在回忆起来,我们的古诗传授教化之以是效率低下,是由于我们一贯在“翻译”诗歌——落实字词,逐句翻译,然后再让学生把翻译给背下来,把自己和学生都给累得半去世。
落实字词这个没什么,毕竟“言”是“文”的根本,只有看重了平时的积累,才能为学生后续的阅读打下根本。但是翻译这件事,多少有些“猪八戒吃人参果”的味道了。
众所周知,诗歌是墨客瞬间思绪的集中爆发,跟我们常读的文言文是有很大差距的,如果我们逐字翻译,根本没办法感想熏染到诗歌本身的美。
赵老师在传授教化中,并没有直接给学生解读诗句的含义,而是带着学生一起研读诗句中涌现的各种意象,让学生明白诗句中意象们的文化含义,懂了意象的文化含义,诗句的内容自然也就跃然纸上了。
当然,这也有一个条件,那便是老师必须要有充足的古诗文积累,不然的话,就算我们想要跳出框子,也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为了让学生明白“杨花”的身后意蕴,赵老师分别列举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东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等诗句,不仅在新旧知识之间建立了联系,更带领学生的思绪走向了更深处。
而这,便是语文传授教化最该有的样子,毕竟,任何学科的传授教化,终极都要落到思维上。
(图转网,如侵删。)
初中阶段的古诗传授教化,必须跳出“我”的思维桎梏。
邱俊老师曾说,当下的语文传授教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老师与学生,老师与文本,学生与文本,学生与学生之间,始终隔着一颗心的间隔。
仔细想来,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单单从阅读传授教化来说,我们总在哀求学生存心读,但是该怎么存心读,我们却没有教给学生办法。
作为一名读者,如果无法做到与作者共情,所有的理解和剖析,都带有浓重的“我”色彩,乃至是我们的无端忖度。
传授教化过程中,赵老师问得最多的问题,便是“作者的心情该如何”,通过对诗中场景的还原,把自己代入作者的思维,自然也就对作者的心境感同身受了。
一位前辈说,当我们开始着眼于“情”之一字的时候,我们就读懂了诗歌,也读懂了作者。如果老师再能稍作点拨,大部分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实在,不止是古诗传授教化,我自己的大部分教室,都带有强烈的“我”色彩——总习气把自己的理解强加给学生,至于学生能不能理解接管,我却很少考虑。
连学生的感想熏染我都没考虑,自然也就谈不上带领学生对作者共情了。
当教室短缺了“共情”,也就只剩下了一潭去世水,更何况本就间隔我们很远的古代诗歌了,传授教化效果低下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当然,如何跳出“我”的框子,和作者同呼吸共喜悲,就须要我们去进一步负责思考了。
(图转网,如侵删。)
教书多年,一贯在原地踏步,这是我的痛。
虽然这些年,我有过些许思考,但也只是浅尝辄止。而且,我所有的思考,也带有浓重的“我”意味,用于某节课也容许以,但是要推而广之,却是切切不能的。
赵谦翔老师曾说:“本日的我,要比昨天的我好;来日诰日的我,要比本日的我强。这便是我的全部志气和永恒追求。”
孔大贤人也曾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定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作为中年西席的我,想要在传授教化上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如果仅靠“十年磨一剑”的呆板打磨,绝对是不足的。
我须要去看看更大的天下,去听更多的课,只有这样,我的教室才会更加丰盈。
我须要静下心来,打磨自己的教室,不求一课一得,只求一日一思,一每天积淀自己。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凡人,成名成家不可能,立业立言也是痴人说梦,但是我想,只要一每天超越自我,这就足够了。
将来的某天,就算依旧误人子弟,也希望不要误得太多。
就让我回归教室本身,用诗歌的办法教诗歌,用散文的办法读散文,用小说的办法解小说,虽然现在的我依旧做不好,但是我想,只要坚持做下去,就足够了。
就像多年之前朋友在年终总结里所说的那样——“虽不能及,心神往之。”
(图转网,如侵删。)
(原创不易,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