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难(shuì nán),即游说进言的困难。韩非认为游说的真正困难在于不能把握游说的工具的主不雅观好恶。指出,游说的成功,紧张在于研究君王生理,投其所好,赢得君王信赖。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落而能尽之难也。
文章开宗明义指出进言的困难:不是难在我没有才智,也不是难在我没有口才,也不是难在我敢毫无顾忌地直言。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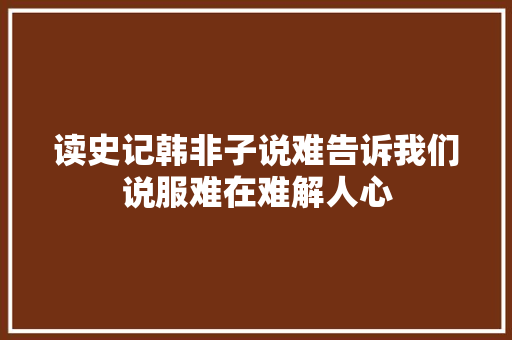
进言的困难在于,如何理解对方的生理,如何用得当的说辞迎合他。
接着,作者假设几种不理解对方而进言失落败的情形:
对方想要追求隽誉,却用厚利去说服他;
对方想要追求厚利,却用隽誉去说服他;
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
这种人更使人崩溃:对方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隽誉的,用隽誉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采纳而实际上疏远;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而表面疏远。
进言者还将面临七种“如此者身危”的情形,令人不寒而栗:
没有泄密的动机与行为,但发言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
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被进说者知道(知道要当作不知道);
进说者方案的事情符合君主心意,被聪明人从外部迹象预测出来了;
进说者的主见得以实施并得到成功,功德会被君主忘却;如果主见失落败,就会被君主疑惑;
君主有差错,进说者用礼义来挑他的毛病;
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
勉强君主做他不能做的事,强制君主停滞他不愿意停滞的事。
如此,进言者在说话前都要反复考虑,有没有违禁,否则有几个脑袋够砍的?
进言者在君王面前谈论与君王有关的人要拿捏分寸
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会被认为是离间君臣关系;和君主评论辩论近侍小臣,就被认为是想虚假身价。
评论辩论君主喜好的人,就被认为是拉关系;
评论辩论君主讨厌的人,就被认为是在试探。
发言要节制火候:
说话刀切斧砍,就被认为是不聪明而笨拙;发言噜苏详尽,就被认为是啰嗦而冗长。
简单陈述见地,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尽言;找事空泛放任,就被认为是粗野而不懂礼貌。
以上都是“说难”的环境,那么进说的办法是什么呢?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
务必要做的是懂得仰承君主,学会掩罪藏恶:
君主有私人的急事,进说者一定要指明这合乎公义而鼓励他去做;
君主有卑下的动机不能克制,进说者就应把它粉饰成美好的而抱怨他不去干;
君主有过高的企求,而实际不能达到,进说者就为他举出此事的缺陷并揭示它的坏处,而夸奖他不去做;
君主想自夸智能,就替他举出同类情形,多给他供应根据,使他借用说法,而假装不知道,这样来帮助他自夸才智。
进说者想让君主收受接管的事,就必须用好的名义,并暗示它合乎君主私利。
进说者想要指出危害的事,就明言此事会遭到的诬蔑,并暗示它对君主也有害处。
有和君主污行相同的,就必须对它大加粉饰,说它没有害处;有和君主败迹相同的,就必须对它明言掩锦,说他没有过失落。
君主自夸力量强大时,就不要用他难堪的事去压抑他;君主自以为决议确定年夜胆时,就不要用他的过失落去激怒他;君主自以为计谋高明时,就不要用败绩去让他尴尬。
如果能做到以上总总,进言者就到达人生佳境了:
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然后极骋智辩焉。
进说的主旨没有什么违逆,言辞没有什么抵触,然后就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慧和辩才了。
比如,伊尹做过厨师,百里奚做过奴隶,都是为了求得君主重用。这两个人都是贤人,但还是不能不通过做卑下的事来求得主上的信用。
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短长甚至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作者用“旷日离久”来形容进言者在国君面前的谄媚历史。到那时,国君的“恩典膏泽已厚”,进说者大的谋划不再被疑惑,有争议的建议不再见开罪,就可以明确阐发短长来造诣君主的功业,直接指明是非来端正君主的言行,能这样相互对待,是进说成功了。
但这种情形会实现吗?伊尹碰着的可是商汤,垂暮之年的百里奚碰着的可是秦穆公,都是明君。如果碰着昏君的话,经由以上层层关卡,能活下来的进言者有几个?耿直的说客的命运是悲惨的。
如果他真能活下来,那他一定是“戏精”,是佞臣,还记得自己的初心吗?昏聩的君王把忠臣变奸臣。
韩非子在这篇论文里,名说“说难”,实际上是阐发了君主惨淡的生理活动 , 猜忌、 多疑、 虚荣、 伪诈、 凶险、 多变等品性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文风锐利,彰显雄辩能力。
而作为进言者的韩非子也决不会把自己塑造成他所描述的“空想”的“戏精”。
《老子韩非列传》: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
《说难》是韩非子的发奋之作。韩非子是韩国末世公子,见韩国逐步削弱,多次上书,终不被所用。
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不雅观往者得失落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说难十余万言。
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也预示了他悲剧的命运。 司马迁不无惋惜地说: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去世于秦,不能自脱。
韩非虽然知道“说之难”,也懂得解脱的办法,但终极去世于秦,不能用《说难》补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