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的国度”,我们对诗的热爱从未消减,反而随着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而进步神速,希冀通过古诗词里的那些浪漫唯美的情绪传染,给自己在奔波的生活中开辟一方净土,以“诗意的栖居”于日常噜苏之中。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朴拙的情绪、生动的形象、幽美的措辞和深婉的意味,无不令人动容。然而,“往事越千年”,那字里行间的动人韵律和那些笔墨背后的朴拙面庞都已随着历史的远去而渐次模糊。我们该如何透过日常所见、所用的古诗词感想熏染那一颗颗炽热而诚挚的“诗心”?
我们有情由相信,真正的艺术是不须要那么多“门槛儿”的:曹胜高教授近日出版《读懂古典诗词》一书,便冲破了赏析、知识、学术之间的壁垒,第一次面向普通读者系统地讲解了古典诗词中的核心观点、紧张事理和基本知识,以补“遍及”多见而“提高”少有之弊,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凡百姓家”。
该书措辞精雅独到而又动听至深,立足于古典诗词而又不仅限于诗词,着眼于诗歌内在的演进规律,用一个个横切面向广大读者展示了诗歌这种集音乐、图画和建筑三种艺术于一体的艺术创造。纵不雅观全书,感触有三:
一 雅俗兼顾 深入浅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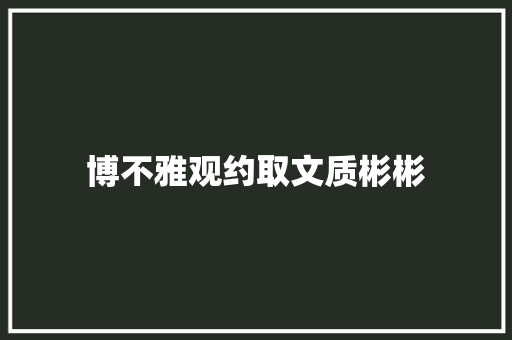
基于一样平常读者系统地理解古典诗词的发生事理、发展脉络、创作机制、鉴赏方法的需求,该书在先容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一些术语时,便利用了普通易懂、贴近生活的措辞,易于理解又倍感亲切。如书中对“兴、不雅观、群、怨”的阐明极具特色:
兴,是诗歌能够感发,就像我们现在唱歌一样,一人唱数人和,不知不觉便进入到情境之中。不雅观,是通过诗歌不雅观察民风,不雅观察老百姓的志向。群,是诗歌能够担负互换的义务,周秦期间的外交官常常引诗来委婉表达志向,后世也相互唱和赠答,表达“心志”,促进彼此的互换。怨,是诗歌的疏泄功能,指被压抑的情绪,可以通过诗歌来开导。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不雅观,可以群,可以怨。”用数人合唱作譬,来解释诗歌的感发功能,贴近生活履历,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不雅观”则是“不雅观察老百姓的志向”,普通易懂;而用“外交官”来表述“各国使者”,则更符合普通读者的措辞习气,也不失落风趣诙谐;“怨”则是指“诗歌的疏泄功能”,言简意赅。类似的表述办法在书中随处可见,比如“以赋结章”,便是“把赋法作为一种句法来利用”,“妙悟自然”便是“心与自然瞬间结合在一起”等。
此外,在详细诗歌的鉴赏中,也采纳了读者更为喜闻乐见的、形象可感的措辞。如对《诗经·邶风·静女》的解读:“爱而不见”,男子去了,女子却没涌现,藏了起来逗他,女子的调皮就显示出来了。男子“搔首踟蹰”,就在那儿徘徊,男子的朴实也显示出来了。
“藏了起来逗他”“就在那儿徘徊”便是读者的口头措辞,生活气息浓厚,情态毕现,跃然纸上。不论是在古典诗词的术语当中,还是在详细诗歌的解读中,都深入浅出地用生动形象的措辞,令人倍感亲切。
当然,作为一部研究型专著,典雅性、严谨性也必不可少。对付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术语,不仅须要简明扼要地表述,也须要严谨精湛地解读。如《文心雕龙·神思》中言:“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雪精神。”作者在该书中指出,“虚静”来源于道家学说,但道家则更看重于从认识论角度来定义,“指的是人在认识外界事物时,主动采纳静不雅观的一种体认办法”。而古典文论中的“虚静”则是强调,在创作前,作者必须达到“虚静”状态,“主客体之间必须做到异质同构,消耗彼此界线”,即“神与物游”。而“神思”的特色正是“神与物游”,“是作者把自己的情绪、心志、兴趣、思理与外在物象相融通,是作者通过情绪体验和艺术理性,把客不雅观物象主不雅观化的过程。”这样才能达到“登山则情满于山,不雅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境界。
二 多种角度 广泛撷取
立足于中国古典诗词,而又不局限于诗词,而是从多种视角,多方采撷,来解读诗词。在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过程中,各种艺术形式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终极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解释《诗经》不仅是歌诗集,也是乐曲集,与音乐密不可分。纵然在诗歌往后的发展脉络中,音乐也充当着极为主要的角色。诗歌的句式、节奏和韵律都是其音乐美的集中表示。该书在《诗的声情》一章便对此进行了极为深入的谈论。此外,在阐发详细诗歌的时候,也能结合诗的音乐性,揭示其感发人的缘由。如李商隐的《深秋独游曲江》: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
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二十八个字,用了十七个齿音,每一个字,都仿佛敲在你的心上。”从音韵的角度,使读者明白了为何读这首诗时伤感怅惘之情萦绕不去。
当然,诗歌与字画同样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王维之以是被苏轼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是由于王维诗歌中所展现出来的色彩比拟,动静结合,长于构图等,都像古典画作一样,给人以美的享受。如“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暖色调的夕阳与冷色调的青苔形成了光鲜的对照,在森林深处的灰褐色中得到过渡,从而实现了物象间的和谐。”使得深林显得不那么幽冷沉重,夕阳也显得不那么轻佻突兀,全体画面的明暗比拟和冷暖对照,读来温暖从容,情景十全十美。再如动静结合的《鸟鸣涧》,以及构图浑融壮阔的《使至塞上》,都将诗歌的画面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该书更是引用传统绘画的构图技法,讲诗歌的构图方法概括为“平远法、深远法、高远法”,并进一步地指出了三种构图办法所带给读者的不同的审美体验。
此外,作者还奥妙地利用书法、武术等传统,揭示了诗歌创作中先有量变而后有质变的客不雅观规律。凡此各类,无不展现了该书涵盖广泛、学养深厚,不仅是品读古典诗词的钥匙,更是管窥中国精良传统文化的窗户。
三 纵横交错 点面结合
长于宏不雅观全局,从文学发展脉络着眼,又能从细微处入手,点面结合,由面成体,作者多年以来基于深厚的学养积淀而形成的学术格局和研究方法,也在该书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示。该书以宏阔的视野,将古诗词品读延展到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层面,如从《周易》到老庄哲学再到玄学,来解读“象”,更是从中西方诗歌的比拟中引出“意象”的主要性;从中国古典美学的层面去品读诗词之美,将读者个人的、零散的、随即的感想提高到审美层面,深刻揭示了“古典作品中的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见意义、艺术风格,为什么仍旧与本日人们的感想熏染爱好相吻合”。在《诗经》和汉乐府期间,“其情绪与想象代表着群体认知,如琢如磨,很随意马虎引起群体的共鸣”,而随着诗歌的发展,文人诗的涌现,即便是墨客更“侧重于个体情绪的表达”,但由于群体代价取向的内在约束,“使得文学并没有完备滑向自说自话的田地”,而依然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这样的审美感想熏染是千百年来浓缩了的中华文明,是文化基因的积淀,即便我们本日看似遗忘了,也能在该书深微贴切的阐发中被唤醒。
同时,该书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出发去梳理诗歌发展的规律,对付普通读者来说,有利于对诗歌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对古典文学有更全面的把握。该书从诗的发生提及,到诗的流变,再到唐宋分宗,以这一线索为经,穿插先容了诗之“六义”、诗之意境、诗之声韵、诗之构思、诗之品读,等等,再以诗之机理扫尾,泾渭分明,脉络清晰。带领读者前辈入诗歌的殿堂,再跳出一时一代之诗歌,纵横、远近之“庐山真面孔”尽收眼底。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顺敦厚,《诗》教也。”我们诵诗、品诗、学诗,并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措辞功底,增长学识见地,更是为了在诗之美学的熏陶下,熬炼品质,提升教化,像诗一样有节制地表达、抒发喜怒哀乐,提高审美境界,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当每一个个体都能具有温润敦厚的君子之风,则社会风气也会文质彬彬、和谐原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目前为止,大众已经对古典诗词中的代表性篇目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如何在此根本上,让读者能够窥得古典诗词之门径,感想熏染古典美学之魅力,教化君子之人格,该书的出版则是极为有益、极为有力的考试测验,具有首创性的意义。(王禹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