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以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河西首郡——凉州为故事原点,以中国古琴名曲《胡笳十八拍》为叙事构造,以当代版的“赵氏孤儿”为故事内核,着力塑造了一批来自民间且拥有文化自觉与大义担当的凉州子弟、义勇之士和热血少年,在山河板荡、世道浇漓、军阀践踏、官衙腐败的大时期当中,如何心系家国命运,满怀忠义豪情,守护河西大地,进而演绎出了一场场死活不弃、惊天撼地的悲壮故事。奔流新闻文化频道今日分享这部小说的精彩章节《第五拍·胡笳29节》。
《凉州十八拍》
第五拍·胡笳29节
叶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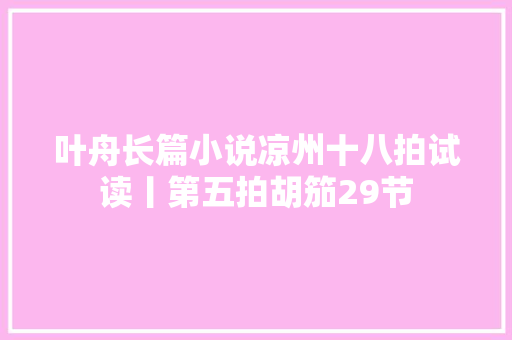
喊了一声停,车轿戛然而止。
这一刻,张不雅观察溘然伸手,捉住了对面顾山农的腕子,双腮潮红,目射精光,急迫道:尊兄,这一起上你给我打了无数个比方,现在你确切地说一句,究竟何谓沙漠?顾山农已经穷尽了辞藻和想象,勉强地说:呃,这大概就即是把亿万兆的沙子堆起来,堆成了一座座山,坐在了凉州的地界上。张不雅观察一拍大腿:没错,这个词该当称之为恒河沙数。顾山农又道:不过呢,远看像山,可一旦走进去的话,人就像秋上的一片落叶,掉在了湖水里似的,恐怕是活路难寻。张不雅观察缓颊道:是啊,这便是芥子宇宙,针尖道场,眼前中国的这一番糟糕时局,内战不止的场面,岂不是也像你所描述的沙漠瀚海一样平常,看不见彼岸,求不得和平么?顾山农笑说:阁下,这里天高天子远的,先请你放下心中的泼烦,伸展了眉头,跟凉州本地的郡老们一同乐呵乐呵吧,毕竟这是你第一次走河西,头一回见识沙山。言毕,顾山农挑开帘子,抬腿下了车,瞭见车夫跑将过来,赶紧将一只下马凳支好,又去搀扶客人。张不雅观察愣了愣,终于鼓足了勇气,拨开车夫,一个蹦子跳将下来,搂住了顾山农的肩膀。
不承想,环眼一望,天地之间平坦如砥,别说沙山了,竟然连一粒沙子也不见。
张不雅观察立时明白,或许由于太激动,方才喊早了,搁浅在了中途中,这个尴尬还得自己来整顿,以免失落掉了身份。这么着,张不雅观察对着车夫,负责地鞠了一躬,督匆匆对方赶紧驾车回城,不必再跟随了,他打算徒步上沙山,没准这也是一桩人生乐事。顾山农的内里唉哟了一声,料知这个任性的客人心血来潮,如果真要走完剩下的这五六里地,黄花菜凉了不说,郡老们也一定会怨怪的。这辆车轿专属于县长吕介侯,车夫亦是,在张不雅观察逗留凉州期间,临时指派给了客人,以示重视,迄今做事了七八天之久,彼此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情分。车夫嘟囔着,求告着,问是不是搪突了客人,或者有不到之处,恳请包涵,否则这么青皮寡脸地回去,县长绝对要开除了他。张不雅观察一迭声地否认,从身上摸出来一件卷轴,递给车夫,释解道:哎呀,你误会不才了,这些天你鞍前马后的,让我过意不去,这是我特地给你写的一幅字,吕县长如果见了,不仅不会责怪,说不定还要奖励你的。车夫是个腼腆男人,几次再三却步,不肯接管。张不雅观察无奈,遂解开了束绳,一头交给了顾山农,他自己也扯开了另一头,将两行飞舞的墨字,呈现在了晴天丽日之下。莫笑拉车受辛劳,请看当年宋太祖。顾山农偏过分去,念了两遍,却不谙其意,刚打算伸开耳朵,聆听对方的阐释时,卷轴却被收走了,重新绑上了束绳。张不雅观察趋前,再次鞠上一躬,两手敬呈上去。车夫红着脸,匆忙接住后,腰身弯成了一张弓,踏实地回敬了三下,而后跳上辕驾,拨转了马头,折返而去。
盯望着武威城的方向,沙石路上漾起了一股股轻淡的烟尘。两侧的高树和郊田上,凉州的秋日业已格外光鲜,貌似一碧如洗的天空,正在酝酿着冬雷与罡风,一样平常人当然难以窥见个中的天机。目睹了刚才的这一幕,顾山农不由得肃穆了下来,这个客人的谦善与学识,那一份蔼然和涵养,犹如一道醍醐,贯注灌注在了他的心头,令他如沐东风,一韶光忘怀了沙山,忘怀了那些翘首以盼的家乡父老。旁侧里,张不雅观察逐步地收回了目光,溘然喊了一嗓子:劳工万岁,劳工神圣。由于隔着一层口音,顾山农听不精密,忙问了一句:阁下,你再重复一遍吧。张不雅观察立时明白了个中的隔阂,拾起一根树枝,在地上负责地写下了这些话。劳工,这是顾山农第一次闻听这个词,虽说大概知道字面上的意思,但个中的奥义,又仿佛一道谜题,吸引了他的好奇心。此刻,乃是两个人首次独处,抛开了在驿馆会晤时的尴尬与窘迫,也阔别了武威城中的鼓噪,站在了地远天荒的凉州一角,各自放下了戒备与客套。顾山农的内里,逐渐潮起了一种渴望,一种想要结交对方的冲动。由于他确切地认定,这个客人将是自己的教养之门,机会之窗,一旦关闭的话,恐怕将永远不再。这么着,顾山农腾起了一种勇气,开腔道:
“阁下,我想借你一样东西?”
“尊兄,你只管嘱咐。”
“借你的这只手。”
“手?”
不待对方有所反应,顾山农抢上前去,一把握住了张不雅观察的左手,而后拉拽上他,一道走向了沙山。张不雅观察当即豁然了,身心轻盈了起来,将自己全部交给了这名引导,一任他指天戳地,纵论河西,皆是一些闻所未闻的山川文章,锦绣辞藻。过境陕西的时候,张不雅观察游历了不少的古迹与名胜,一贯被诗词牵引着,个中尤喜王维的那首《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不承想,此刻置身于祁连山下,穿行在广袤的河西绿洲上,这一幕訇然而来,激越心头。从顾山农的脾气上阐发,再从上一次短暂的交往上判断,张不雅观察的心中,泌出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动机,几次再三告诫自己,这个溘然间神采飞扬的青年,绝不是县长吕介侯的门客,更不是用来敷衍他的一枚棋子。于是乎,张不雅观察一扫前些天的烦懑和郁愤,以为天高云阔,万物斑斓,乃至对全体凉州的那一份深刻敌意,也逐渐地退潮了,忘怀在了脑后。两个人相率而行,一边攀谈着,一边跳跃着,大有相见恨晚之势。半路上歇缓时,主客二人论了齿序,原来张不雅观察属兔,顾山农为马,前者比后者整整年长了三岁,竟然连月份都是同等的。在这一番惊喜下,顾山农苦苦哀求,让张不雅观察赶紧改口,最好不要再一嘴一个尊兄地喊了,称呼他一声贤弟,则是此生莫大的喜悦。张不雅观察也顽劣开来,一副板上钉钉的态度,坚辞不从,持续迭地抛出去了十七八个尊兄,险些呛住了对方。顾山农被喊急了,又是鞠躬,又是作揖,求告再三,追问客人究竟开一个什么条件,他才能恰当地改口,让彼此莫逆起来。张不雅观察放下了戏谑,板正地说:
“这好办,待我从迪化和猩猩峡,从敦煌一带回来后,我开始做兄,你从此为弟。”
“割头?换帖?咱们结下这一世的金兰之谊?”
急迫地问。
“兴许吧,但最好是战友,做同道中人。”
“阁下,你真的打算单人独马,一贯走到猩猩峡口,走到迪化,走到天涯的尽头么?这一条路太危险,也太叵测了,其实让我替你捏一把汗,放心不下。”到了这个地步,顾山农已是热肝辣肠,取出了全部的肺腑,恳切地说,“要不,阁下在凉州待上个一年半载,最最少也要过了旧历新年,等明年开春之后,等我忙完了手头上的琐事,山农乐意替你牵马拽蹬,随扈旁边,哪怕是远赴口外,去游历全体新疆,我也万去世不辞。”
张不雅观察拊掌大笑:“岂敢,岂敢。尊兄的志向,在于做一介贸易领袖,打通河西走廊的这一条商业通道,让百货茂盛,民众富余,这的确令人钦佩。唉,不才不过是务虚之人,前来游山玩水的,你大可不必分心,千万不能让我羁绊住你的手脚,耽搁了你的大事呀。”
“阁下,你为何独执己念,一意西行,全然不顾前路上的危险呢?”
“倘若危险是值得的呢?”
“一个危字,加上一个险字,又何谈值得?”
“而这正好是转圜的契机。”
“呃,还请阁下开示,山农洗耳恭听。”
忽然抱拳。
“的确,正如尊兄所言,既然认定将来的路上,布满了各类的危险与荆棘,那就不值得去蹈去世犯难,去戴着桎梏起舞,而该当苟且,该当驯顺,填犬儒之乐谱,放奴隶之歌声。俗话说,蝼蚁尚且偷生,飞鸟还爱惜羽毛,遑论像你我这样懂得短长、知道进退的人。”张不雅观察不愧是一位文章家,以屈求伸地说,“但是,这个天下上偏偏有那么一小撮的人类,长了反骨,生了贰心,反倒以为所谓的危险,或许才是一条光明的救赎之道。”
“反骨?救赎?”嗫嚅道。
“不错,这便是眼前腐败已久的中国,十万遑急地须要具备的一场启蒙运动,人不分老幼,地无问东西,必须全情投入进去,求得一条去世地重生的出路。否则的话,这个国家假如连续被糟践下去,势必瓦裂在即,无足轻重,终极将沦为一支劣等之民族。”
顾山农溘然以为,个人的心中涌出了一股岩浆般的东西,五内俱沸,恳切道:“阁下,我彷佛听懂了,但实际上我无知透顶。那么,照你刚才的意思,阁下穿州走府,不远千里地投入到了凉州境内,如今落脚在河西首郡,莫非你便是一位专门来寻路的先锋官,一只唱白天下的雄鸡?”
“我跟尊兄殊途同归,一样的念想。”
“不,阁下才是我的启明星,我的祁连山,山农岂敢与天争高,跟山比肩呀。”顾山农的颊酡颜透了,一揖到底,“上一次拜访真是受教多多,回家之后,我总是咀嚼再三,仔细消化,恐怕辜负了阁下的点拨和垂青。另一个,山农给阁下绍介的那些河西噜苏,纯粹是鲁班门口弄斧,贤人面前念经,对的你就听上一耳朵,欠妥之处只管一风吹净吧。”
“尊兄,你我即将要干的这些事情,大抵上是男儿道场,壮士行为,难免步步惊心,危险时在。我是白手来的,可没带什么礼物,在承平堡和保价局开张之际,我只能送你这么一句话,还请你笑纳。”
男儿道场,壮士行为,顾山农暗自咂摸着,心中炎火升腾。
“哦,如果说你我有所不同,恐怕也只在于尊兄效仿了当年的班霍二人,用了马蹄,用了驼队,用了自己的一双大脚,在川原平旷上突进,在苍莽山河中行路,这实属一种范例的实践主义。至于我,手中具有的不过是一沓纸,一杆笔,务虚罢了,只能替尊兄喧哗与叫好,从而东西呼应,揭橥原形。”这个枢纽关头上,张不雅观察俯下身,攥住了郊田上的一把湿土,捏塑成型,竟成了石头的样子,慨然道,“但是,不管差异有多大,你我的这一项天课,这一桩义务,事实上是为这个国家效忠,在替全体西北除锈,目的只在于光大民族,鼓铸国魂。”
“除锈?”
顾山农急迫地问。
“对,非除不可!
如此一来,才能抖擞精神血肉,气作山河,光绚我们民族。”
“阁下,请你替我拨云见日吧。”深深一揖。
“西北者,乃中国之心腹。尤其是河西绿洲,包括远处的那一座祁连山,天马怒龙,容仪丰伟,堪比一根特立的脊梁骨,端正忘我。自古而来,从国家的气候上勘察,必定是北胜于南,西胜于东。这一方水土,埋藏着我们民族的千经万典,圣言贤传,一向是匡危扶倾的发源之地,犹如一尊金鼎,一座佛龛,令人敬畏。”张不雅观察丧失落了手中的泥土,遥指着弧形的天空下,那一线义士般的山脊,唏嘘地说,“只可惜,后来的政权分子们,要么鼠目寸光,要么势孤力蹙,一方面锁国,另一方面却内战不休,取诮于列邦,让这一片大好河山,见弃于天下民族之林,见轻于全体中国,成了一块疼痛的锈带,无人问津。”
顾山农一惊,愕然道:“锈带!
”
“但是,它锈而不去世,去世而不僵,一贯在等待着梗直壮烈、蹈去世犯难之人,前来除锈,前来培根固本,重新让它苏息过来,挺直脊梁。”张不雅观察敛回了目光,沉雄地说,“像这一类人物,史不绝书,典范犹在。以是,我这一次的游历,便打算用自己的这一支笔,将这些粗陋的心得,奉告天下,求得一个办理之道。”
“那在阁下看来,该当如何除锈?”
“开路。”
截铁地说。
“打通东西,连接道路,寻见一个生息之机?”
“不错,还要运送,繁昌贸易。”
顾山农激奋地说:“阁下,这正是承平堡的主见,也是保价局的目的。”
“那么,恭喜尊兄开业大吉,将来有一番崭新而有力的作为,这也就不枉了你我相识一场,让我往后在上海和江南一带,对西北有一个美好的惦记。”张不雅观察同样还了一礼,果决地说,“山农,我方才讲的男儿道场,壮士行为,说白了,便是为国家尽一分心力,培一分元气,绵一分国祚,别无他图。”
“阁下,莫非你准备动身,打算离开凉州,连续去西天取经?”顾山农吃惊道。
“最迟后天。”
“但是,那件事还没有了却呀?”
“呃,那不过是身外之物,丢了也就丢了吧,我现在习气了,不想为它所困。”
闻听此话,顾山农一韶光浑身发冷,却又抑制不住这些天以来,建立在心中的那一份依赖与信赖。顾山农明白,自己不能强人所难,再多的挽留,毕竟也是一幕天涯重逢,终有挥泪决袂的那一刻。这么着,顾山农再次上前,一把捉住了客人的腕子,将一枚黄澄澄的戒指,迅速箍在了张不雅观察的指根上,知足地笑出了声。张不雅观察盯望着自己的指头,瞭见戒指上卧着一只貔貅,兀自摇了摇头,但是也未曾摘下来,交还给主人,只说:
“呵呵,我并不信这些。”
“呃,阁下还是戴上吧,兴容许以辟邪。”这枚金戒指来自弟弟惊白,原来是请托顾山农,交给梅郎中的一笔定金,但北疆的病人一贯没来,于是揣在口袋里许久了,“阁下一旦离开了凉州,去往猩猩峡一带,这上千里的长路,难免会有一些颠簸与不顺,避一避邪祟也是该当的。毕竟你出门在外,身处异域,不管站在了哪个山头上,还是要入乡顺俗,拜拜那一尊山神吧。”
“也罢,先暂且寄在我的身上,等返程回来后,我再璧还给尊兄。”
“衬你,你戴上可真俊秀。”
“告饶了,我以为自己浑身的铜臭气,切实其实不像一个精良的读书人。”自嘲道。
依旧望不见沙山,剩下的里程还有一大半,懈怠不得。日头踞伏在头顶上,空气逐渐地燥热了起来,两侧的郊田上白花花一片,刺人眼目。两个人拽开了手脚,大步流星,嘴里呼哧呼哧的。偶尔,四目相对之际,各自会心而笑,仿佛共同流落于天涯一隅,互为珍惜。顾山农终于耐不住这一番单调,央告说:
“阁下,请你给我讲讲江南,讲讲上海滩吧?”
“然后呢?”
顾山农一股脑地说:“再讲一讲武汉,南京,广州。”
“再然后呢?”
“当然是北平,天津,东三省了。”
“呵呵,尊兄真是野心不小,气概非凡,你这是让我在做一篇中国文章呀。”
“拜那一本《中华最新形势图》所赐,我最近险些将它快翻烂了,不过我还想听听阁下的亲口讲述。”顾山农追撵了上去,不依不饶地求请着。
张不雅观察者,本名张俊彦,字独木,江西上饶人氏,上海滩报界闻人,国际不雅观察家,一支笔辛辣老练,擅于针砭时弊,向来言之凿凿,立论煌煌,拥有广泛的拥趸以及深厚的人脉。此番,张不雅观察首次涉足西北,踏勘山川形胜,记录风土民情,受到了陕甘两省的极大礼遇。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阶层,出于为尊者讳,一概称其为张不雅观察。半个月前,甘肃省府电令武威县做好相应的接待准备,统统需求,均由当地供给。县长吕介侯不敢怠慢,亲率了一哨人马,在古浪峡口跟张不雅观察接洽上了,并当场给后者敬了三碗下马酒。
干系链接:
叶舟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试读丨第一拍·胡笳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