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翻书
荐好书
扒一扒
铁匠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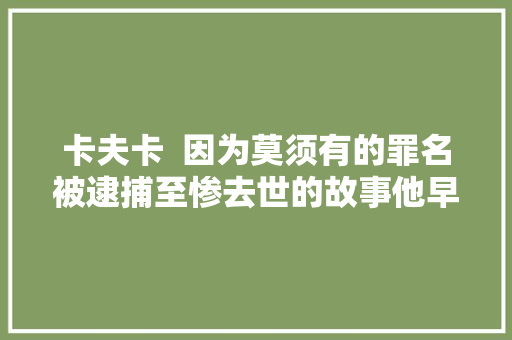
《审判》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最为著名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925年。
主人公约瑟夫·K在30岁生日那天溘然被捕,罪名、审判...统统都来得莫名其妙。他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却从此陷入无休无止的官司之中。他寻求各种帮助,但所有试图“帮助”他的人,不是将他引向自由,而是为了掌握他教他屈服威信。经由一年的挣扎,K在他三十一岁生日的前夜被莫名其妙的处去世在采石场。
看似“魔幻现实”的情节却具有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卡夫卡一贯试图揭示当代文明的困境,在看似理性、进步的当代社会中,人们却遭遇着“变形”和“异化”的困境,遭遇着无时无刻被审判却无路可逃的命运。
但卡夫卡对这些荒谬的生存状态的描述又充满了文学性,米兰·昆德拉说,我们无法比卡夫卡的《审判》写得更深入了,他为一个极无诗意的天下创造了极有诗意的意象。
如何进入卡夫卡笔下这个“极无诗意”的天下?
如何体会卡夫卡的另类诗意?
另一位伟大作家布鲁诺·舒兹为我们供应了钥匙🔑
阅读提示:如果以为字体过大或过小可以按屏幕右上方选择“调度字体”。
《审判》波兰版跋
布鲁诺·舒兹
(本文由波兰文直译,本文译者为林蔚昀,
收录于《审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布鲁诺·舒兹,出身于德罗活贝奇的波兰犹太裔作家,被誉为波兰二十世纪的文学宝贝。其风格魔幻动人,充满对生活的细微不雅观察以及不可思议的奇想。
舒兹生平只写了两部短篇小说集《鳄鱼街》和《沙漏下的调理院》,以神话的办法描写自己的童年以及家(最出名的便是那个不断去世去活来、蜕变成各种奇怪生物的父亲)。其作品风格常常被人拿来和和夫卡、普鲁斯特比较。
创作:抵达原形的路子
在卡夫卡生前得以出版的作品有如百里挑一。由于卡夫卡对自己的作品抱着重大无比的任务感,并且以崇高的、宗教般的神圣态度看待创作,这使得他无法知足于任何造诣,只能一篇又一篇地扔弃些充满神来之笔的精品。只有一小群好友才有机会在时候就看出,卡夫卡即将成为一位格局宏伟的创作者,他把那终极的任务揽到身上,辛劳地奋斗,试图办理最深奥的课题。
对卡夫卡来说,创作从来就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带领他抵达终极原形的路子,让他可以找到人生的正道。卡夫卡命运的悲剧是,虽然他终其生平抱着绝望的激情亲切探求、渴望攀附到崇奉的光芒之上,他却无法找到它。虽然不愿意,他的命运还是走入了幽暗之地。这可以阐明为什么在临终之际,这位早逝的创作者交代密友马克斯·布罗德(MaxBrod)将其创作尽数销毁。作为卡夫卡的遗嘱实行人,马克斯却决定违反去世者的遗嘱,反而将那些幸存的作品陆续分成好几册出版,奠定了卡夫卡作为这个时期伟大心灵的地位。
弗兰兹·卡夫卡,出生于1883年,生活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小说家。1904年开始写作,紧张作品为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揭橥,3部长篇也均未写完。
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期,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伶仃、绝望的个人。文笔明净而想象奇诡,常采取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大家殊,暂无(或永无)定论。
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当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卡夫卡丰富又强烈的创作——在早期就十分完全成熟——实在从一开始便是来自于深刻的宗教体验。他的作品正是在这种体验引发之下,所创造出来的记述及见证。卡夫卡的目光总是被那凌驾于世俗之上的、神性的意义所吸引,他以这样的目光瞥见隐蔽的现实,带着研究的热心探索它深奥深厚的秩序、组织和架构,丈量人性和神性之间的边界到底在何处。
他是歌颂神之秩序的墨客,说真的,这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文类。纵然是最极度的诋毁者和讽刺作家,也无法像卡夫卡那样把个天下描写得如此揶揄讽刺、变形、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荒诞可笑的样子。
在卡夫卡心目中,神性天下的崇高无法以别的办法表达——只能把它表现成否定人类天下的强大力量。神性天下的秩序离人类的秩序如此迢遥,超越所有人类可理解的范畴,它的崇高在人类眼中成了负面的力量,遭受到他们暴烈的反抗和感情性的批评。话说回来,人类在面对这些力量的夺权时,除了抗议、不能理解以及一壁倒的批评之外,还会有什么反应呢?
约瑟夫·K:人类可笑的傲慢与盲目
《审判》的主角在他的案件初次开庭审理的时候,便是这么弗成一世地大肆批评了法院。他夸年夜地攻击它,表面上有效地把它痛批了一顿,从被告的身份转换成原告。从人类的眼力看来,法院陷人了尴尬的处境,变得退缩、无助。这份无助,完美地表现出法院的崇高和人类世俗事务之间的不平衡。这统统都让满脑筋改革动机的主角感到愉快,这又加剧了他的自大与狂热。
盲目的人类便是以这种办法去面对神之力量的侵袭的他们浮夸自我,把古老的做慢披在身上——然而,这份傲慢并不是引起神之愤怒和天谴的缘故原由,而是它的副产品。约瑟夫·K以为自己比法院高尚百倍,法院些色厉内荏的欺骗手段和阴谋让他以为恶心。他于是试图用国家利益、文明和事情来回嘴它。真是可笑的盲目!
他的高尚和权利无法保护他,让他免于面对那已经无法避免的审判。审判深入他的生命,仿佛完备凌驾于他的高尚及权利之上。
约瑟夫·K感到审判像一个紧箍咒,在他身上越收越紧。不过,他没有停滞做梦,仍旧相信他可以避开这场审判,在它所触及的范围外生活。他哄骗自己他可以通过女人走歪路左道,从法官部里得到些什么(在卡夫卡笔下,女人是人与神之间的贯串衔接),或者通过那名好似和法官有点关系的画家——托钵人。卡夫卡就以这种办法不遗余力地批驳、取笑人类在面对神之秩序时所采纳的郱些绝望、可疑的行为举止。
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 (Edvard Munch,1863—1944)1893年所作的油画《叫嚣》。在这幅画上,蒙克以极度夸年夜的笔法,描述了一个变了形的尖叫的人物形象,把人类极度的孤独和苦闷,以及那种在无垠宇宙面前的恐怖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他主要代表作品之一。
约瑟夫·K的缺点是,他执拗地坚持自己的人类权柄和正当性,而不是一句话都不说地乖乖屈膝降服佩服。他勤学不辍、不断改写给法院的答辩书,每天都想办法向法院证明他都无懈可击、人类的不在场证明,这所有统统努力和“通过法律路子办理”的意图末了全都诡异地落入徒劳无功的陷阱,完备无法到达法院高层。
人类竭尽所能想要和这个各部分不成比例、表面凹凸不平、内部充满抵牾的天下建立关系,然而这统统一点用途都没有,只会造成误会。两者之间不会有任何交集,所有的考试测验只是拐弯抹角,无法切入重点。
在倒数第二章(这仿佛是全体故事的关键),透过监狱神父的寓言,整件事的另一个面相浮现了出来,并不是法律压迫犯人,而是人终其生平在探求“法律的入口”。
看起来,法律彷佛在人类面前隐蔽自己,严密地把自己守在崇高、不可碰触的领域,同时秘密地戒备人类侵入内部盗取神圣事物的意图。在这个美妙的寓言之中,监狱神父拉起了守卫法律的任务。他在诡辩、狡诈和愤世嫉俗的边缘游走,虽然看似和这些东西与世浮沉,但实在这却是他身为一个法律爱好者最为严苛的试炼,他看似否定了法律,但事实上他是为达成法律的目的而做出了最大的捐躯。
审判: 法律是如何入侵人的生命的
在《审判》中,卡夫卡用某种抽象的手腕,向我们展示了法律是如何侵入人类的生命的。他没有用任何现实生活中的个案来诉说它,到末了,我们还是无法知道约瑟夫K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们更不知道,他的人生是为了找到什么样的原形而存在的。
卡夫忙只给了我们一种整体的氛围和调性——人类的生命碰触到至高的神性原形。本书最高的艺术造诣是,卡夫卡为这些人类措辞无法捉摸、无法阐述的事物找到了适当的表达形式,找到了某种物质上的替代品,并且在里面打造出这些事物的构造,至连最眇小的地方都不要遗漏。
“There is hope, but not for us.” - Franz Kafka
卡夫卡在书中渴望向读者通报的这些创造、洞见和阐发,实在并不但是他个人的创见,而是所有时期和国度的神秘主义者的共同遗产。他们总是用主不雅观、随机、特属于某种社团和秘密团体的措辞来诉说这件事。
然而这一次,卡夫卡用措辞的邪术,首次创造出某种平行现实、某个诗意的实体,并且在上面展现了这些事物。虽然他没有讲到这些事物的内容,但是透过这种办法,纵然是最虔诚的神秘主义者,都能感想熏染到那来自迢遥崇高事物的吹拂,对他们来说,《审判》即是他们核心履历的诗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