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月的各种“女性书单”中,关于叶嘉莹师长西席的两本书,特殊引人瞩目。
一本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为有荷花唤我来──叶嘉莹在南开》,其余一本是公民出版社的《我与姑母叶嘉莹》。
生于1924年的叶嘉莹师长西席,是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大家。自1966年开始,叶嘉莹师长西席先后曾被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校邀聘为客座教授及访问教授。1979年始,她每年回中国教书,曾先后应邀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40余所海内大专院校责任教授中国古典诗词。
99岁的叶嘉莹师长西席,传承中华古典诗词近八十载,设帐南开大学逾四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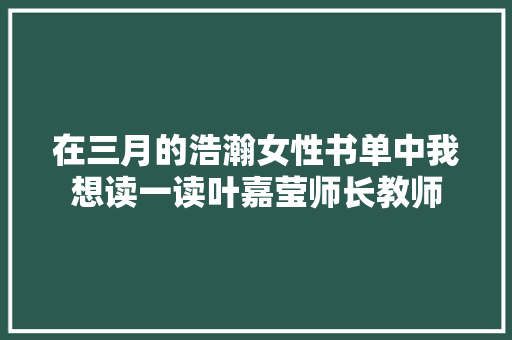
2019年10月19日,南开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一群中文系1982级学子登门拜会叶嘉莹师长西席。师长西席漫忆了四十载授业南开的过往,师生相谈甚欢。末了她满怀期冀地说:“你们出一本我在南开讲学的书给我吧。”
《为有荷花唤我来──叶嘉莹在南开》的编写,动念于此。
《为有荷花唤我来──叶嘉莹在南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如今,翻开这本书,在编后记“在师长西席的感召下”,可一读这本书的由来。
“出一本严明的书不易,给所敬爱的前辈出书不易,给一位登时书柜、名扬海内外的名师出书尤其不易。”对编者而言,这是一次全新寻衅,也是一个重大课题。
在叶嘉莹师长西席“我与荷花及南开的分缘”的领衔下,本书作者最高龄者年近九旬,最年少者才刚二十出头。他们中有专攻中国古典诗词的学者、教授,有听叶师长西席诗词讲座入门并追随多年的“叶粉”,有“文革”后规复高考入学的首批南开学子,有在叶师长西席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事情的助理、老师及由此毕业走出校门的硕士、博士……
编者经历了反复的筛选、润色、删减等工序。受叶师长西席诗词的启示,全书以“客子初从海上来”“谁知散木有乡根”“师弟分缘逾骨肉”“弱德持身往不回”这四句来划分紧张篇章,反响了师长西席从事中国古典诗词教诲,尤其是在南开四十多年的传授教化、研究、创作生涯,让师长西席的生涯脉络、学术造诣、人格魅力更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叶师长西席曾说:“只有返国来教书,是我唯一的、我生平一世的自己的选择。”从《为有荷花唤我来──叶嘉莹在南开》一书中,可以读出师长西席这种选择的执著。
在《为有荷花唤我来──叶嘉莹在南开》有一篇《我与姑母叶嘉莹》,最近,这篇长文也扩展成为一部书,由公民出版社出版,它的作者叶言材是叶嘉莹师长西席的侄子。
《我与姑母叶嘉莹》公民出版社
执教于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中国系的叶言材与叶嘉莹师长西席不仅是亲姑侄,且同为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发展及治学过程中深受叶嘉莹师长西席关照与影响,更是叶嘉莹师长西席受邀返国执教、创办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与中外文化名人交游等主要时候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对叶嘉莹师长西席抱有深刻的理解和朴拙的情绪。
《我与姑母叶嘉莹》不仅生动重现了叶嘉莹师长西席成长于斯、永铭于心的叶氏大家族和察院胡同老宅,回顾了作者青少年时叶嘉莹师长西席归国与家人重聚相伴并游历讲学于祖国各地的珍藏影象,更将叶嘉莹师长西席与中外诸多师友结下深厚情意的知心交游娓娓道来,个中包括陈省身、杨振宁、李霁野、陆宗达、夏承焘、缪钺、邓广铭、陈贻焮、冯其庸、史树青、吉川幸次郎、冈村落繁……
“本来他(作者叶言材)对我的家世平生就比外人理解得更多,而且他在我们家族子弟中,无论所学中文专业或给外国学生讲授中文的职业经历方面,都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与我附近和比较能够理解我‘返国教书之志’的人。”
在《我与姑母叶嘉莹》的媒介中,叶嘉莹师长西席说,叶言材文思敏捷,识见又广,一写起来就下笔不能自休,洋洋洒洒,“他负责和努力地以他的影象补充了我以前一些记述的不敷,这些关于人与事的叙写,使我极为冲动。”
实在,关于叶嘉莹师长西席的人生,有很多图书值得一读,比如《沧海波澄 我的诗词与人生》(中华书局)、《风景旧曾谙 叶嘉莹谈诗论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红蕖留梦 叶嘉莹谈诗忆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有荷花唤我来──叶嘉莹在南开》与《我与姑母叶嘉莹》,则是从他者的视角,讲述了叶嘉莹师长西席的诸多主要人生进程。包括文学记录电影《掬水月在手》的同名书本,也在此列。
2018年6月,在南开大学的迦陵学舍,我有幸聆听过叶师长西席讲诗词,关于她的人生,她与诗词有关著作,须要逐步读起。
【抢先读】
学诗最主要的是学做人
□张元昕
能够成为叶老师的“关门弟子”是我的大幸。叶老师和我们家有很深的渊源。当年我外祖父母编撰《中国历代花卉诗词全集》时,四川大学的缪钺师长西席代叶老师把她的一些诗词寄给了当时在广州的外祖父母,末了收录到全集中。我九岁时,有一次通过家中的卫星电视看到《大家》访谈栏目。《大家》每期都会先容一位在某个领域做出精彩贡献的“大家”,那一期恰好讲的是叶老师的人生。我看后以为叶老师实在太伟大了!
当时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如果我要倒下去,我也要倒在讲台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能让叶老师乐意倒在讲台上,乐意为诗词奉献她的生平?我很郑重地见告我的外祖父母,见告我的母亲,我要随着叶老师学习。
当时外祖母和我各写了一封信寄给叶老师,没想到叶老师真的复书了。她在信中说:“元昕如此爱诗甚难堪得,其所作亦有可不雅观,只可惜未习音律。如有机会见面,我可当面为她讲一讲。”2009 年春天,正是温哥华樱花最美的时令,母亲第一次带着我和妹妹去拜见叶老师。那天下午,我们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二楼的阅览室见到了叶老师。
一开始,我以为叶老师会是一个很严明的人,有点怕怕的。见面后,我创造叶老师是一位慈祥可爱的老奶奶。她第一天请教了我们格律,她先教平仄,在一张纸上用横线代表平,用竖线代表仄。她教我们五言诗平起该当如何、仄起该当如何;如果写七言又该如何;又说平仄并不是去世板的,如果去世记硬背很难写出好诗。
叶老师教导我们,要让自己的诗合乎平仄,就要学会吟诵。教完平仄,她还亲自教我们吟诵了好几首诗,她教我们吟诵的第一首诗是王之涣的《凉州词》。
第一次去温哥华见到叶老师当天的傍晚,叶老师还约请我们一起与施淑仪老师和陶永强状师共进晚餐。随后陶状师在送我们回旅店的路上,听妈妈说我们是专程从纽约到温哥华拜见叶老师的,很是惊异,说难得我们这么恳切。陶状师回家后把我们专程来拜师的事见告了施老师,施老师又转告了叶老师。当天晚上,我们接到叶老师的电话,约我们第二天一起去温哥华的中山公园赏梅。
那天小雨稀疏,略带寒意,叶老师一边一个拉着我和妹妹的手,在公园里漫游。每碰着对联,叶老师都会教我们读,还讲解个中的意思。那些对联,很多都是叶老师所作、谢琰老师书写的。一起走来,看到嫩绿的新柳,或是树上的玉兰,或是阁前的方塘,叶老师都会让我们背出相应的古诗。施老师走在后面跟妈妈说:“你看叶老师本日多愉快,她们三个人在一起真是其乐融融!
”
现在回忆起来,那天该当是叶老师对我们的考试。几天后,妈妈带着我们一起,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叶老师的办公室,正式向叶老师行了拜师礼,三拜九叩。
那年,我十一岁,妹妹九岁。叶老师跟我们说过,她小时候也行过拜师礼。叶老师的尊师重道之心,一贯是我们最敬仰她的风致之一。她生平颠沛流离,所有的东西都丢了,但是她记录顾随师长西席讲课的八本条记,却一本都没有丢失。后来叶师长西席还找到了顾师长西席的女儿,辅导其整理后正式出版了。
2009 年暑假,我们第二次去温哥华,其间有幸和叶老师一起去惠斯勒山度假。那几天,我们和叶老师住在一个房间,我和妹妹睡在客厅的沙发床上,她住在卧室。叶老师担心我们晚上睡不好,起身照顾我们。蒙眬中看到叶老师走出来,给我们盖好被子,她才回去。那么多年的师生关系,实在她是把我们当成她的孙女来对待的。
在温哥华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看书,到了中午十二点半,叶老师会定时去用饭。妹妹耳朵很好,她听到叶老师走路的声音就知道叶老师来了,我们就会跑过去扶着她一起下楼。
叶老师每天都带着很大略的三明治,还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烫过的西蓝花、红萝卜、小橘子,有时候还会有小番茄。她的午餐非常大略,我们也就随着带三明治。现在回忆起那些光阴,真是太美好了。
叶老师吃午饭的时候会给我们讲诗,教我们吟诵,讲墨客的人生,见告我们学诗与做人的道理。有一天她跟我们讲中国的两个半墨客,屈原、陶渊明和半个杜甫。为什么杜甫是半个呢?由于杜甫说过“语不惊人去世不休”,解释他还有和别人攀比的心。人生最高的境界便是反面别人攀比,实现自己内心的代价。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所强调的“内明”:“无求于外,但求于心”。
这种境界恰好对应西方哲学家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他提出人生有七种需求层次, 最高层次便是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当时叶老师拿出笔, 在一张餐巾纸上把selfactualization写给我们。她说陶渊明的诗“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陶渊明不是为写诗而写诗,他直抒胸臆,心里面想什么就写什么,从来没有与任何人攀比的心。他任真固穷、抱洁以终,这样的墨客、这样的风致才是我们当代人该当学习的。我一贯珍藏着叶老师写有self-actualization 的餐巾纸。
叶老师的这些话在我心里种下了种子,那便是学诗最主要的是学做人。通过诗,我们能够感想熏染到古人的高尚风致与教化,感想熏染到他们在面对人生困境时的持守,感想熏染到他们为了空想而不惜奉献统统的精神。
摘选自《为有荷花唤我来──叶嘉莹在南开》
杨振宁师长西席
□叶言材
据我知道,叶师长西席原来与杨师长西席并未曾有过见面的机会,但对付杨师长西席的大名早已久仰。1991年秋冬之际, 杨师长西席来到南开, 听说叶师长西席也在南开,就请外事处的逄处长引见。逄处长先给叶师长西席打了电话,征询是否方便?然后陪同杨师长西席来到专家楼叶师长西席的房间拜访,文理两位大家终于见面了。听姑母说:当时房间里没有茶水可以招待杨师长西席,只好给杨师长西席斟了一杯自己煮的“山楂水”。杨师长西席说自己曾读过叶师长西席的著作和诗词……文理两位大家畅谈了许久。
其后,因杨师长西席的生日附近,杨师长西席特意约请叶师长西席出席“祝寿会”。叶师长西席便作了四首绝句送给了杨师长西席,以表贺寿之意。1992 年6 月9 日,逄处长为杨师长西席的七十华诞举办了一场大型庆贺会。会上,杨师长西席带来了叶师长西席送给他的那四首诗,并已请人用羊毫书写了下来,还执意约请叶师长西席上台讲几句话。当时叶师长西席说:本日来参加杨振宁师长西席“祝寿会”的都是物理学家,有杨师长西席的同学、同事、同行的学者,而我是学中文的,但我可以和杨师长西席认一个“半同”的关系,由于他所上的崇德学校和我上的笃志学校是同一个教会办的,是兄妹学校,男校叫“崇德”,女校叫“笃志”,而且,他上崇德学校时正是我上笃志学校的时候。
叶师长西席为杨师长西席写的四首绝句如下:
《杨振宁教授七十华诞口占绝句四章为祝》
卅五年前仰大名,共称华冑出豪英。过人聪慧通天宇,妙理推知不守恒。
记得高朋过我来,年时相晤在南开。曾无茗酒供谈兴,惟敬山楂水一盃。
谁言文理殊途异,才悟能明此意通。惠我佳编时展读,博闻卓识见高风。
初度欣逢七十辰,华堂多士寿斯人。我愧当筵无可奉,聊将短句祝长春。
以前只是听说姑母与杨师长西席相识,而且不止一次地说过“杨师长西席的文科旧学功底很好”。我想杨师长西席作为一位天下著名的物理学家,能够如此爱好古典诗词,实在是当代自然科学研究者们的榜样,心中钦佩不已,一贯愿望有机会能够拜见。
2004 年10 月21 日,南开大学为叶师长西席庆贺八十生日,陈省身师长西席、冯其庸师长西席、文怀沙师长西席等各界大家都到场贺寿,当然杨师长西席也来了。但是杨师长西席是在前一天下午到达的,并与叶师长西席一起接管了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的采访,文理两位大家进行了一场极具历史意义的对谈,内容是:理工科的人是否也该当学习中国古典诗词。对谈中,杨师长西席还讲自己正在研究《易经》,认为它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将统统繁芜的事物归纳为大略,与西方的将看似大略的事物细化为繁芜的演绎化思维完备不同……
在场旁听的不但有我,还有我的同学傅秋爽、张力,以及张力的太太丁伶青。
2008 年12 月尾,杨师长西席约请叶师长西席去他家做客,然后一起到清华园“甲所”餐厅吃午饭。那时我恰好也在北京,姑母便带我一起去了。那日冬雪初霁,清华校园里白茫茫一片,显得极为优雅干净,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走进清华。
摘选自《我与姑母叶嘉莹》
本文为钱江原创作品,未经容许,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统统作品版权利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法律路子深究侵权人的法律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