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也是襄阳古代诗歌的源头。反响襄阳公民生活的诗歌,见于《诗经》中所收录的以“风”为种别、以“周南”、“召南”为地域区划的诸诗中。个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诗经.周南.汉广》一诗:“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是一首樵夫唱给俏丽无比、自持崇高、可望而不可即的心上人“游女”的山歌,并由此衍生出流传于以襄阳为中央的汉水流域的“汉水女神”的动人传说。据获襄阳市批复的鱼梁洲(2015—2030年)培植方案,作为襄阳“城市绿心”的鱼梁洲,未来将在环岛景不雅观带江东一侧树立“汉水女神”的巨大雕像,这个颇富诗意的汉水文化具象性标志符号,将成为继万达广场诸葛亮巨型铜像、岘山孟浩然巨型浮雕之后襄阳的又一文化地标建筑。
在襄阳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进程中,诗歌犹如百花园中一支芳香四溢、艳丽无比的奇葩,引领着襄阳文学的提高方向,尤其在先秦期间、李唐期间和现当代期间,更以其刺目耀眼如炬的诗歌名家及辉煌残酷的艺术造诣,掀起了襄阳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次创作高潮,造诣了令襄阳人引为骄傲的中国文艺史的佳话。
襄阳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高潮涌现于先秦期间。期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本土墨客宋玉、王延寿,以及客居襄阳的“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
宋玉是战国末期辞赋家,襄阳宜城人,与精彩爱国墨客屈原齐名。他不仅以楚辞名篇《九辨》开启了中国文学史“悲秋文学”之先河,而且以想象丰富、辞藻富丽的《高唐赋》《神女赋》等赋作承前启后,为中国文学史上新体赋的形成奠定了坚实根本。后被人们广泛引用的“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宋玉东墙”等典故皆出于其辞赋。同为宜城人的王延寿在中国文学上霸占主要地位。他的名作《鲁灵光殿赋》有“近代辞赋之伟”的美誉,对汉赋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北朝期间精彩的文论家刘勰在其光辉著作《文心雕龙》里,也因此将王延寿与司马相如等十人并称为“辞赋之英杰”。文学造诣位列“建安七子”之首的山东绅士王粲(字仲宣),在南下投奔刘表、客居襄阳十年间创作了不少颇具影响的作品。其代表作《登楼赋》作为汉末抒怀小赋的代表,以其“气格遒上,绵意绪邈,骚人情深”的艺术特质,受到人们的极大推崇,被刘勰称为“魏晋之赋首”。现耸立于襄阳城东南角城墙之上的仲宣楼,即为纪念王粲在襄阳作《登楼赋》而建,为襄阳标志性文化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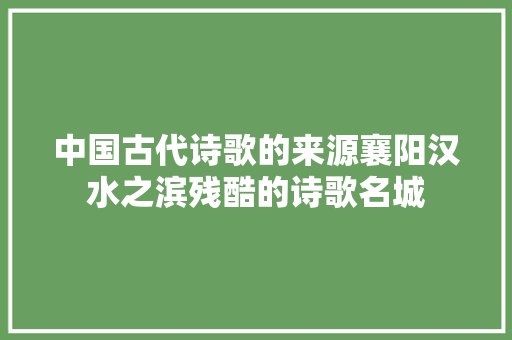
古代襄阳诗歌的第二次创作高潮涌如今唐代。唐代的襄阳诗歌,是襄阳诗歌发展史、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曲华彩乐章。这一期间,襄阳诗坛可谓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佳作如林,呈现了杜审言、孟浩然、张继、皮日休等在中国诗歌史上霸占主要地位的本土大家。以名篇《登襄阳城》为家乡人熟知的杜审言,在五言律诗的创作上取得了巨大造诣,被学术界视为五言律诗的奠基人。张继的诗歌紧张是游记游览、酬赠予别之作,最著名的是那首七言绝句《枫桥夜泊》。长期隐居鹿门山的皮日休,是襄阳文学史上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文学家,他的诗歌和小品文在中国文学史上霸占主要地位。
最令襄阳人骄傲的是诗坛巨擘孟浩然。他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首创者和领军人物,也是襄阳历史上第一位通过诗歌办法大力宣扬家乡自然山水的墨客。其《秋登万山寄张五》《与诸子等岘山》《夜归鹿门山》《登望楚山最高顶》《早春汉江漾舟》《高阳池送朱二》等诗篇,皆为描摹歌颂襄阳山水之佳作。值得称道的是,在唐代数以千计的墨客中,孟浩然还是以布衣身份被天子诏令入京第一人。此事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一大新闻,极大引发了青年士子们的写诗激情亲切。孟浩然生平,诗作等身。收录其诗作最多的是郑振铎汇校本《孟襄阳集》,共268首。据著名孟浩然研究专家、湖北文理学院王辉斌教授考证,剔除伪作,真正为孟浩然创作的诗作大约在255首旁边。孟浩然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除山水田园诗外,举凡唐诗中所常见的宴游、送别、酬答、歌咏、怀思、登览、行役、感遇、咏物、闺情等题材,孟集均有阅读。孟诗中有许多随处颂扬的名篇佳作,其《春晓》更是妇孺皆知,为亿万读者熟习和喜好。孟浩然诗歌淳厚真切,形成了融清幽、雅丽、雄浑于一体的独树一帜的诗风,具有极高的审美代价,大墨客杜甫的诗句“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十二首之六)是对孟诗艺术代价的高度评价,也从一个侧面反响了人们对孟诗的喜好程度。
由于孟浩然及其首创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巨大影响,唐代期间的襄阳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重镇和诗歌中央,吸引了浩瀚的文人墨客和诗歌大家前来拜会、宦游。大墨客李白在旅居湖北安陆期间,与孟浩然有过多次交往,不仅以“吾爱孟役夫,风骚天下闻”(《赠孟浩然》)之句表达了对孟浩然的由衷敬仰与爱戴,还留下了《襄阳曲四首》《大提曲》《襄阳歌》《赠孟浩然》等许多歌咏襄阳的富丽诗篇。此外,王昌龄、王维、白居易、韩愈、温庭筠等大批文学名家也曾来襄阳游览,并由此产生了洋洋大不雅观的歌咏襄阳的不朽诗作,极大地促进了襄阳诗歌和唐代诗歌的发展繁荣。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迄今的现当代期间,是襄阳诗歌创作的第三次高潮。
当代襄阳诗歌的精彩代表是张光年。张光年笔名光未然,襄阳老河口市人,中国当代著名墨客、文学评论家。作为墨客,他的代表作是随处颂扬的歌词《五月的鲜花》和气势磅礴的组诗《黄河大合唱》。后者被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谱曲成为民族交响史诗而被广为传唱。作为评论家,其造诣紧张表示在针对郭沫若、臧克家、李瑛等当代著名墨客诗作的评论文章。
从1949年新中国出身至今的当代期间,是襄阳诗歌开启新征程、实现新超过的辉煌历史期间。本期的襄阳诗歌经历了“新中国”、“新期间”、“新世纪”三个发展阶段。
新中国襄阳诗歌起步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1952年苏光照揭橥在《湖北文艺》的《凤英回外家》,拉开了当代襄阳诗歌创作的序幕。该诗作通过凤英向妈妈报告土改使农人物质翻了身、现在农人又要文化翻身的喜讯,激情亲切歌颂了新中国出身后屯子的新生活。1955年,罗成秀、王化郁先后揭橥诗作《新西湖颂》《再也不能当睁眼瞎》,以昂扬激越的诗情赞赏了鄂西北公民在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的业绩。1958年战士墨客乔林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白兰花》,生动刻画了一位纯朴、武断、刚毅、机警的屯子青年妇女形象,歌颂了大别山根据地公民对抗击日寇侵略和国民党发动统治所表现的大胆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该诗1958年由公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得到墨客郭沫若的高度评价,在全国诗坛产生了较大影响。
1950年代末,同全国的诗歌状况相同,在狂热激进的“大跃进”期间,全民写诗,大家是歌手,表面繁荣热闹、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不雅观主义情调、充满豪言壮语,实则内容假大空的襄阳新民歌乏善可陈。而襄阳籍墨客白云天创作的叙事诗《神鱼的故事》则是难得的收成。诗作以盛行于湖北秭归的民间神话传说为原本,讲述了屈原投江后被洞庭神鱼运回屈原故里秭归与亲人相见的动听故事,想象丰富,文笔幽美,充满神奇瑰丽的浪漫色彩。进入1960年代后,由于文艺界的左倾思潮愈演愈烈,襄阳诗歌创作的道路也越来越窄。终极不可避免地走入去世胡同。
新期间的襄阳诗歌和新中国三十年比较,无论在墨客数量、整体实力,诗歌数量与质量,还是在作品题材的广阔性、主题的深刻性,墨客的艺术个性化、创作风格的多样化等方面,都有长足发展和进步。
本期生动在襄阳诗坛的中坚力量,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乃至更早的一批中年墨客,如吴鄂东、龚正荣、李圣强、黄耀辉、彭泉瀚、刘蒂、任金亭、彭广全、汪光房、毛翰、金口哨等。他们成长于新中国成立之后高亢激越的颂歌时期,经历了颠三倒四的“文革”岁月,也经由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运动的心灵洗礼,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对现实与历史有着深刻的把握与洞悉;在诗歌不雅观念上,深受“托物言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中国传统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同时也多多少少受到了改革开放后吹进国门的西方当代诗风的熏陶。因而,他们的诗歌在思想与宗旨上,表现出对现实与历史的批驳性与反思性;在诗艺上既表现出直抒胸臆又委婉蕴藉的古典风格,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借助于意象营构传情达意的当代审美意见意义。
这些中年墨客文学功底深厚、诗艺成熟,本期相继奉献了自己的代表作,例如,吴鄂东的怀人抒怀诗《曾卓》,龚正荣的长篇传奇叙事诗《爱情与恶欲》,黄耀辉的写景短诗《武当晨兴》,李圣强的诗集《远山》及乡土题材与历史题材的诗作《半店风情》《霸王之醉》,彭泉瀚的诗集《彭泉瀚朗诵诗歌集》及书写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朗诵诗《中国:灾害孕育着俏丽》,邓家顺的诗集《中国军营》,毛翰的政治抒怀诗《钓鱼岛》,彭广全的诗集《告别》及写景抒怀诗《茶山风景》《水韵襄阳》等,“爱的歌者”任金亭的诗集《母亲树》《爱我所爱》,“青春墨客”汪光房的诗集《我给青春一个吻》……这些精良诗作为襄阳诗歌增长了光彩,也扩大了襄阳诗歌在全国的影响。
在本期,与上述中年墨客在诗坛并肩携手同行的,因此宋明发、叶青、赵黎明、张卫华、张建成、雪耕、马安学、谢冰凌、郭付才等为代表的60后墨客。
宋明发著有诗集《爱情岛》《无语的西部》《走出西部》等多部。其诗作的最大特点,是用奇异的语汇形成表意的陌生化,用跳跃的节奏制造言与意的分裂,用隐含的情绪线索串联起密集的意象,让读者追寻着墨客的非常规逻辑用生活履历和个性化感悟去补充陌生化意象言外之意的空缺,从而实现或差异化或趋同性的文本解读与诗意增值;叶青(1963——1996),揭橥诗歌100余首,代表作为借助范例意象“瓷器”表达爱国情愫的《中国:CHINA》;张建成出版有诗集《一条河流的情歌》,其诗歌深受法国象征主义墨客波特莱尔《恶之花》的影响,并在其《致白色——在赤日炎炎中长久痴迷地走着的女人》一诗中有所反响;杨学耕,笔名雪耕,著有诗集《我歌我心》,诗作多次获奖;马安学著有诗集《锦绣的日子》,诗作入选全国多个诗歌选本;谢德瑛,笔名谢冰凛,著有诗集《微笑的红罂粟》《迢遥的家园》,作品多次获奖并当选载;郭伏才,笔名含笑,诗集《风笛演奏者》有一定影响。
上述60后墨客均接管过良好的大学(或硕士研究生)教诲,知识构造较为完善,创作起步早,深受当代美学不雅观念和中西方当代诗歌影响,在传承中国古典诗歌血脉的同时,更追求在诗歌中表现当代意识和艺术个性。其诗作呈现的整体艺术风格极其当代诗歌理念,与同期中国诗歌整体发展走向高度契合,充分表示了襄阳墨客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新意识。
进入二十一世纪,襄阳的诗歌创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墨客军队不断壮大,诗作数量大幅增多,作品质量显著提高,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呈现出诗体多样、题材多维、手腕多变、主题多元的新局势。
墨客军队是诗歌创作数量质量和整体繁荣的根本担保,新世纪以来,襄阳的墨客军队空前壮大, 涌现了以襄阳市诗词学会为依托,以焦泽浩、程发义、孟凡、高山嵩、李邦政、罗辉、严爱华、郭明强、徐敏、舒敏、王祖泽等为代表,专注于旧体诗词创作的老年诗群;由70后80后构成的青年诗群;由中、青、少不同年事段墨客组合而成的女性诗群;其余还呈现出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出生的新生代墨客。形成了老中青少四代墨客相互雕琢、齐声共唱,旧体诗词、自由新诗交相照映的创作新格局。
由70后、80后构成的青年诗群,代表墨客紧张有朱华杰、李征(笔名大刀李征)、李红平(笔名满江红)、周红南、毛平生、李小波、田升剑(笔名田晓隐)等;女性诗群的代表墨客则紧张有左艳琳(笔名不染、不染之荷)、阎雯、李默、张洁、尤晓红、刘诗笛(笔名陌峪)等。
阵容齐整可不雅观的墨客军队,为新世纪襄阳诗歌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经由长期的费力耕耘和创作积累,本期间襄阳墨客们纷纭推出了自己的诗集,为新世纪襄阳文学奉献了有分量的成果。如2000年出版的杨丽的诗集《黎明之约》、刘文生的《黑夜的歌谣》、蔡嘉彬的《鸟群飞临》;2001年出版的宋明发的《走出西部》;2002年出版的大刀李征的《大刀李征短诗选》、刘传国的《银迪霞歌》;2004年出版的晓航的《蝴蝶人诗选》 、尚建国的《天空有鸽子飞过》;2005年出版的文爱艺的《雨中花》《太阳花》、任金亭的《爱我所爱》;2007年出版的毛翰的《天籁如此》;2009年出版的刘传国的《竹笛情歌》、竹丫子的《我们的天下水草丰满》、王俊楚的《动感村落庄》;2011年出版的黄耀辉的《凡心韵语》、汪光房的《我给青春一个吻》;2011年出版的张洁等女墨客的诗歌合集《十二女子诗坊》、不染的《照见自己的光亮》;2012年出版的朱华杰的《无可奈何花落去》、邱述安的《仲春蝉鸣》、徐先念的《七彩瀑》、蔡嘉彬的《风花雪月》;2013年出版的《彭泉翰朗诵诗歌集》、李小波的《光阴里的呓语》、江南客的《曲线逃离》、李道立的《生平在等》、金呼哨的《方言的故乡》、吴鄂东的《方言的故乡》;2014年出版的张洁的《草上的玉轮》,李道立、阎雯、毛平生等的诗歌合集《诗韵南漳》,刘诗笛的《彼岸花开》,周红男的《怀念一座城池》;2015年出版的焦泽浩的《韵语新声》、程发义的《乡情集》、孟凡的《心曲》《古城新韵》、李邦政的《岁月如歌》《金秋漫吟》、黄耀辉的《那一片丛林》、周少诚的《汉岘吟啸》等。
据不完备统计,新世纪襄阳墨客出版的诗集达50部以上,是襄阳新中国三十年、新期间二十年前两个期间20部诗集总和的2.5倍,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世纪襄阳诗歌的整体水平与实力。
“一江碧水穿城过,十里青山半入城”,这是武侠大师金庸眼里的山水之城; “谁能持我诗以往,为我先贺襄阳人”,这是宋代文豪欧阳修笔下的诗歌之都。如今,襄阳的墨客们,正伴随着新世纪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斗志昂扬,阔步向前,以他们深奥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气冲霄汉的豪迈诗情,书写着新时期的崭新诗篇,用他们云蒸霞蔚的华彩乐章,书写着襄阳文学的新传奇,把襄阳这座汉江之滨的诗歌名城装点得更加残酷夺目!
原标题↓
《襄阳:汉水之滨残酷的诗歌名城》
向作者张治国致敬致敬!
������������
感谢您为襄阳,为文学,为社会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