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一首,则因此视觉图画为主的绝句。整篇便是一幅图画,也没有在第三句、第四句让句法发生变革,更没有从描述转入抒怀,可以说是范例的诗中有画的精品。当我们说诗中有画的时候,意思是,诗与画作为艺术形式,其规律有共同性。但是,任何共同性中一定包含着差异性,统一中必有抵牾。德国文论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早就论述过诗与画的抵牾。当代艺术理论一贯强调:画是视觉艺术,是共时直不雅观的;诗是措辞符号艺术,是历时的,二者的规律有所不同。以是在苏轼说了诗与画的同一性往后,明朝人张岱也说,诗中之画,画中之诗,都不一定好,而且有些好诗也画不出。他说“蓝田白石出,玉川红叶稀”还可以画,而“昂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难画了。
诗与画的抵牾,紧张是诗的历时性和画的瞬时性的抵牾。画只能是静态的,而诗则可以是动态的。苏轼这首诗,当然是一幅图画,但是他的追求彷佛便是打破图画的静态。
第一句,“黑云翻墨未遮山”,倒是一幅图画,大致符合静态的规律。好在很有特点:黑云黑到像打翻了墨水一样,该当是很浓重的。但又不是,只遮住了一部分山。这解释雨势来得很猛,还没有遮住全部。下面的“白雨跳珠”,很明显,是用色彩上的比拟,写雨的特点。不仅仅是云黑,而且有雨白,其最白者为雨珠。“乱入船”,活蹦乱跳着,闯进船来。这里有一个疑问:船从何来?题目上写的是“望湖楼”,不是在楼上吗?该当是乱入“楼”才对。但是,文献没有给我们支持,只能设想,这是墨客的想象,或者是他在望湖楼上喝醉时想起当时乘船游湖时的情景。好在诗的空间想象性是比较浮动的。但这却是画所不许可的,在船上是一种画法,在楼上又是一种画法。这就解释,虽然是诗中之画,所遵照的却仍旧是诗的规矩,好就好在以诗的规矩打破了画的规矩。如果一味拘泥于画,就不但这一句成了问题,而且下面的诗也没法写了。
如果说,第一、二句的“黑云翻墨”与“白雨跳珠”,是比较微不雅观的比拟的话,那么第三、四旬“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则与前两旬明显形成宏不雅观景不雅观的双重比拟。第一重仍旧是色调的比拟,浓黑的云忽然消逝,变成了通亮的天。这个比拟是比较强烈的,由于“水如天”,不但和原来的浓云遮山形成比拟,还写出了水天一色,分外透亮。但光是这样的比拟,还不能算是很精彩,由于这在宋诗中,是比较普通的技巧。苏轼的才华集中表示在第二重比拟,便是从相对静中有动的视觉画面,经由大动态的风云变幻,末了又定格在静态的“水如天”的画面上。这样的迁移转变,之以是给读者以深深的触动,是由于这里有一个心灵感应的动态过程。从色彩的黑白对转,到心灵的由动到静的变幻,使得本来静止的画面,变成了诗所同化了的“动画”。而这种“动画”,对付墨客的内心来说,是非常奇妙的霎时。这是画所无能为力的。外在的大变动,隐含着内在的隐秘的颤动,这就以诗的优长战胜了画的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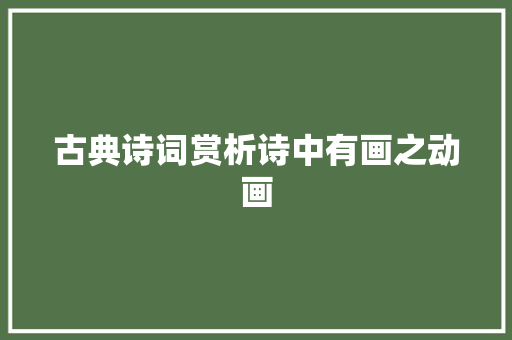
对付中国古典式抒怀来说,直接抒怀是比较少见的,情常常与感联系在一起,“情绪”一词可能由此而生。而诗缘情,情的本性便是动的。诗之感,与画之感的不同,就在于动。情之特点,在感而能动,故有“冲动”之说(冲动比之感触,更有情绪的内涵)。觉得或者感触只有“动”起来,才能表现感情,动有“动情”或“情动”之语。《诗大序》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要“动”起来,才能借措辞而成形。苏轼在以动画写情方面,彷佛是故意为之的。他的《有美堂暴雨》绝句有云:“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句旬都是画面,幅幅画面都是“动画”。没有动态,就没有苏轼豪放派的气概了。这样的“动画”艺术,在宋诗中也不少见。王安石有《书湖阴师长西席壁》一诗,也是诗中有画的代表作: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推门送青来。第五章古典诗词美学批驳 357前面三句险些都是静态的画面,当然,个中多少有些动的暗示,如“扫”、“栽”、“护”,三字都是动词,但均为静态画面,可以忽略;到了末了一句,写的是门外的青山,明明是静止的,但王安石把它写成了动的,而且是大幅度的运动:远远的青山居然主动闯进门来。这更可以解释:诗中有画,该当是心灵之“动画”,绝非仅仅是可视之静画。心灵之动画,更妙在可视之静态中蕴涵着不可视之“动感”。这种动感是“动情”(或情动)的结果,也是读者“冲动”的由头。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这首诗只有二十个字,全部是描述,供应了一幅图画。《大历诗略》说它:“宜人宋人团扇小景。”意思是只有图画、视觉形象,没有直接抒发的身分。但是,这首诗的好处,肯定并不是只有视觉形象,如果只是画图,只是视觉的美,就肤浅了。这是中国古典抒怀诗歌中的一种风格:通过图画来抒怀。正由于抒怀不同凡响,这首诗才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磨练,本日的读者仍旧不难熬痛苦到作者感情的传染。类似这样全篇都是图画的绝旬名篇举不胜举,王维的《田园乐》便是一例。此外,杜甫的《绝句四首》之一:两个黄鹂呜翠柳,一行白鹭上上苍。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也因此图画来抒怀的,却并不能列为上品。那么刘长卿这一首的好处究竟在哪里?在这首诗的视觉画面中,有没有超视觉的成分?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情致,模糊渗透其间?要把这些说清楚,相称不随意马虎。历代诗话,对之赞不绝口。有的赞其“清”“却不寂寞”(《批点唐音》),有的称其“凄绝干古”(《唐诗正声》),有的更说“无限凄楚”(《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所有这些评论,只管意见互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除了《大历诗略》认为它是一幅画图以外,其他都认为此诗中有一种情致,挺精彩的。
但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情致,却不很随意马虎说得清楚。
“日暮苍山远”,关键在一个“远”字。苍山为什么远?如果认为只是写景,就只能说,这是写实。青山由于日暮,光芒暗淡,而变得模糊了,这是光的效果。但是这句话中,还含着更多的意思,这就要联系诗的题目“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来思考。“逢雪”,这是很主要的。日暮,而且又下雪了,苍山,青色的山,当然就模糊了,产生迢遥的觉得。在这样一幅图画中,那暗淡的光芒,是不是暗示着心情的暗淡?下雪了,天快黑了,在这一幅图画中,空间那么广阔。远景镜头,是不是暗示着,人在这样阔大的空间中,显得比较dx?是不是感到有一点压力?投宿何方呢?是不是有一点四顾茫然,乃至有点焦虑的觉得?以是这第一句,并不是纯粹的描述,在画面上隐含着模糊的茫然、焦灼的感情。
“天寒白屋贫”,又是一幅图画。从句法上来说,和前面那一幅是并列的。但是,它们不是分裂的。由于两幅图画,在形态上是同等的。白屋,一样平常表明,都说是贫寒人家的屋子,但是不是还有一点雪下在屋顶上的效果?和日暮苍山一样,同样是大空间,冷色调,暗淡的感情。从标题上“逢雪宿……”,就可以知道,这是投宿了。在一片苍茫、在冷色调的图景之中,从散文思维的角度来说,这多多少少该当有一点安慰吧。然而,墨客却回避了这样的情致。为什么呢?彷佛以为还有比这更有特点的,也便是更主要的:柴门闻犬吠。在这一片冷色调的画面之中,溘然来了一声狗叫。意脉在这里发生了默默的迁移转变,是不是可以融会得到?本来视觉画面不但是冷色调的,而且是无声的。这一声犬吠,带来了一点热闹,视觉画面就转向了听觉,无声就转向了有声。“犬吠”在汉语里,是属于“鸡犬之声”,其文化韵味是人间的生活气息。这种颇具热闹气息的声音,冲破了视觉的生僻,意脉的内在蕴藏,就暗暗地转化了。这便是一声狗叫之以是能传染读者的缘故原由。接下来:风雪夜归人。这一句,从直觉来说,更加精彩。为什么呢?第一,刚刚感到听觉美好的读者,又一次被墨客带进了一个画面:归人,是在黑夜和风雪交加的背景上涌现的。第二,墨客不让这个场景发出任何声音,却把默默的安慰、无言的温暖留在画面之中,于结束旬,不作结束之语,以延长读者的想象。《唐诗笺注》说:“上二句孤寂况味,犬吠人归,若惊若喜,景致入妙。”由此可知,虽然是一幅视觉图画,但个中隐含着的情绪,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视与听、寒冷与温暖、孤寂与安慰的意脉转化。
以画面和声音交织而取胜的唐诗绝句,还可以举出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也是一幅图画。前两句写静,细细剖析,有两种静,一种是外部的景物静,一种是内在的心灵静。内心不静,怎么会感想熏染到桂花落下来?这样的内心,不但静,而且是不是和春山一样有点“空”?下面两句,还是写静,但如果还是从画面上、视觉上去写,就可能是动,以动衬静,这就可能缺少变革,陷入单调了。王维转向写听觉之静,不因此动来衬,而因此声来衬。“月出惊山鸟”,很精彩。精彩在什么地方?精彩在玉轮出来了,月光移动了,本来是没有声音的,是悄悄的,却惊动了山鸟。这便是从视觉之静,转入听觉之静。视觉之静,是相对付物体之动的,而听觉之静,是相对付声音之动的。春山安静到玉轮稍有变革,就会把小鸟惊醒。小鸟不是被声音惊醒的,而是被月光的变革惊醒的。这种效果解释,山里是多么的宁静。“时鸣春涧中”,“时鸣”,是断断续续地叫,以有声来衬托无声,在一座大山里,有一只鸟叫起来,全体山里都听得很清晰。可见山里是多么安谧了。同时,不可忽略的是,能够聆听这么精细的声音的人,他的内心又是多么宁静,多么精细,多么空灵。
这里,人的感想熏染和大自然的状态是高度统一的。这种统一,不仅仅是诗学的,而且是佛学的。这种状况,是内心没有任何顾虑,没有任何包袱的人的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