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1949年生于江苏无锡。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教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江苏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江苏省社科名家,“书喷鼻香江苏”形象大使。
最近,莫砺锋教授在《群众·大众学堂》刊文,原题为《唐诗宋词:闪烁文化自傲的光芒》。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与基因,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湛,个中最主要的是包括思维办法、生活态度和代价判断在内的精神承传,那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五千年文明史中蕴含的正能量。
得益于汉字超强的表达功能和稳固性子,中华先民的业绩及心迹相称无缺地保存在古代文籍中。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各种书本,便是传统文化精神的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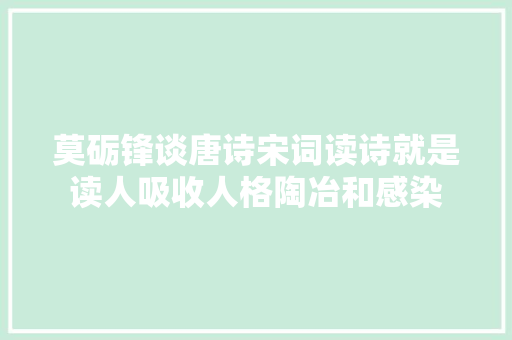
然而古籍汗牛充栋,我们该当从何入手呢?我首先推举中国古典诗歌,即从《诗经》《楚辞》开始的中国古典诗歌。
读诗是理解先贤心态的最佳路子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和颜悦色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弘大雅之响。故陶潜多本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读诗便是读人,阅读那些长篇短什,古人的音容笑脸如在目前,这是我们理解先民心态的最佳路子。
读者或许会有疑惑,难道古诗中没有虚情假意或浮夸伪饰吗?当然有,但是那不会影响我们的阅读。金代的元好问曾讥评晋代墨客潘岳:“心画心声总失落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的确,潘岳其人热中名利,谄事权贵,竟至于远远地看见权臣贾谧的车马即“望尘而拜”。可是他在《闲居赋》中却自称“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这样的作品,怎能取信于人!
与潘岳类似的墨客在古典诗歌史上并不罕见,例如唐代的沈佺期、宋之问,宋代的孙觌、方回,明代的严嵩、阮大铖,皆是显例。但是此类墨客只管颇有才华,作品的艺术水准也不弱,毕竟流品太低。除非用作学术研究的史料,他们不会进入当代人的阅读视野。至于那些一流的墨客,则绝对不会涌现这种情形。
古人著述,本以“修辞立其诚”为原则, 并明确反对“巧语乱德”, 更不要说因此言志为紧张目标的诗歌写作了。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华民族在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秀的传统,便是人品与文品并重。
经由历代读者的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墨客,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他们的作品一定是第一等真诗。他们敞愉快扉与后代读者羞辱相对,我们完备可以从其作品中感想熏染墨客们真实的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地体会传统文化的精神。从《诗经》《楚辞》到明清诗词,全体中国古典诗歌史都具有很高的阅读代价,如果兼顾作品的经典意义、阅读难度等成分,则唐诗宋词应是我们的首选阅读工具。
唐宋词中的入世精神
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期间,五七言各种诗体都在此时达到了繁盛的阶段。唐朝墨客精彩代表是李白和杜甫。李白激情亲切讴歌现实天下中统统美好的事物,而对个中不合理的征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歧视。李白诗中所蕴含的追求解放、追求自由的精神,虽然受到现实的限定却齐心专心要征服现实的态度,是中华民族反抗阴郁势力与庸俗风气的强大精神力量的表示。以是李白诗歌虽以浪漫想象为紧张外表特色,但实在仍含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李白诗风激情亲切旷达,长于利用想象、夸年夜等手腕,措辞风格清丽自然。
与李白齐名的杜甫在青年时期也受到盛唐诗坛的浪漫氛围的深刻影响,但是安史之乱前夕的阴郁现实使他从盛唐浪漫墨客群体中游离出来了。他以复苏的洞察力和积极的入世精神来进行诗歌创作,为安史之乱前后的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过程描述了生动的历史画卷,对“豪门酒肉臭,路有冻去世骨”的阴郁现实进行入木三分的戳穿和批驳,杜诗因而被后人称为“诗史”。杜诗中充满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中积极成分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情的形象凸现。在艺术风格上,李白诗挥洒快意、洒脱旷达,杜甫诗精益求精、沉郁抑扬,对后代诗歌的审美风尚树立了两个双峰并峙的典范。
词这种分外的诗体产生于初盛唐,到宋代发展成一代文学之胜,宋词成为文学史上与唐诗交相照映的诗体。宋词名家辈出,流派浩瀚,造诣最高的词人有苏轼和辛弃疾。苏轼在词史上首先冲破了晚唐以来词专写男欢女爱的艳情的局限,对改造词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但大量写作抒怀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而且在描写女性的传统题材中一扫脂粉喷鼻香泽,从而完成了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怀诗的转变。苏轼的另一贡献是在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长了高昂雄壮的成分,并使词的措辞风格涌现了豪放、洒脱的新成分。
到了南宋,时期的动荡引起了词坛风气的巨大变革,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的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续了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年夜方冲动大方和沉郁凄凉两种方向充足了豪放风格。苏、辛常被看作豪放词人,但是他们也善于写婉约风格的词作。从总体上看,宋词的特色是题材走向上看重个人抒怀而不是反响社会现实,其风格则方向于委婉蕴藉、深情缅邈,这种美学特色也反响了中华民族传统审美思想的一个侧面。
那么唐诗宋词对付当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代价?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便是儒家说的“诗言志”,这在《尚书·尧典》中就已涌现。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的理论。有人认为“言志”倾向严明、正大的主题,“缘情”则是倾向抒发那些个性化、私人化的情绪,二者是对立的关系。
但是从唐诗与宋词的实际来看,“言志”和“抒怀”并不是对立的。初唐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这解释情与志在唐宋人看来是一个观点。比较笼统地阐明,情志便是指一个人的内心天下,包括对生活的感想熏染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代价判断。
既然如此,唐诗宋词的内容就跟当代人就没有什么间隔,由于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绪、基本人生不雅观和基本代价不雅观。比如对真善美切实其实定和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的英雄行为的赞颂,唐宋人如此,当代人也如此。以是唐诗宋词中的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绪、思考和代价判断可以毫无阻碍地通报到本日。
此外,唐诗宋词年夜小无遗、真切生动地展现了先人的生活情景,以及他们的生活态度。唐诗宋词中蕴含着美好的人际情绪,比如孟郊的《游子吟》对母爱的歌颂,杜甫诗中对儿女的款款深情,都是动听至深的真情流露。又如歌颂友情与爱情,这是唐诗宋词中发展得最为充分的一类主题。
由于唐宋的墨客词人在抒写情绪时都是通过详细、生动的生活情景来进行的,以是会给当代读者留下极为真切的在场之感,比如与朋侪或情人的离愁别恨,都是通过环境陪衬、情景描述来抒写的,作品中会展现出详细的场景,使当代读者身临其境。
柳永写一对情人的离去:“寒蝉悲惨,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摧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情景是如此生动,情绪是如此真切,读来动听肺腑。我们阅读唐诗宋词,早年人的生活情景中得到启示,就可以生活得更从容、更优雅,从而更细致地品味人生的意义和美感。
诗词传情提升人格境界
当然诗宋词对付当代人的最大意义是个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提升我们的人格境界,对我们有巨大的教诲浸染。读诗的终极目标便是读人,阅读唐宋时期的大墨客、大词人,谛听他们的心声,感想熏染他们的脉搏,就能接管人格方面的熏陶和传染。
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的诗歌,展现了从始至终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他24岁离开江油,仗剑出蜀,英气干云。一贯到他61岁,虽已老病交加,但仍想从军建功立业。可以说,李白生平斗志昂扬,从未精力萎顿。他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民气抱负。
只有李
这样的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的诗中不是没有苦闷、牢骚,但末了的基调始终都是昂扬奋发的。比如《行路难》,详细描写了道路困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以至于发问“多歧路,今安在”,但此诗的末了两句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生平中只有短短几年作翰林供奉的经历,但他从来不因自己的布衣身份而以为低人一等,他决不在王公大臣面前卑躬屈膝,相反是平交王侯。
总而言之,李白是诗国中独往独来的一位豪士,他充分表示了浪漫乐不雅观、豪迈积极的盛唐精神。李白的思想无拘无束,自由清闲,绝不局限于某家某派。他决不盲从任何威信,生平追求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意志。李白的诗歌激情亲切洋溢,风格豪放,像滔滔黄河般倾泻奔流,创造了超凡脱俗的神奇境界,包蕴着上天入地的探索精神。李白的意义在于,他用行为与诗歌掩护了人格肃静,弘扬了昂扬奋发的人生精神。多读李白,可以鼓舞我们的人买卖志,可以使我们在人生境界上追求崇高而谢绝庸俗,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解放而谢绝作茧自缚。
杜甫生平遵照儒
他是儒家精神在唐代文学中最好的代表,以是钱穆师长西席称杜甫是唐代的“醇儒”。儒家学说的根本精神是仁爱思想,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部杜诗,其基调便是这种精神。
正因如此,我们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会深受冲动。在一个秋风秋雨的夜晚,秋风把杜甫的茅屋刮破了,秋雨漏下来了,床头都潮了,很难挨到天亮了,但墨客居然发下宏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什么叫“安得广厦千万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的“安居房”的观点。
杜甫的伟大情怀便是要关心他人,要关心社会,特殊是要关心弱势人群。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正能量。杜甫服膺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以关爱天下苍生为己任。杜甫生逢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关头,亲自经历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动荡岁月,时期的疾风骤雨在贰心中引起了情绪的巨大波澜,他用诗笔描述了兵荒马乱的时期画卷,也倾诉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沉郁情怀。杜甫因超凡入圣的人格境界和至高无上的诗歌造诣而被誉为中国诗歌史上惟一的“诗圣”。
杜甫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穷愁潦倒的一介布衣,平生毫无功业建树,却名至实归地跻身于中华文化史上的圣贤之列,从而实现了人生境界上跨度最大的超越。杜甫是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个命题的真正实施者,他永久是后人提升人格境界的精神导师。
苏轼的思想繁芜丰富
他一方面深受儒家入世精神的影响,在朝为官时风节凛然,在地方官任上则政绩卓著。另一方面,他从道家和禅宗吸取了离世独立的自由精神,形成了洒脱从容的生活态度。苏轼生平屡经磨难,曾三度流放,直至荒远的海南,但他以坚韧、旷达的人生态度傲视困难处境,真正实现了对苦难现实的精神超越。他的诗词内容丰富,兴味盎然,堪称在风雨人生中实现诗意生存的指南。
苏轼65岁那年从海南岛北归,途经江苏镇江的金山寺,自题画像,后面两句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个地方都是他的流放地,而且越来越僻远、荒凉,他在困境中的韶光长达十年。苏轼给当代读者最大的启迪,就在于他在诗词中展现的在困境中的人生态度。他45岁那年贬到黄州,不久就开始开荒种地。可惜官府借给他的那块荒地太贫瘠,收成欠佳。于是他想买一块较好的地来耕种,在朋侪的陪伴下到20里开外去相田。田没有买成,途中还碰着风雨,于是他写成一首《定风波》,其上片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缓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写他在相田途中有时碰到的那场风雨吗?当然是。但是这仅仅是写自然界中的风雨吗?当然不是。它实际上写的是人生途中的风风雨雨。
苏轼不但沉着武断地走完了十年困境,他还把困境变成了顺境。他在困境中还是有坚持、有创造、有光辉的人闹事迹。像《定风波》这类作品中包含着人生不雅观方面的强烈意义,对我们有巨大的启示浸染。
辛弃疾是南宋词坛上少
雄豪英武的侠士。他本是智勇双全的良将,年青时曾驰骋疆场,斩将搴旗;南渡后曾向朝廷提出全面的抗金方略,雄才大略盖世无双。可惜南宋小朝廷以偏安为国策,又对“归来人”充满疑忌,辛弃疾报国无门,末了赍志而殁。
辛弃疾的词作充满着捐躯报国的壮烈情怀,洋溢着气吞骄虏的英风英气。他以军旅词人的身份把英武之气搀入诗词雅境,遂在词坛上首创了雄壮豪放的流派。多读辛词,可以熏陶爱国情操,也可以培养尚武精神。那种为了正义奇迹而不平不挠的代价取向,一定会导致人生境界的超越。
宋词在辛弃疾以前,原有偏于软媚的缺陷。辛弃疾挟带着北国风霜、疆场烽烟闯进词坛,把豪杰之气和尚武精神写入词中。宋代的寿词多数比较庸俗,而辛弃疾为韩元吉祝寿的《水龙吟》却说:“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词中以收复失落土、击退强敌的报国壮志来与韩元吉相互勉励,这种情怀是何等壮烈。阅读辛词,可以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可以造就一种刚健、积极的人生态度。
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人格境界的传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野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从整体来看,唐诗宋词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光彩夺目的明珠,永久值得我们器重。
摘编自《群众·大众学堂》2018年第4期,原标题为《唐诗宋词:闪烁文化自傲的光芒》
作者:莫砺锋
任务编辑:陈伟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