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年事如何变革,遭遇若何繁芜,我们的心境总能用一首诗词来表达。
诗以言志,歌以咏怀。
诗词的伟大,不但在于其高超的艺术手腕,更在于个中蕴藏的人生境界。
下面的这三首词,便揭示了我们生平中追寻的三种人生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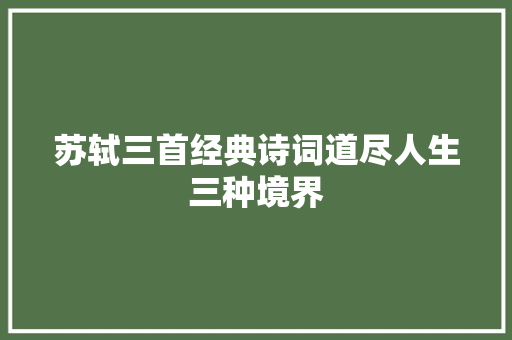
青年洒脱,中年通透,老年超然。
青年洒脱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周国平曾说:
“傻瓜从不自嘲;
聪明人嘲笑自己的失落误;
天才不仅嘲笑自己的失落误,而且嘲笑自己的成功。”
苏轼的生平不是被贬,便是在被贬的路上。
元丰五年,被贬黄州的苏轼来到城外的赤壁矶。
看到壮丽的风景时,他感慨万千:
想当年,三国的周瑜羽扇纶巾,雄姿英发,而如今的自己却被贬江湖,早生华发。
正当众人以为苏轼接下来会黯然神伤时,他却笔锋一转,写出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神来之笔。
和永恒的江水、江月比较,短暂的荣辱得失落又算得了什么呢?
长于自嘲的人最为洒脱,他们每每有着强大的自傲与宽广的肚量胸襟,也总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以一笑而过的态度应对苦难,终极将困窘的生活过成了诗。
《史记·孔子世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孔子带着子贡、子路等弟子漫游到郑国,由于一些突发情形,孔子和弟子们走散了。
弟子们十分焦急,分头探求孔子。
后来,有位行人见告子贡说:
“东门外站着一个人,脑型有点像尧,眼睛有点像舜,嘴有点像皋陶;
但从远处望去,却更像一条丧家之犬,这个人是不是你要找的老师呀?”
子贡来到东门外,果真找到了孔子,并把那人的描述见告了他。
孔子听后不仅不生气,反而笑着说:
“他的形容很贴切,我确实像一条丧家之犬。”
林语堂说:
“人生涯着,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
生活不易,何必纠结,那些以洒脱为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由于他们在认清原形后,依然选择热爱。
倘若年少的你能够学会洒脱,你便能接管自己的毛病,原谅外界的刁难,为原来苦闷的生活,增长几分笑剧色彩。
中年通透
“回顾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梁实秋在《人生不过如此而已》中写道:
“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
中年之际,得失落与悲喜已不再是那么主要,保持一颗通透的心,去回味自我才可以活得通透。
写下这首词的苏轼,已经在黄州度过了三个春秋。
虽然苏轼被贬黄州的日子不好过,但他却主动脱去文人的长袍方巾;
穿上农夫的芒鞋短褂,建鱼塘,开东坡,寻美食,迎新生。
这天景象不错,苏轼和朋侪出游沙湖道,突遇春日急雨。
拿着雨具的仆人们先行回去了,一起嬉戏的朋友避雨不及、狼狈不堪。
唯有苏轼缓步自若,怡然自得。
风停雨歇,苏轼蓦然回顾,悠然感怀,任你风雨交加,我自岿然不动。
人生如行舟,历经风雨依然从容的心境,便是人在中年时最好的压舱石。
柳宗元21岁便进士及第,一起升到监察御史里行,可谓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
然而“永贞改造”的失落败,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改造的核心人物“二王八司马”统统被贬,柳宗元作为个中骨干也被贬永州。
虽说还有司马职位,但柳宗元在永州连个住处都没有,他只得借住在寺庙之中。
出身名门王谢的他何曾这么狼狈过?
但他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身患重疾,几近丧命,母亲病故,儿子短命,妻子早逝,持续串的打击让柳宗元感想熏染到了命运的多舛。
就连后来的欧阳修也同情道:
“天于生子厚,禀予独艰哉。”
柳宗元的前半生虽满是风雨,可这无情风雨依旧不能让他望而生畏,以是,他选择用山水装点自己的余生。
与其在苦难中自怨自艾,不如在失落意中探求一份淡定从容,在迷茫中保持一份通透。
“投以空空地”的柳宗元阔别了尔虞我诈的官场,得以“纵横放天才”,和朋侪一起游历了永州的山水。
走累了就坐在草地上,拿出一壶酒,不醉不归;
喝醉了,就躺在草地上休憩一下子,做个好梦。
十年的永州生活,柳宗元以笔墨为这里的山水作传,这便是他不屈苦难的宣言。
正如余秋雨在《柳侯祠》中评价柳宗元说:
“灾害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韶光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人生自古多风雨,有谁相安过百年。
真正的强者,哪怕生活是一地鸡毛,他也会把这一地鸡毛系缚成鸡毛掸子,掸去心灵浮尘。
人到中年,要有能在困难面前,与之握手言和的勇气。
如此,才能在山重水复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柳暗花明。
老年超然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陆游曾在《作雪寒甚有赋》一诗中写道:
“老人别有超然处,一首清诗信笔成。”
人在老年,已是“满目青山落日明”,唯有超然物外,方可领略这晚霞的美。
老年的苏轼生活十分淡泊,常与朋侪一起饮酒赋诗。
这一夜,苏轼夜饮醉归。
怎奈家童甜睡不醒,无法入门。
但他并不气恼,而是转身拄杖临江,沐着明月清风,听闻涛声。
此时的苏轼感想熏染到世间各类,浮浮沉沉,究竟抵不过民气的超然物外。
一只小舟消逝在烟波浩渺之中,也将苏轼的心绪带到了那无垠的江湖中。
他也终于在江湖中抵达了恬淡自适的超然旷达佳境。
周国平在《悲观·执著·超脱》中写道:
“在人生中还有比成功和幸福更主要的东西,那便是凌驾于统统成败福祸之上的豁达肚量胸襟。”
在老年,学会放下执念,不伤春悲秋,才能优雅地老去。
季羡林的老年便是如此度过。
他在58岁时曾挖土挑粪,88岁时转身成为“文学泰斗”。
只管身份发生了变革,但他对付生活的态度一贯是淡然自适。
面对人生中的低谷,他将自己住过的牛棚形容成大院,将自己看作是孙大圣。
这份苦中作乐,将他的身心从困难中解脱出来。
苦难,只能使他豁达乐不雅观;名誉,亦不过是过眼云烟。
1999年,在季羡林的寿宴上,来宾们纷纭盛赞他的品质和学问,说他是“明灯”,是“太阳”。
到季羡林讲话时,他说众人刚刚赞颂的并不是他,他只是一个尽本分的学者罢了。
后来,他更是亲自辞去外界强加给他的诸如“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等隽誉。
摘掉了这几顶桂冠,季羡林才算规复了“自由之身”。
丰子恺说:
“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
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
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全无事。”
生命须要一份超然,光阴亦须要一份从容。
年少时拿得起,年迈时放得下,岁月的无情,究竟会被一个人的超然所融化。
当你老了,修得一份超然,余生自然无恙。
在央视记录片《苏东坡》中,有这样一句话:
“险些每个中国人,都会在不同的境遇里,与他相遇。”
苏轼身上,有道家的顺应自然,有儒家的积极进取,也有佛家的放下解脱。
少年时洒脱,中年时通透,老年时超然,便是苏轼教给我们的最好活法。
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
(来源: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