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道逝世的那一日,我和父亲谈天,父亲说,我的爷爷和江泽民同年生,但我爷爷已经故去多年。
随着父亲年纪的增大,对付生命的老去,他彷佛格外敏感。他常常说,村落里的谁谁去世了,年事多大等等。
父亲又和我感叹:村落里能活过60岁的男人少之又少。
我知道父亲内心的惶恐,对生命老去的惶恐,可我无能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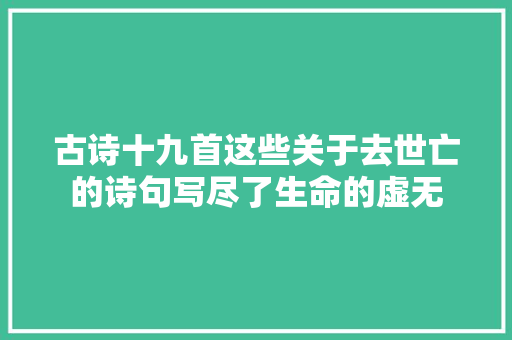
父亲今年61岁,三高、糖尿病、糖尿病肾病,做过心脏支架。由于这么多的病,父亲对生命格外惶恐,他常常感叹自己是活日子的人。每闻此言,我除了安慰只能独自伤心。唯一能做的便是好好事情、生活,让父亲宽心。
他最操心的还是弟弟,弟弟勉强在武汉买了房,可背负着累累的房贷。最近弟弟阳了,居家。弟媳即将临蓐,母亲在那边照顾。一家三口,住在一套屋子内,传染的几率也很高。父亲日日视频电话讯问,满是忧虑。
父亲极自律,逐日磨炼,掌握饮食。这几年身体各项指标掌握的还不错。
我总是在心里祈祷,希望岁月能对父亲温顺一些、慈善一些。
读《干校六记》时,有一处写道,有人去世了埋在地里垒起一个土包,过了几日,耕地的机器轰轰轰地从地里驶过,连那个土包都不见了。读到此时,让人唏嘘:生如草芥,去世一如草芥。
读《古诗十九首》,这种感叹更强烈。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社会与政治的“多余人”,他们被打消在政治系统编制之外,绝望于生命的痛楚。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宵会》)
人生非金石,岂能龟龄考。(《回车驾言迈)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
这是他们对去世亡的理性认识,镇静而无奈。生命原形的冷漠对他们而言,已经是“司空见惯浑常事”,但他们这样反反复复地强调,却不免让“痛断刺史肠”。还有些对去世亡的详细描写,阴森惨淡,更让我们惊悚不安: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去世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驱车上东门》)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去者日以疏》)
这是对去世亡的感性体验。使我们害怕的不是去世亡,而是去世亡之后。从陈去世人的角度来写去世亡,从被人遗忘的宅兆来写去世亡。
郭北墓与城内的高楼大厦对峙,这宅兆被称为“最长久的建筑”,由于可以住到天下末日,但这不是最实质的认识,真的能睡到天下末日吗?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这才是大虚无,不仅生不复存在,连去世也不复存在。当宅兆被无情地挖开、荡平时,我们曾经活过的、曾经来到过天下的事实,都被人否定。我们根本未曾存在过,这里把“去世”的意义发挥到极致。
我们这有一片开拓的新小区,门楼粉妆玉砌,夜晚灯火辉煌。屋子南北通透、视野开阔,屋子与屋子的间隔够大,绿化面积也大。可是本地人基本都不买,听他们说良久良久以前那儿是乱葬岗。
冬日,阳光甚好,我们徒步去那儿晒太阳。却瞥见,有一幢屋子外有一堵围墙,围墙外是荒草萋萋的坟。围墙内呢?那些坟呢?
民气的冷漠,生者对去世者的冷漠,是人生的大无聊、大寒冷、大荒诞!
生命的终点是去世亡,去世亡之后无来生。
在有限的生命里,要负责地好好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