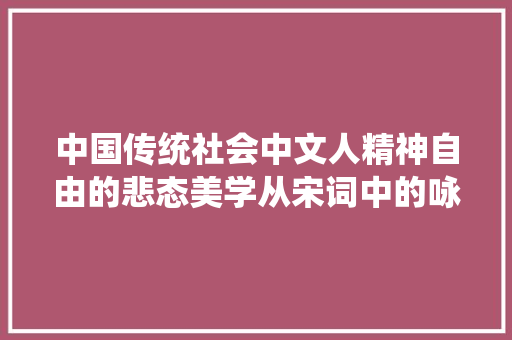择要:宋词中的咏叹调集中表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精神自由的悲态定式。本文以“宋词中的咏叹调”为材料,以中国传统社会文人精神为落脚点,以悲态的三个递进范畴展开,来还原悲态艺术形式的文化生理,加深对中国文人精神构造的实质理解,探究中国文人精神自由与悲态形式的一定联系。同时也能给我们当代人生活中的自我调节供应启示。
关键词:宋词;咏叹调;文人;精神自由;悲态
“咏叹调”本是西方歌唱艺术的一种形式,是一个声部或几个声部的歌曲,或者专指独唱曲,是一种着重表达歌唱者感情的抒怀调;而“宋词”是一种新体诗歌。取“咏叹调”中的抒怀义味,摒除宋词中的纯挚叙事作品,取其“抒怀词”,便可称为“宋词中的咏叹调”。然而从中文意义上来讲“叹”当中蕴含着“悲”的元素,该当在其内涵当中表示。虽然关于咏叹调的内涵如此丰富,看起来涉及很多专业术语,实则这种咏叹调是我们在宋词中最常打仗的,非常熟习的。
宋词是中国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中国美学不可或缺的材料参照。以“宋词中的咏叹调”为材料,以中国传统社会文人精神为落脚点,以悲态的三个递进范畴展开,可以还原悲态艺术形式的文化生理,加深对中国文人精神自由的实质理解。
一、对抗与失落意
作为美学的审美工具,“悲”所表示的是主体与客体的敌对与否定,并且主体在一定意义上低于客体。在美学的范畴,悲有悲态、悲剧、崇高、荒诞四种表现形态,因此“悲态”作为悲的形态之一,一定具有其普遍特色,即对抗(这种对抗,普通来讲,可能在小说中传达的更明显,可以理解为便是主人公和所谓的恶势力的斗争,比如贾宝玉与封建不雅观念之间。当然这只是赞助理解,不是对抗的全部意蕴)。然而在对抗当中主体是弱小的,在悲态中这也注定对抗的结果表示为一种失落意(比如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捐躯)。以是对抗与失落意是作为悲态的第一个范畴的。在宋词当中,无论是豪放派的苏轼与辛弃疾,还是婉约派的李煜与李清照,都有着不同层次和不同程度上的对抗失落败后的失落意。
(一)“悲态艺术”高产量时期宋词紧张盛行与宋代,宋代战乱频发,积贫积弱,南宋则更偏安一隅,山河破碎。在这样的年代,百姓流落失落所,英雄壮志难酬,文官怀才不遇,亲人生离去世别,家国朝不保夕,凡此随处可见对抗,悲从中来。这样的时期尤其为文人悲态艺术的创作供应了“丰富’的题材,是悲态艺术产生的“肥沃土壤”。因此,在此期间,涌现了大量的“咏叹调”,呈现了一大批“悲态词人”
这样的“悲态艺术”高产量的时期,不但宋朝。《古诗十九首》是汉末士人的集体悲歌。“意悲而远。”“诗多哀怨。”这给十九首诗定了一个悲怨失落意的情绪基调。比较之下,唐朝盛世所产出的唐诗,总体气质上是丰腴的,壮美的,典雅的,当然也不乏分外情形。这表示了悲态艺术的产生是有一定性和普遍性的。
(二)“悲态艺术”高产量群体张法认为:“悲态是由人生失落意的沉痛,升华为对宇宙人生本体讯问的感伤情怀。”故悲态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喜怒哀乐的悲,它要从宇宙人生的高度去感想熏染、不雅观照而令其具有哲学意义。因此悲态背后是须要有超越、理性、反思的哲学背景与文化生理的,这也决定了“悲态艺术”一样平常情形下是在受过教诲,具备文化素养的“文人”群体当中产生的。
然而,在中国“学而优则仕”,所谓文人群体,大部分也是“士人阶层”。这个群体大都是有现实的政管理想、诉求和社会任务感的,他们对付时期的危急与弊病更为敏感,对付生命意义探索的更深。这也决定了其艺术创作的主题有不可避免的入世根本。
不过这只是对付宋代或者说传统社会而言,在当代社会中,国民本色普遍提高,知识和文化不再节制在少数人的手中。同时经由当代性的洗礼,人们的自我反思意识也比传统社会强烈许多,因此,悲态艺术的“高产量群体”也扩大了很多。在这里,我们着重谈论宋词的情形。
(三)“悲态艺术”高产量主题在悲态中,对抗客体来自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加上特定的时期与群体,其主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仕途不顺,官场沉浮,抱负难展,壮志难酬的人生追求与伟大抱负的碰钉子。以苏轼与陆游为范例:“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去世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其二,离愁别绪,回顾相思,生离去世别的无可奈何。这在李清照和李煜词中表示最明显:“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顾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其三,人生苦短,渺如蜉蝣,世事无常:“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由前两个主题进而升华为第三个主题,从第三个主题中就表示出终极追问了,由此便过渡到了悲态的第二个范畴。
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群体和特定的主题之下,对抗与失落意的普遍性产生,悲态艺术大量,因而也是普遍性的产生,正好指向了传统文人精神天下。表示了悲态在起源上与中国文人精神的暧昧关系,也为文人精神自由的实现供应了“契机”。
实在这三个主题对人类来说是永恒的追问,不止对付宋代的文人。当代的我们纵然科技发达,也难免有身如蜉蝣之感。在经济年夜水里,在制度框架下,在茫茫人海中,汲汲察察,而又无所安定。
二、讯问与把握人生追求与离愁别绪升华之后,会产生人生苦短,世事无常的感叹,同时这也是一种生命终极的讯问。悲态是由人生失落意的沉痛升华为对宇宙人生本体讯问的感伤情怀,须要从宇宙人生的高度去感想熏染、不雅观照。然而在悲态中,工具是抽象的,是人无法怪罪的自然、社会或是命运。由于 “悲态所面对的一样平常是无形的一定律”它不详细化为有形的事物。以是这种讯问必须超越日常感情,一定是有终极关怀的。但是讯问不是质疑,而是悲的反思、感叹和抒发,主体对付宇宙规律是持一种理性把握,乃至崇奉的态度,苦恼的只是为什么会悲要发生在自己身上。讯问的目的是为了把握,没有讯问便不会对宇宙规律有所反思,二者的统一构成了悲态的第二个范畴。在宋词的咏叹调当中也无不表示着这种讯问和把握。
(一)对日常感情的超越当“人生失落意的沉痛”在没有达到对宇宙人生的终极思考,或者说,还表现为人生喜与怒、哀与乐、离与合在哲学层面的“天人规律的合拍”的时候,即是“悲情”。要实现从悲情到悲态的超过,首先须要超越日常的感情。“寻寻觅觅,冷生僻清,凄悲惨惨戚戚”,凄冷的笔调领悟了亡国之痛、孀居之悲、沉沦腐化之苦,因而显得格外深奥深厚与厚重,然而有哀无伤,只是一种悲情表达。
离愁别绪,触物伤情,当人生的离去转化为永久的虚无,就表现为对宇宙规律偏离的讯问,即美学中的悲态。“僵卧孤村落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更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怀激烈;“壮志病来消欲尽,出门搔首怆平生。”的怀才不遇的悲哀;李煜“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河山”的国破怀伤,“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无奈忧郁,由此引发对人生的哀怨伤婉,对不幸遭遇的痛彻讯问。不是顾影自怜的自悲感情,而是有感而伤的讯问,乃至是理性的追问,这就过渡到了下一个环节。
(二)对命运终极的追问主体超越日常感情,上升为对宇宙人生的追问。当感情转化为追问,追问的工具,即客体就涌现了。在悲情当中由于没有与宇宙规律偏离,而表示为物我、主客的原始混沌,当涌现追问的时候,主客分离了,主体开始关注客体。这个客体便是抽象的宇宙规律,抽象的社会和自然,抽象的命运,而不是详细的工具,这是它与悲剧的差异。在宋词当中,不乏这样的追问:“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自是人成长恨水长东”。这是对不幸命运的通彻追问。
(三)对宇宙规律的崇奉追问并不等同于质疑。在宋词当中虽然随处可见追问,但是追问的内容“宇宙规律”到底是什么?“我”是否能够把握?为什么悲发生在我的身上?并不是宇宙规律精确么?宇宙规律存在吗?以是这种追问背后是对宇宙规律的崇奉。“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李煜对付自然规律是无奈的,“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对付命运也是无奈的。他首先是相信有自然规律存在的,且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然而,为什么命运如此弄人,这些文人依然要崇奉呢?这又回到了悲态的缘起上。客体是高于主体的,宇宙规律的强大是人无法与之反抗的,也是人无法从中节制的。对付这种强大的力量,主体只能选择承认,对付这种神秘不可节制的力量,主体只能选择崇奉。但这种崇奉只是对规律的崇奉,是理性的迂回,而不是非理性的宗教崇奉。在理性的辅导下,人可以去把握、归纳和顺应规律,人终将找到一个安身置命的平衡点。
这种讯问与把握无疑是有反思性、超越性的,这是一次主体人性的拔高,这种拔高表示出了自由的向度,文人精神自由由此便产生了。
三、安置与自由
探求到安身立命的平衡点,便是如何安置的问题。这种“悲”不能漂浮着,而必须在一定的文化生理构造中降落。悲态中人与社会,与人生,与自身的对立表现为无形的理解与顺应,在理解与顺应中天人又回归统一了,这种统一是让人舒适的。文人这种安置的生理构造紧张来自于老庄哲学与禅宗,理性的把握使得悲态具备了更深层次的哲学意蕴。这种安置,不是主体“被安置”,而是主动地选择顺应,这也表示出传统文人的精神自由的维度。在一定律的支配中,主体一定地想要冲破束缚,实现自由,然而这种自由注定是有限的,也注定是将意志溶解了的理解与自我安置,是在不通过撕裂和抗争下的人与一定的统一的自由。
(一)老庄哲学与禅宗的人生安置态度人与宇宙规律的偏离是痛楚的,以是必须探求新的安置点来回归。这一次的回归,与原始主客不分已经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是讯问后的回归,在辩证法意义上来讲,是更高层次的回归,这个从偏离到回归的过程,就完成了一次悲态的审美。
面对生命短暂与宇宙永恒的冲突士人没有决意于与它们作斗争以改变现状,也无法和它们展开斗争,只能理解、 接管与屈服它们,安置自己这便是士人的悲态生理。这种安置的生理紧张来自于老庄与禅宗,但是又于儒家精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面强调过这个分外的“文人”群体,是有社会身份的,他们大都入仕,故而有着入世精神。然而在现实中这样的社会诉求总会受挫,乃至收到伤害,固一定指向一定的社会弊端。比如李清照,战乱使他与丈夫阴阳两隔;陆游,政治系统编制将他排斥在外;李煜,朝代更替带来的人生落差。而这些社会存在是他们无力改变的,便转而追求老庄或者禅宗的自我安置,这也表示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形成的稳定的三角生理构造。
老庄哲学当中的安置表示为“虚静”、“逍遥”。深层次看庄子本人也表示出一种悲态人格,其达不雅观任性,狂放不羁,洒脱达不雅观的深处,是对人道命运持一种柔顺的态度,装的是循分顺应的内核,如“吾生也有涯”。然而这种柔顺是超越性的,因此虚代实,超越现存秩序达到太虚极静。如苏轼的“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然而老庄哲学是丝毫不触动现存秩序的合理性的,只是避而不谈,在这一点上儒家是积极融入的,二者都承认现存秩序的存在。而禅宗的“寂静”是消耗统统有无、色空、善恶、许是,统统因果时空、物我界线的,因而也彻底否定了现存秩序。故而其安置表示为“寂静”、不闻不问。但他对现存秩序现实性的否定只是在主不雅观意识上的,尚无法触动现实。不过禅宗进入美学领域却极大地影响着传统文人的生理构造,悲态中的超越性的自由安置便是其范例表示,超越物我对立,超越时空、物象束缚的精神自由以及直不雅观顿悟的灵感偶得是其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自由不会触及现实,更不会触及宇宙规律,是失落意文人的避难所,是一种悲态的安置。
值得把稳的是,悲态只是阶段性的,安置也只是暂时的,中国传统文人的追求仍旧是治国平天下,这是刻在文人骨子里的。悲态的安置只是一种缓冲,尤其老庄的“虚静以待”是没有完备放来世俗追求的,文人群体只要一有机会,就又纳入到现存秩序中。这便是传统文人的生理构造。
抛开群体而言,苏轼算是一个个例,苏轼的自我安置当中,有一种更有效的方法,便是直接关注当下生活,不负生命,悲态中得乐,比如发明东坡肉等事例。这是世俗和享受型的直接对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生命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是脱开中国一向的社会为先意识的人本主义,是超出时期而有某种当代哲学意味的。
(二)从无自由的意志到无意志的自由由于安置一种顺应的态度,故而是“无所作为”的,纵然是自由的,但是是无意志的,这便是悲剧与悲态中主体态度的差异。在悲剧当中,主体是故意志的,是有决心和勇气的的,因而他们会与详细的工具,或者说是直接工具进行激烈的斗争,乃至不惜付出毁灭的代价,在个中得到的自我升华与自由是“自由意志”的表示,这也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模式。在中国哲学中也是有“意志”的,但一旦如此,又失落去了自由,当文人在现实秩序中施展意志时,便急速意识到自己是不自由的。这便是邓晓芒所说的儒家是“无自由的意志”,而道家是“无意志的自由”中国文人便在二者之间徘徊。故而中国传统文人精神自由总体上一定是无意志的,从而是悲态的,其精神自由是建立在悲态人格根本之上的。
虽然这种悲态精神自由是无意志的,但并不能说是悲观的,这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传统差异于西方主客二元对立定式的表现和结果。美学问题便是人学问题,悲态生理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主体性意识、自我意识的薄弱,然而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生命意识的觉醒,且悲态进入美学领域有极大的贡献。文化可以有多样性,然而人类学应该是有普遍性的,中国文人应该连续致力于主体性的挖掘,西方也应从中国思维中探求启迪,故而中西碰撞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温小腾.《诗经》的悲态美初探[J].晋中学院学报,2006(04):14-17.
[2]覃素安.论《古诗十九首》士人的悲态生理[J].文艺评论,2016(08):89-95.
[3]杨铠瑞.从“庄周梦蝶”浅析庄子的悲态生理[J].吕梁高档专科学校学报,2009,25(03):32-34.
[4]邓月影,刘劲杨.繁芜性视野中的审美范畴研究——以悲范畴为例[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4):21-26.
[5]张法.环球化时期的灾害与美学新类型的寻求[J].社会科学研究,2011(02):1-8.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