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更细微的格律上来说,诗分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不讲究平仄,也多数不固定句数和字数,有时会有是非句交杂的杂言体;近体诗则有固定的字数和句数,没有是非句,也讲究平仄及韵脚。但词既包含了古体诗杂言的形式,也包含了近体诗所讲究的平仄和韵脚。至于曲,形式比词来得自由,字数较不固定,有时连句子都可以增加。此外,曲常常利用衬字,便是在原来的曲牌中规定的字数外,基于让语气或语意更完全、增长声音情绪等缘故原由,可随意增加一些字,让歌词的内容听起来更为活泼、浅白,唱的时候,这些字常日都是轻轻带过的。这些衬字可以随意增加,乃至有过衬字比歌词本身要来得多的作品。
有些曲牌是延续了词牌,内容格式险些一样,例如“念奴娇”,这时就可以用有无衬字来分辨到底是词还是曲。但要把稳的是,曲的字数或句子可以增加,是就其曲牌本来的正字而言,衬字是不算在内的。再从音律上说,近体诗不论五言、七言、绝句、律诗,都有固定的平仄,而词也有固定的平仄,但其固定的平仄是根据词牌不同而有所变革的,以是不像近体诗纯挚。这一点,曲也是一样的,每个曲牌也会有规定的平仄,而且比诗、词更加严格。
末了,就诗、词、曲整体的风格而言,清代李东琪曾概括地说:“诗庄词媚曲俗。”诗,适宜言志,古人多数拿来写比较严明的议题,如自己的政管理想、人生志向、社会关怀等,所以是庄严的;而词,多用于抒怀,又常写男女情绪,相较起来是较为女性化、妩媚的;而曲,题材博杂,措辞也是最为口语的,虽然诗、词有时也会用方言、俚语等,可是都不及曲来得多,以是曲比较浅近易懂,更加普通。经由比较,我们可以得知,诗、词、曲三者,有相同类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由于三者又有发展上的先后以及干系性,以是又有人把词称为“诗余”,曲称为“词余”。
词还有许多别称,较常见的是“乐府”,由于词和乐府诗都是配乐而唱,以是就有人把词称为“乐府”,但实在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词又可称“是非句”,这是由于很多词都是是非句的形式。词还有前面提到过的“诗余”这个别称,除了由于词与诗有发展上的关联性以外,也是由于词在一开始不被文人看重,视为“小道”,是写诗之余才去作的。这些别称常见于词人的词集名,如《东坡乐府》便是苏轼的词集,《稼轩是非句》是辛弃疾的词集;而《草堂诗余》则是宋代的词选,依据词的主题将词进行分类,方便歌伎在不同的场合中选唱合宜的歌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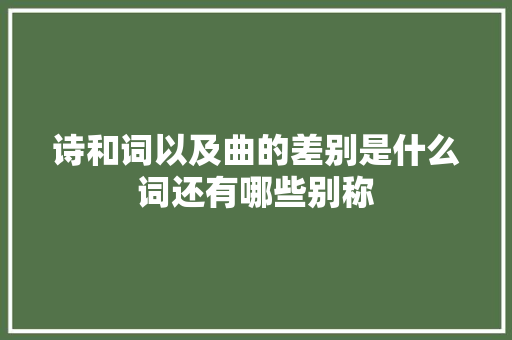
词还有比较特殊的别称,如“琴趣”或“琴趣外篇”。这个典故来自陶渊明,根据《晋书·陶潜传》的记载,陶渊明不太懂音乐,但却有一张没有弦的琴,每与朋友聚会,就操琴唱和,并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表示只要能理解琴本身的意见意义,又何必用弦来发生发火声音呢?后来“琴趣”就成了词的别名。词人的词集也有以“琴趣”命名的,如《醉翁琴趣外篇》是欧阳修的词集,《淮海琴趣》便是秦不雅观的词集。
有时候,词、曲也会有混称的情形。例如唐代时,词实在叫作“曲”,或者又称“曲子词”,而现在所谓的元曲,在元、明时又常被称为“词”,紧张还是由于这两种文体都和音乐有关,又都是歌词,在发展上也有关系的缘故。实在,文体的演化与特色,都是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一开始难免会有些混乱,或是在演化过程中产生一些新的不雅观念与意义,因此才会产生某些文体名称稠浊、涌现别名等情形。有些人乃至认为词的那些别称不好,但这倒也无须过分深究,主要的还是能理解“词”这个别裁的真正内涵是什么。
我是“浪里白条一只猪”,执笔走天涯,与大家一起分享、理解中国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