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释“秀”的差异及缘故原由
古人对“秀”的阐明,可归为三个层面。第一,以黄侃、范文澜、周振甫等为代表,从修辞学角度着眼,认为“秀”即“秀句”,“像鹤立鸡群,是一篇中的警句”。第二,以刘师培、詹锳、傅庚生等为代表,以风格论为态度,认为“秀”是有别于“隐”的文学、美学风格,表示为柔性的“秀美”特色。第三,以张少康、祖保泉、叶朗等为代表,从形象论切入,主见“隐秀”是创作文学意象的办法和原则,“秀”即为“秀象”。
以上三种不雅观点分别从不同视角切入《隐秀》篇文本,皆触及“秀”的某些实质特色。客不雅观地讲,“秀”属于模糊观点,“有一定的自由度,以容纳各种变形和千奇百怪的再定义”(宇文所安语)。而从文本属性来看,残篇《隐秀》为“开放的作品”,相较完全的闭合式文本,其内容具有更强的不愿定性。因此,“秀”的意涵势必呈现出多元性。事实上,古人已意识到“秀”及《隐秀》篇文本的分外性,故坚持己见的同时也肯定部分异质不雅观点。例如,周振甫等在将“秀”认定为“精警格”的根本上,也承认其涉及某些艺术表现的内容;詹锳等谈论“隐”“秀”风格时,紧张针对“隐篇”“秀句”的文本样态;张少康等在将“隐秀”作为“意象”书写原则的同时,不得不引“秀句”说做补充。之以是承认“秀”的多义性,更多是阐述策略上的妥协,但如此阐释每每忽略了“秀”的诸多意义间的联系与差异,有时还会令不雅观点含混。
“秀”内涵的层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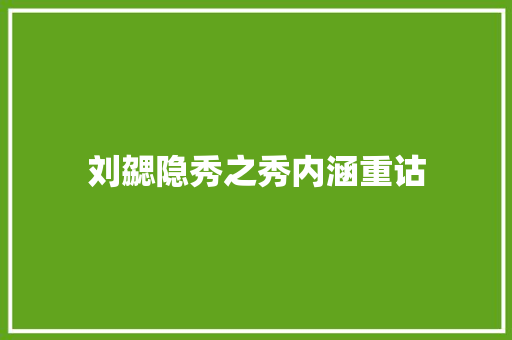
“秀”的内涵虽多样,但细读文本,不难创造,刘勰论述“秀”是沿着“释名章义”“选定亲篇”“敷理举统”的严密逻辑展开的,绝非模棱两可。因此,“秀”一定有明确且唯一的文本含义。但基于文本字面内容的本义不等同于作者本意。作者本意是指作者原来想要通过文本所表达的意图。这种意图潜藏于笔墨表面之下,同文本本义一起构成观点内在的张力。对“秀”内涵的重诂要充分重视文本本义与作者本意的共构性。
针对“秀”本义的考释,首先要重视《隐秀》篇在《文心雕龙》中的位置。《文心雕龙》体大虑周,组织严密,《隐秀》篇的主旨一定服从于整部书理论体系的构建。其所在的创作论部分,《神思》《体性》等以下七篇是带有总述性子的篇目,另有《声律》至《附会》等十一篇分述措辞技巧。《隐秀》位于分述篇目中间,因此其主旨应同附近篇目如《夸饰》《事类》等类似,是关于“隐”和“秀”两种修辞手腕的先容。
其次要以《隐秀》篇的文本论述为主要依据。从对文本的虔诚度上讲,将“秀”理解为“秀句”最合理。“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是刘勰给“秀”下的定义,即“秀”是篇章畛域内最出众的部分。《隐秀》篇文本中有两处直接以“秀”论句,“篇章秀句,裁可百二”“秀句以是照文苑”,举例“秀之为用”时,则援引了王瓒《杂诗》中的“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
魏晋以来,文坛对佳句颇为关注。理论阐发方面,陈琳、陆机、陆云、沈约等都曾以“片言”“警策”“妙句”“出语”言之。文学实践方面,史籍记载的干系业绩可印证当时炼字析句之盛。例如,《世说新语·文学》:“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咸太息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晋书·王坦之传》:“坦之标章摘句。”《南齐书·文学传论》:“张眎摘句褒贬。”因此,刘勰立专篇谈“秀句”也是对魏晋以来文坛审美风尚的呼应。
刘勰利用“秀”这一观点的本意在《隐秀》篇残文中无迹可寻,但通过他未照搬当时的术语以描述文章中的“超越常音”之句,而选用“秀”这个极具审美意味的词汇也能窥测一二,其应有以“句”为依托标示“秀”的风格的意向。那么,刘勰为何选择“秀”来命句,“秀”又呈现出若何的美学特色?
以往研究对“秀”的美学表现的解读方向于阴柔美的论调,但“秀”作为刘勰褒赞的审美空想,若仅是柔婉媚态,岂不同他所批评确当世“风昧气衰”“负声无力”的文风附近?刘勰推崇“秀”,缘于其昭示的风格符合儒家诗教“雅”的取向。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阐明,“秀”的本义为“禾黍”,除赞颂植物外不雅观秀茂外,还有重实重质之意,引申至形容文学审美也应是对外在辞藻和内在思想的双重肯定,正所谓“才情之嘉会也”。这与贤人文章“衔华而佩实”的特色具有同等性。
南朝宋齐之间,原来清新雅丽的五言古调在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下形成一种新体,以江淹、鲍照为发轫。这种诗歌新风颠倒词序,不避危仄,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评价道:“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详细如鲍照之“君子彼想”,实应为“想彼君子”;江淹的“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则应为“孤臣坠涕,孽子危心”(孙德谦《六朝丽指》)。刘勰并不认可这种依赖造语惊奇博得读者关注的做法,以是便以喻示着文质合一、穷力追新但不失落雅丽之“秀”作为纠正险俗诗风的新风格。
至于“秀”代表的风格之刚柔,《文心雕龙·杂文》有“信独拔而伟丽”同“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中的“独拔”互文,可见在刘勰看来,“秀”应有古人所说的气势夺人、恢宏之刚性特色。但《文心雕龙·定势》言:“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年夜方,乃称势也。”此原则虽为刘勰针对诗文整体体势风格而言,但也适用于章中辞句。具有“秀”之风格的文本应不拘刚柔,包举洪纤。以是,柔嫩如“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瘦硬如“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皆能为诗中秀拔之句。
“秀”与“隐”之间的繁芜关系
至此,无论将《隐秀》篇中的“秀”理解为“秀句”还是“秀”的风格,其先决条件都将“秀”视为纯粹独立的观点。如果刘勰仅冀图表达“秀”之风格,则完备可以“隐篇”“秀句”为题,进行更详尽的论述。他阐明“秀”,与“隐”对举,该当同《风骨》《情采》《比兴》等类似,暗示了两个观点彼此独立但不对立。
以《隐秀》篇残文中仅有的一段描述“隐”“秀”关系的笔墨为证,“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故文之英蕤,有秀有隐”。傅庚生阐明说:“‘源奥而派生’的自然以‘复义为工’,‘根盛而颖峻’的自然以‘卓绝为巧’。”以是,“隐”和“秀”的关系应为并立共生。二者看似彼此独立,但实际上具有内在关系,“心术”和“文情”实质皆为内心情绪,因此,“隐”“秀”具有同源性。“秀”虽以光鲜独拔示人,但支持它“精髓耀树”的是潜藏于地下的茂盛的根,而这个根便是深隐的情。“秀”应是“秀出”与蕴藉的结合。在“秀句”创作中,这种相生相谐的状态十分明显。如《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景写情,融情于景,将个人对军旅生活的无奈与酸楚以春季杨柳、冬季雨雪的景致更迭表现出来。《古诗十九首》中隐没情志的“秀句”,如“浮云蔽白日”,李善注曰“以喻邪佞之毁忠良”,而“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则暗示游子不忘故乡之意。大量文本证明,刘勰对“秀”的认识具有其深刻性,这种有“秀”有“隐”的创作及表现原则应是《隐秀》篇所表达内容的精华所在。初唐元兢《古今墨客秀句》受刘勰“秀”论影响颇深。元兢在媒介中评“落日飞鸟还,忧来不可极”两句,说“扪心罕属,而举目增思,结意惟人,而缘情寄鸟,落日低照,即随望断,暮禽还集,则忧共飞来”。显然,他对付“落日”两句的“秀”的理解也是从景中含情、情兴意显等方面去把握的。
因此,刘勰“隐秀”之“秀”的内涵是文本本义与作者本意“一体两面”的结合,其本义为“秀句”,是对古人论述“章句修辞之学”传统的继续,以及对当时沉迷佳句创作与批评风气的回应。同时“秀”也表达了一种“秀”之风格与“隐”“秀”相间的审美原则,是刘勰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弊病及创作实质深刻反思后的思想结晶。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延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