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晰的梦,一个真切的梦。
醒得太快,想回到梦中,已不可能。
月光脉脉,竹风轻动,
仿佛正在远去的梦的行踪,仿佛那并非是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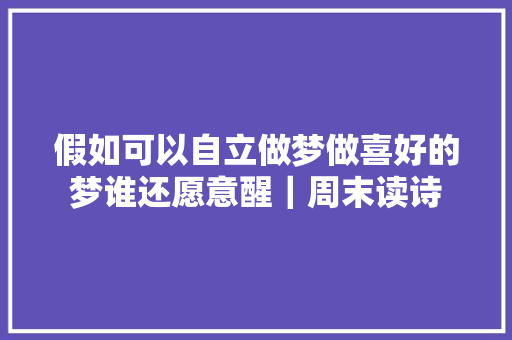
现在是深夜,而我给你写信,
月光落在白纸上,落在不可能的地方。
不知你在哪里,我给你写信,
我将把这些字留给陌生人。
撰文 | 三书
01 何处按歌声,轻轻
《诉衷情》
韦庄
烛尽喷鼻香残帘半卷,梦初惊。
花欲谢,深夜,月胧明。
何处按歌声,轻轻,
舞衣尘暗生,负春情。
如果可以自主做梦,做喜好的梦,做梦的主宰,谁还乐意醒来?
纵然有人在旁善意提醒,说这只是个梦,说梦是假的,那么好吧,就让我们把梦做得更美一些更久一些。庄周梦蝶,不也让韶光少焉停歇,不也美了几千年吗?何况庄子不也提醒过,所谓醒来,不过是醒在另一个梦中。
做过的梦,风骚云散,正如现实的每一天,我们在个中显现,如真似幻。或许你瞥见的一朵云,便是某个梦见你的人做过的梦。梦并不真实,但梦里的觉得却很真实,而觉得并不随梦的消逝而消逝。
唐末五代墨客韦庄的这首词,如果不用耐心细读,将会被轻易地概括为“写一个女子梦醒时分的情思(或表达她的孤寂之类)”。应该永久记住,我们阅读诗歌,并非为了获知某人有若何的思想感情,而是为了去感想熏染情绪的状态,进而去感想熏染事物本身。我们若还渴望享受诗歌这门艺术,那就更不能概括了事,而应让感想熏染的过程尽可能延长。不论对词语和句子,感情和语气,意象和留白,我们都该满怀好奇,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打开一层又一层的惊喜。
为了充分感想熏染,我们不妨做一次演员,想象你便是诗中的那人。想象你醒来时,瞥见烛尽喷鼻香残。从这两个形象,你瞥见韶光的流逝。但不仅如此,由于形象在艺术中并非为了认知,即非使意义易于理解,形象为的是制造出我们对事物的分外感想熏染。
当你恍然从梦中醒来,你创造自己刚才竟睡着了。入睡之前,烛炬点燃,喷鼻香熏正浓。那么醒后的烛尽喷鼻香残,就传达一种冰冷的现实感。紧接着的“帘半卷”,这个形象耐人寻味。古典诗歌常常以“卷帘”之意象暗示心情,例如李白的《怨情》开始就说“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卷起珠帘,明显便是在等人,而人不来,久候不来,于是深坐颦眉,但帘子还是没有放下,如此写出美人的心情。李后主词不亦云:“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没有人来,以是帘也不用卷了。
那么“帘半卷”究竟是何心情呢?即卷即非,即非即卷,在等又不在等,不在等又想等。这才这天常处境中,谁都会有的抵牾心情。今人很少用门帘,没有门帘,可以想象一扇门。一扇半开的门,比起全开或全闭也更故意思。而在这首词里,醒后瞥见烛尽喷鼻香残,随即目光投向帘半卷,彷佛那是个出口,梦的背影若隐若现。
看到居室中这些事物,她的知觉回到现实,这才“梦初惊”。方才的打量是将醒,第一句之后,才在惊中醒寤。“花欲谢,深夜,月胧明”,彷佛仍残留着梦的踪影,但这塌陷而湿润的时候,她置身于冰冷的事物中。
“何处按歌声,轻轻”,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了歌声。深夜梦回,听到渺茫的歌声,不是梦,却像来自梦中,像是唱给她听。那歌声,仿佛候鸟留下的天空。
那歌声把她唱成一个幽灵。但墨客不这样说,他说:“舞衣尘暗生”。墨客供应了一个视感,以强化听者的感想熏染,并使我们永久记住。因此这样说才是好诗。舞衣象征过去的欢快光阴,“尘暗生”,如今一片静寂,落满灰尘。
末了的“负春情”,不正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吗?酷爱《花间集》的汤显祖在写《牡丹亭》时,或许真的想到了这首词。
陈淳《花卉图》
02 深夜梦回,我连续老去
《归国谣》
冯延巳
何处笛?深夜梦回情脉脉,
竹风檐雨寒窗隔。
离人几岁无,
今头白,不眠特地重相忆。
深夜的笛声,是不是像某个人在哭泣?不要问那人是谁,那是你,也是我,是听见笛声的每个人。
吹笛人,借你的笛让我哭一下子吧,我早已不知该如何哭泣。
何处笛?何处按歌声?不知何处吹芦管?诗中的这些“何处”,皆不必了知,你听见了,它就落在你心上。因不知而神秘,而更美,而给人安慰。
“深夜梦回情脉脉”,与韦庄的词一样,但道一句“梦初惊”,梦见了什么,只字未提,但谁听了都能懂。不必絮叨梦中所历,更不必如某些盛行歌曲涕泪纷飞,仅淡淡几笔,脉脉情思,悄悄泪痕,哀婉矜贵,回味不尽。
从笛声的哭泣中醒来,隔着寒窗,听表面的竹风檐雨。为什么今夜我梦见了你?
“离人几岁无”,如果这个梦带来他的,那是什么?当时空阻隔令人绝望,唯一能超度自己的便是梦。梦中的相遇也是一种相遇,且能够任意打乱时空的秩序。在诗中或故事中引入梦境,是叙事对空间限定的打破,并将韶光引入空间,从而也实现了对韶光的重构。
人是在等人的时候老去的。几岁无,能不头白?末了一句“不眠特地重相忆”,尤其意味深长。大概本来已经心如去世灰,等到末了已不等,以不等等之。梦见之后,离人彷佛又活过来,彷佛就要回来了。“不眠”者,不能眠,不欲眠,不忍眠,为的是“特地重相忆”。“特地”是一个手势,她想抱紧这个梦,再次好好想想他。
在回顾中,在竹风檐雨声中,在寒冷中,她连续老去。那支笛呢?没人知道它去了哪里。
陈淳《花卉图》
03 被梅花熏断的梦
《诉衷情》
李清照
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枝。
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
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
更挼残蕊,更捻余喷鼻香,更得些时
关于此词的写作韶光,论者多系之于南渡后逃难途中。然不雅观其词气娴静蕴藉,只是些淡淡的哀愁,并无流落无告之凄楚,或许作于南渡前亦未可知。提出这个疑点的用意在于,如果是南渡往后,那么梅在词中便寄托乡思;如果是南渡以前,可能另有隐情别具暗示。
由于“梦远不成归”一句,此词常被认定为写乡思。夜来醉酒,就寝时卸妆时动作迟滞,梅萼的残枝仍插在发上。本来沉醉又春天,该当睡得很沉,然而竟被梅花的喷鼻香气熏醒,而梦里正在归家的途中。
梦很难圆满,纵然好梦,也总被打断。在这首词里,说是归梦被花喷鼻香唤醒,究竟是被什么唤醒,这是不可知的。有时并无外力,梦到关键处却俄然醒,梦被中断。被中断的遗憾,犹如话未说完,必将在梦醒后追忆填补。
下片即是对梦的追忆。“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孤寂是孤寂,但墨客写的并非孤寂,而是梦的痕迹。人、月、翠帘的情态,无不尚有梦在。杜甫在《梦李白二首》中也有:“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这并非墨客的修辞,而是从一个真切的梦中溘然醒来时,人所共有的一种体验。
以下两个细微的动作和三个“更”,不都是在竭力留住依稀尚存的梦吗?“挼残蕊”,“捻余喷鼻香”,残蕊和余喷鼻香也来自梦,至少可藉以重返那个梦,甚而在想象中完成被中断的部分。然而梦毕竟已醒,细细回味为的是“更得些时”。
如果不是写乡思,那么上面所说的隐情是什么,又是如何被暗示出来的?以词中的语气来揣度,隐情也可能是她和丈夫之间的感情疏离,这个视角也完备被文本支持。且梅花可以寄乡思,也可以表相思,清照在《孤雁儿》中就写过:“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上片感情恹恹,或许夫妇分隔两地,或是她心绪烦闷而怀念乡居,故为归梦难成而憾恨。若如此阐释,下片的挼残蕊、捻余喷鼻香,便有了为感情而苟延残喘的暗示。
陈淳《花卉图》
04 一封被梦催成的信
《无题》
李商隐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李商隐的诗歌声音本身就令人迷醉。这首《无题》虽写梦醒,然而读来更是如梦难醒。
醒时月斜楼上,五更钟响。凌晨的梦每每特殊清晰,如果梦见久别相思的人,那将无异于一场梦中的约会。
梦见他或者她,从翡翠被、芙蓉帐来看,应该是她。抛开这个细节,性别身份则可换为你我他她。只要谁曾艳遇爱情,谁便是刘郎。
与恨俱醒,仍醒在这张床上。恨他“来是空言去绝踪”,这张床上还铺着同样的被子,还挂着同样的帐子。玉轮和钟声莫非都来做证,见证他的无情,见证这个梦?
“梦为远别啼难唤”,梦里的人一样平常都是不明以是地涌现,飘然而至杳然而去。梦中也每每没有韶光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只有当下。这首诗却不同,在梦里由于远别而哭到难唤,此梦实在太真实。梦醒之后,被强烈的思念敦促,墨都来不及研浓,伏枕疾书。
书成,顿而复苏。再看“蜡照半笼翡翠被,麝熏微度绣芙蓉”,忽兮恍兮,个中有情。不知是喜是悲,才要欣慰,已觉伤悲;才觉伤悲,又感欣慰。李白的《长相思》曰:“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空余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犹闻喷鼻香。喷鼻香亦竟不灭,人亦竟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点青苔。”与义山此二句心有戚戚。
很多当代诗在写情人分开之后,也常常写到床。别的旧物触动的伤感,皆不及床。床不仅触动伤感,还放大空旷,并给被留下的人以怪异的觉得。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一万”作为虚数,夸年夜渲染相见的不可能。蓬山已非舟车足力所能及,奈何还隔了蓬山一万重。瞬间,这封被催成的信,倏然寂灭。
在前三首词中,梦醒的人没有在深夜写信。在末了一首诗中,信是写了,但即是没写。然而,诗,难道不是更好的信吗?所有的好诗不都是情书吗?写给那人,写给自己,写给天下,更写给无穷的远方、无数陌生的亲人。
作者 | 三书
编辑 | 徐悦东
校正 |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