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史上,不管是文人雅士还是普通人家,大家对竹子情有独钟,他们都会在庭院中开辟出一块空地,种上几株竹子。栽种竹子的地方或大或小,但这并不影响人们空隙之余欣赏翠竹的心情,人们对竹子的喜好之情是一样的。
人们喜好竹子,由于竹子青翠挺立、高风亮节、凌寒傲雪、经冬不凋、四季常青,更由于竹子保持不懈的性情受到了人们的称颂。
人们由于竹子的各类美好品质,将它与松、梅合称“岁寒三友”。古往今来,历代文人对它们倾注了无限情怀。竹子既有梅花迎傲霜雪的倔强品质,更以高雅客气、乐于奉献的美德,摒弃了梅花孤芳自赏的不敷,使之形象更趋完美,赢得并霸占了人们心中独特的地位。
在悠悠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竹子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国悠久的文化与竹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竹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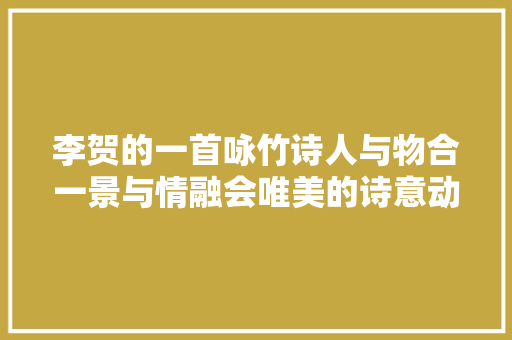
竹文化
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淇奥》一诗中,就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
《淇奥》借绿竹的挺立、青翠、茂盛来赞颂卫武公的高风亮节,首创了以竹喻人的先河,成为中国诗歌以及文学作品中竹文化的起源。
我国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竹文化起源于诗经时期,自《淇奥》之后,竹子已经成为了人们常常去赞颂的植物之一,竹子也被授予了美好的风致,诗中的竹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历代文人墨客对竹吟咏不断,创造出大量的咏竹文学作品。魏晋期间有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绅士风姿;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诗中也写道:“宁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竹子的挺立、常青不凋的色彩,以及竹子在风中的摇荡的声音和清疏的身影,尽入诗怀,墨客并借用竹子的形象去象征与表现客气、高洁、耿直、刚毅、思念等情志和思想,构成情志寄托于竹意象、情志贯注于竹意象、情志超越于竹意象等几种文学符号类型,显示出传统文人清新淡雅、宁静柔美的审美特色。
竹子在人们心中已然成为品质高尚,不畏困境,不惧艰辛,中通外直,坚忍不拔,宁折不屈,高风亮节的象征。
在我国诗词长河的诸多的赞咏竹子的作品中,不得不提一下唐代墨客李贺的一首咏竹诗《昌谷北园新笋》。李贺的家乡在昌谷(今河南省宜阳),那儿有青山碧水,茂林修竹。特殊是翠竹,险些长满了昌谷的每一块山林,每一块空地,昌谷切实其实便是竹子的海洋。
李贺十分爱竹,在摩挲不雅观赏之余,写了不少咏竹的诗句,有时还直接把诗写在竹子上,以寄托自己的情思。李贺的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斫取青光写楚辞,腻喷鼻香春粉黑离离。
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
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李贺出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洛阳宜阳县三乡)。李贺祖上是李唐皇室宗亲,可是到他这一代家道早已中落。
同时期墨客李商隐为李贺写过一篇传记体的《李贺小传》,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恒从小奚奴,骑巨驴,背一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见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
’”。
由此可见李贺不遗余力的好学程度,李贺在学习上付出了大量的韶光和精力。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五岁的李贺就已经誉满京华,与同时期的大墨客李益齐名了。
李贺很小就有诗名,最早受知于韩愈。李商隐的《李贺小传》中就说李贺“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也便是说说,一代文学年夜师韩愈独具慧眼地创造了李贺的才华。
李贺是中唐有代表性的墨客之一。 他的诗歌风格瑰丽奇峭,意象繁密跳脱,用字坚锐深奥深厚。他的诗作能给人带来梦幻的色彩的,力量的震荡,竹苞松茂的享受,李贺的诗歌被誉为唐诗阆苑中的一朵奇葩。
韩愈画像
可是,功名并没有向这位才子投来橄榄枝,运气彷佛也没有垂青过这位才子。他参加科举考试,总是与登科擦肩而过,并不是由于他的成绩,而是他连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审核通过,缘故原由竟然是李贺父亲名字中的“晋”字与进士的“进”字犯嫌。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借口。
只管对李贺有知遇之恩的韩愈“质之于律”、“稽之于典”,韩愈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关系积极斡旋,争相奔忙,为李贺辩解,但依然无法改变这一现状。万般无奈之下,李贺不得不离开长安。
李贺画像
未能参加进士考试,对李贺法人打击很大,当年回到昌谷后,他写了不少抒愤之诗。大约因其为李唐宗室的后裔,又有韩愈为之推奖,元和六年(811年)五月,李贺又返回长安,经宗人推举,并考察后,担当了从九品的奉礼郎。从此,李贺在长安度过了长达3年的仕宦生涯。
由于迁调无望,功名无成,李贺心中的哀愤与孤激进步神速,加之妻子病故,这统统让墨客忧郁成疾,从此一病不起。
元和九年(814年),他决然辞去奉礼郎之职,重回昌谷,过起了隐居的生活。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正待有一番作为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这样的生活,个中的弯曲与无奈,落魄与哀怨是可想而知的。
这位蹉跎半生,空负一身才华的墨客,兜兜转转终于回到了原点,他也终于在家乡走完了自己二十七年的短暂人生。
李贺在家乡昌谷写的这首咏竹诗,旨在表达心中堆积已久的哀怨之情。结合李贺的仕宦之旅和人生境遇,可以看出,竹的形象就与墨客自己直接抒怀的形象叠合起来,不再是独立清闲的实体。这样写,是虚实结合的写法,虚与实之间并行不悖,读来让人无限感慨。
开篇两句“斫取青光写楚辞,腻喷鼻香春粉黑离离”,意思是说:刮去竹子上的青皮,刻上楚辞般的诗句,白粉光洁的竹身上留下一行行玄色的字迹,字迹经久弥新、文字飘喷鼻香。
这两句描述墨客在竹上题诗的情景,笔势如题写诗行的笔锋一样,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流畅的措辞文采斐然,又不失落蕴藉蕴藉。透过诗句,这位空负才华的怀才不遇的墨客在竹子上题诗的情景彷佛跃然纸上,历历在目,这是一个动听的画面。
句中的“青光”指代竹皮,同时把竹皮的颜色和光泽清楚地显现出来。“楚辞”代指墨客创作的歌诗。
墨客从自身的生活感想熏染遐想到屈原的遭遇,这里因借“楚辞”蕴藉地表达了郁积心中的怫郁之情。首句短短七个字,既有动作描写,又有情绪表示,蕴意十分丰富。
尤其是墨客描摹竹子的形态时,利用了比拟映照的手腕:新竹散发出浓郁的芳香,竹节高下布满白色粉末,显得活气勃勃,活泼可爱。可是题诗的地方青皮剥落,墨汁淋漓,又使竹子的美好形象受到玷污。
墨客奥妙地以“腻喷鼻香春粉”和“黑离离”这一对色彩形成强烈反差的比拟,来表现内心的忧愤。
后两句“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大意是说:新竹无情但却愁恨满怀,谁又能够看得见呢?竹叶上的露珠滴落,彷佛在雾里号泣的泪水一样,压得千万枝竹枝弯下了身躯。
这两句以竹叶上的露珠象征伤心的泪水,着重表达墨客忧愤的感情。墨客时势所迫,他只有在家乡昌谷的竹林中,彷佛才能得到心灵的抚慰,光阴镌刻在墨客心灵上的创伤,也彷佛只有在竹林中才能得到治愈。
“无情有恨”,指的是墨客在竹子上题诗的事,墨客毁损了新竹俊美的容颜,可说是“无情”的表现。而这种“无情”正好是长期郁积在墨客心中的无法抑制的怫郁导致的。
这是一种若何的怫郁呢?清代学者姚文燮在为李贺的诗集作注时,曾写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语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述:“良材未逢,将达成以写怨;芳姿点染,外无眷爱之情,内有沉郁之恨。”
姚文燮一语中的地指出了李贺此时的处境以及心境,这样的评价也是相当中肯贴切的。
李贺在家乡昌里时,不止写过一首咏竹诗,在另一首咏竹诗中,墨客写道:“箨落长竿削玉开,君看母笋是龙材。”
“龙材”指的是出类拔萃的竹子,在墨客的眼中,也出类拔萃的人才。墨客以“龙材”自喻,希望自己能像雨后春笋那样,节节拔高,直上青云。
但结果却是险些无人欣赏,李贺生前,他的诗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讴歌、评论、转发。
越是美好的希冀,与现实的反差也就越大。万般无奈之下,墨客只能回到故里,整日与竹为邻,与竹为伴,度过了生命的末了光阴。
墨客在竹子上题诗,无非是为了排解心中的怨恨。然而无情也好,有恨也好,却无人得见,无人得知。
这从“无情有恨何人见”一句中就可看出端倪,墨客摒弃直抒胸臆的陈述句,用疑问句的语气和句式将心中感想诉诸笔端,在大开大合的写作手腕中寄托情思,诗意也呈现出变革多姿的风貌。
细细品味末了一句,墨客蕴藉地回答了上句提出的问题,措语委婉,然而感情充足。墨客极力刻画竹子的愁惨容颜:烟雾环抱,面孔难辨,就像是伤心的女子掩面而泣。
而压在竹枝竹叶上的露水,时时地向下滴落,这与因伤心而垂泪的女子的形象是何其的相似。
表面看起来,墨客是在写竹子的愁苦,实在是移情于物的手腕,也便是将人的情绪授予在竹子上。人的怨情变成竹的怨情,从而创造出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动人境界来。
此诗通篇采取“比”“兴”手腕,移情于物,借物抒怀。就表现手腕来说,写竹的形态是实写,写人的感情是虚写,虚实结合,相得益彰;而从命意来说,则恰好相反,写人的感情是实写,写竹的形态是虚写,虚实相生,情景交融。
由于墨客虽然从头至尾都在写竹子,墨客的形象却又无处不在。墨客的描述、举止和精神寓含在诗句中,寓含在竹子的形象中,人与物完美地领悟在一起,景与情贴切地交织在一起。
竹子的愁愁容宛如人的愁容,竹子的哀情也与人的哀情相通,人与竹守望相助。然而墨客兴寄深远,将自己的情绪寄寓在竹子上,避免直抒胸臆的口头对白,从而形成了墨客与竹子的心灵对白。
李贺的这首咏竹诗,是诗人情感的倾泻,也是诸如有着像李贺这样人生境遇的古代文人情感天下的一个缩影。
中国古代文人与竹子之间的心灵交契,既是一种文化情态,更是一个历史过程。竹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既是人的品质的表示,也是墨客对认知办法的探索与诠释。
李贺的这首诗之以是动听,正是由于墨客以这样的办法寄托了自己的情思,人与竹的心灵交契,竹子被授予的文化情态,墨客对生命认知的探索与全诗,全都浓缩在这首只有二十八字的诗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