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谈
《大宋宫词》开播已久,不雅观众对之爱恨交加,爱它道具纷华靡丽,恨其剧情支离破碎。
电视剧的片头曲,是一首古歌谣《越人歌》,演唱者是谭维维,歌手的唱功自不必说,嗓音沁人心脾,宛转空灵。
但笔者实在不能理解,宋词数量既多,质量又佳,导演何以选择一首远古歌谣,作为描述宋代宫廷生活电视剧的主题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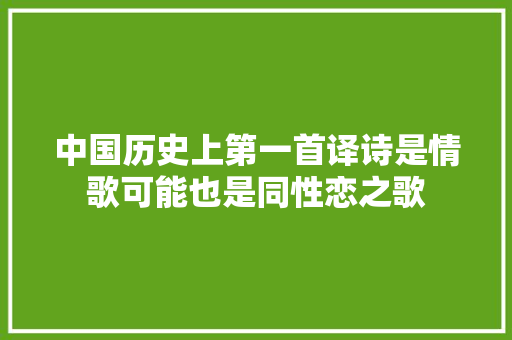
这还不是重点,这首歌谣有很大争议,导演是否真正理解《越人歌》,老谈也是打了一个重重的问号。
纵使《越人歌》写得极美,但以之作为《大宋宫词》片头曲,笔者坚持认为,多少有些望文生义,文不对题。
很多年之前,冯小刚拍过一部《夜宴》,电影中也涌现过《越人歌》,周迅与吴彦祖,便是影片的主演。
那时的周迅,好比今更俏丽,美如一幅画;那时的吴彦祖,好比今还英气,英气如生风满树。
周迅扮演的青女,着一身素衣,戴一片面具。宫殿的清香,氤氲了她的素颜;清澈的嗓音,却能穿透统统恍惚与迷漫。
琵琶轻弹,舞袖缓行,歌声悠然:
今夕何夕,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青女的《越人歌》,唱得又缓又慢,在舒缓中犹然透出一股冷峻,那是血溅碧水的声音。
歌声既毕,一场杀伐随即展开。争斗与刺杀,如歌声般舒缓,黑衣黑甲的卫兵,一袭白衣的吴彦祖,就像是在水墨画中杀伐争斗。
周迅所演唱的《越人歌》,显然便是一首情歌。
情歌之谜
从《越人歌》文本来看,它也的确更像一首情歌。
后世的情诗,对其亦有借鉴。譬如,《诗经》当中有一首《绸缪》,诗歌以反复吟诵的办法,戏谑的口吻,比兴的手腕,描述新婚闹新居的场景。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
今夕何夕,见此外子?
子兮子兮,如此外子何?
《绸缪》中所谓“今夕何夕”,即是对《越人歌》中“今日何日兮”的直接照搬。
《越人歌》的典故,起源于汉代学者刘向,记录的一则故事。
楚王的弟弟名曰鄂君子晳,他乘青翰舟泛游湖泊,趁着鼓声歇停,万籁俱寂之时,爱慕他的越人舟子,对着鄂君身影,唱起这首情歌。
舟子用古越语唱歌,刘向也如实将原文记录下来: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是不是像一篇乱码?看不懂没紧要,鄂君当初也听不懂,他让旁人翻译为楚国话,于是便有了传诵千古的《越人歌》之词。
这首情歌,带着淡淡忧伤,旖旎缠绵,鄂君听了也不由动容。
鄂君轻轻走到舟子身边,将她拥入怀抱,又为其盖上锦衣绣被。
很多人以为,唱歌的渔夫,乃是一介女子。譬如唐朝墨客李商隐,作过一首《念远》之诗,个中有如下几句:
皎皎非鸾扇,翘翘失落凤簪。
床空鄂君被,杵冷女媭砧。
李商隐写得很有情调,床幔之上,诸物俱备,唯独短缺锦被,以是显得空荡荡。说得就彷佛,少女在期待王子的到来。
清代大儒梁启超,也认定渔夫即是女子,他还宣告,《越人歌》实在该当是“越女棹歌”。
不论如何,这种阐明最是浪漫,自然也更深入民气。
哪怕到了当代,台湾墨客席慕蓉,还将《越人歌》,改编成一首唯美柔和的当代诗歌。
用我清越的歌/用我朴拙的诗
用一个自小和顺羞涩的女子
生平中所能
为你准备的极致
在传说里他们喜好加上美满的结局
只有我才知道/隔着雾湿的芦苇
我是若何目送着你逐渐远去
席慕蓉直接将“棹船越女”,具象化为“自小、和顺、羞涩的女子”。
在这首当代诗歌的附记里,席慕蓉写出自己对《越人歌》的理解:
有人说,鄂君听懂了这首歌,明白了越女的心迹后,微笑着把她带回去了。但是,在阴郁的河流上,我们所知道的结局不是这样。
席慕蓉的这本诗集,的确就叫《在阴郁的河流上》。笔者读罢附记,却愈发糊涂,真就沉迷在“阴郁的河流上”了。
如席慕蓉所言,我们知道的结局不是这样,那会是若何呢?原文中可是把结局说得很清楚,鄂君“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
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颂歌之谜
《越人歌》虽然原唱与译文俱在,但若想读通原歌,困难极大。缘故原由无他,古越语随着时期的发展,也经历了不断地演化。
首先动手研究《越人歌》之人,并不是浪漫的墨客,而是较真的措辞学者。
对《越人歌》进行研读的第一人,乃是韦庆稳师长西席,韦公是壮族拉丁笔墨创始人之一。他将乱码一样平常的原文,解构为壮语,再翻译成汉字:
今夕何夕,舟中何人兮?
大人来自王室,蒙赏识约请兮,当面致谢意。
欲瞻仰何处访兮,欲待饮何处觅。
仆戴德在心兮,君焉能知之兮?
除韦师长西席之外,还有别的学者,将原文解构成侗语、占语、乃至马来语,尔后逐一翻译解读。
这实在也无可厚非,虽然歌者以“古越语”演唱,但“古越”之地,到底对应本日何地,一贯以来,也都是学者辩论之所在。
但学者达成的共识是,渔夫该当是一位男士,他以谦卑的姿态,阿谀赞颂鄂君。
这首《越人歌》,反而是一首颂诗。
渔夫以谄媚迎合的姿态,奉承崇高的君子。鄂君表现得很名流,原文中所谓“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实在也不是见不得人的耻辱之事。
按照楚人的礼节,鄂君双手扶了扶越人的双肩,又持重地把一副绣满花纹的被面,披在他的身上。
学者也论证出,鄂君的举止,没有狎昵的身分,只是一种礼俗罢了。
诚然,早在先秦时期,女生的确和男士一样,长于划船。譬如产生于先秦时期的民歌《河激歌》中,有如下几句:
罚既释兮渎乃清。妾持擑兮操其维。
蛟龙助兮主将归。呼来櫂兮行勿疑。
一个“妾”字即点明渔夫的性别。
但学者的研究同时表明,为鄂君唱歌的渔夫,该当是个男生。
鄂君所乘坐之舟,可不是一样平常的筏子,原文上说的是“青翰之舟”,以翠羽和犀尾为饰的华盖,上面还装满乐器,所谓“会钟鼓之声”。
试问,女生有力气驾驭这艘“豪华游轮”吗?
同性恋歌之谜
演唱《越人歌》之渔夫,该当是一个男性,还有其余一个缘故原由。
《越人歌》实在起源于两个故事,两个故事之间,还存在着“套娃”的关系。
话说,楚国襄成君受封之日,他穿翠衣,带玉剑,履缟舄,艳服出行准备渡河。
恰在此时,楚国大夫庄辛经由,庄辛看到襄成君,心里十分欢畅,于是上前见礼,并且很冒昧地说道:“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
襄成君忿其僭越的行为,终极不予答理。庄辛洗了洗手,给襄成君讲起了,前文所述鄂君的故事。
要知道,鄂君官至令尹,这个职位是楚国的最高官衔,执掌一国之国柄,身处上位,以率下民。襄成君不过刚刚册封受爵,人家鄂君显然比他崇高多了。
然而,鄂君犹然可以与渔夫交欢尽意,我堂堂楚国大夫,为何就不能握你襄成君之手?
末了,襄成君果真把手递给了庄辛。
大夫庄辛毫无疑问是男性,他若想回嘴襄成君,所例举的渔夫,一定也是男性。
不知诸位创造没有,庄辛与襄成君的故事,渔夫和鄂君的故事,通篇都带有若有若无的暧昧气息。
庄辛先是对襄成君说,“臣愿把君之手。”襄成君末了把手交给他,随口又说了一句话:“吾少之时,亦尝以色称于父老矣。”
鄂君就更直接了,听罢渔夫的表白,欣欣然“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
《越人歌》难道是中国第一首同性恋的赞歌?
学者都研究不通的议题,笔者哪有资格下结论。
好在威信也有了论断。
理学大家朱熹,曾经评价过《越人歌》。他首先对其艺术性,给予了高度评价:“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学而得其馀韵,且于周太师六诗之所谓兴者,亦有契焉。”
但说到《越人歌》之内容,朱贤人以寥寥七字评价:“其义鄙亵不敷言。”至于为何鄙亵,朱熹没有明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说呢?
第二个威信,来自于本日的字典。《国语辞典》中,有“鄂君被”词条,它被阐明成,“歌咏男女欢爱的典故。”
《国语辞典》实在也说得暗昧,恐怕阐明成男男欢爱更贴切吧?
威信当然要保持正襟危坐的姿态,而后世的小说家,完备放开了写,就像是解脱缰绳的野马。
著名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书中有如下记载:“朋友之情,更胜于男女!
你不看别的,只有鄂君绣被的故事。”
其余,将《越人歌》翻译为英文的柏丽尔女士,也方向于认为,该歌谣乃是“同性恋之歌。”
同性恋行为之对错,笔者不宜揭橥辞吐。但将这首充满谜题的古歌谣,用于讴歌北宋真宗天子的爱情,其实有些欠妥。
但若是导演深谙《越人歌》之奥妙,将对歌曲的诸多谜题,引申为宫廷、宗族、君臣之间的迷离与制约的关系。那导演真是太高了。
对不起导演,我实在是编不下去了。
-作者-
老谈,always talk,总是夸夸其谈之人,除此外,别无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