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花蒙蒙水泠泠,小儿啼索树上莺。(唐·贯休《春晚书山家屋壁二首》)
狎浪儿童,横江士女,笑指渔翁一叶轻。(清·吴伟业《沁园春·不雅观潮》)
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唐·胡令能《小儿垂钓》)
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宋·杨万里《舟过安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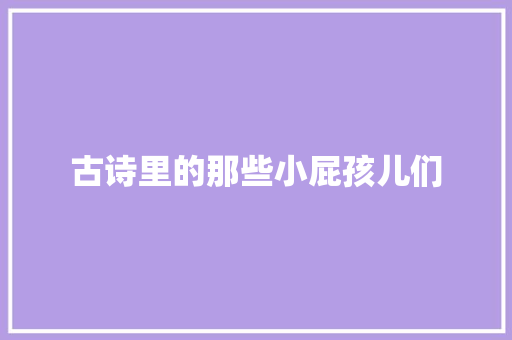
南村落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当代社会,小屁孩儿们仍旧油滑,试穿妈妈的高跟鞋啦,为了几个空瓶子倒掉妈妈昂贵的护肤品啦,掀翻菜盘子啊,将家里的墙壁随意涂鸦啦……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家里有小屁孩儿的请对号入座。
古时的屁孩儿们,也很油滑,他们怎么个油滑法儿呢?
他们撑小船儿“偷采白莲”;他们哭着索要树上的黄莺;他们笑话渔翁的船太小;他们怕惊跑鱼儿,以是不理问路人;他们撑伞借风飘船;他们陵暴杜甫,抱走他屋顶的茅草……
嬉戏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宋·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清·高鼎《村落居》)
三贤尚未明斯旨,羊鹿牛车孩子戏。(宋·释印肃《颂十玄谈·祖意》)
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取当银铮。(宋·杨万里《稚子弄冰》)
桑柘外秋千女儿,髻双鸦斜插花枝(元·卢挚《蟾宫曲·寒食新野道中》)
古今一样,屁孩儿们喜好嬉戏的天性不会改变。不过,随着时期发展,当代孩子们的嬉戏大多变成了手机与电子游戏,与大自然打仗太少了,缺了一份天然的拙朴娇憨,实在有些可惜。
而古时屁孩儿们嬉戏玩耍,在自然之中玩自然,在野外之中野着玩儿,以是,更加亲近大自然,充满童趣。他们追黄蝶,放纸鸢,戏羊鹿,脱晓冰,荡秋千……俨然便是一个个自然的精灵。
劳动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清·袁枚《所见》)
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宋·雷震《村落晚》)
童子柳阴眠正着,一牛吃过柳阴西。(出自宋代杨万里的《桑茶坑道中》)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薄暮后,不脱蓑衣卧月明。(唐·吕岩《牧童》)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其七》)
小男供饵妇搓丝,溢榼喷鼻香醪倒接䍦。(唐·李郢《南池》)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清平乐·村落居》)
蚕娘洗茧前溪渌,牧童吹笛和衣浴(唐·贯休《春晚书山家屋壁二首》)
半夜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唐·颜仁郁《田舍》)
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唐·孟浩然《田家元日》)
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唐·张籍《野老歌 / 山农词》)
墨客最爱写乡野的孩子,大约皇家贵族的孩子,他们不便随意写,也可能以为短缺可写性。不少墨客在“樊笼”里呆久了,骨子里很憧憬田园生活,而他们瞥见乡野中参与劳动的孩子时,便难抑诗情;或者,墨客自己便是田园隐居人,免不了写自家劳作的孩子。
以是,写孩童劳动的古诗很多,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乡野生活实在也不随意马虎,很多时候,孩子们也要参与到劳动中去。
古时,最宜孩童们做的事便是放牛,诗中呈现了牧童的千姿百态,骑着黄牛唱歌,在牛背山吹笛、睡觉;其余的,便是伴随父母劳作,在阁下搭把手。
这些劳动中的孩子,仍不失落天真可爱,放入诗中,增长了一丝活泼清新之感。
佳节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宋·苏轼《守岁》)
袨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金朝·元好问《京都元夕》)
我们小时候最盼过节日,掰动手指头数日子,一天一天地等,一日一日地盼,节日来了,父母免不了要劳碌一场,在烟火的热闹中,孩子们窜来窜去,偶尔偷食桌上已做好的美食,然后一溜烟儿跑了出去,年夜声吆喝着呼朋引伴。儿时那种大略的快乐,至今影象犹新。
实在,无论光阴怎么变,孩子们对节日的情绪千年难易。古时的孩童与当代的我们并无两样。除夕之夜,他们不理会父母的逼睡,欢闹到天明;元宵之时,他们在街上耍灯火…
这种贯通古今的景象与拙真情绪,在孩子身上完全地保留了下来。
迎客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唐·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幼童疑是有村落客,急向柴门去却关。(唐·崔道融《溪居即事》)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唐·贺知章《还乡偶书二首·其一》)
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唐·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隐士宿置酒》)
儿时,我是非常愿望家中忽然来客的。那种溘然而至的惊喜之感,让我特殊快乐。为什么快乐,有些说不清理由,纯粹便是惊喜,便是快乐。
我想古代的孩子也会这样,他们扯着客的衣服不舍其拜别;疑惑有村落客到了,急急去开柴门;笑问客从哪里来。
艰巨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唐·杜甫《百忧集行》)
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唐·杜甫《羌村落三首·其三》)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悲惨。(唐·杜甫的《狂夫》)
看了不少写童子的诗,唯有杜甫的最苦。真真以为杜甫先生长西席是个愁眉苦脸的人,写天真烂漫孩子,他也能写得苦出汁来。
饥饿的孩子向父亲索要饭食;长年征战,孩子们都上了沙场;没有了朋友的经济声援,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
杜甫有错吗?没有!
大多墨客喜好写美好,但天下全是美好的吗?杜甫如实地写出封建时期,穷汉家孩子生活悲惨的面貌,当头一棒地让众人保持了几分复苏,这世上原来还有这么多孩子生活困难,失落却了童年应有的欢快无忧。
新生孩子擎铁棒,直上须弥打一槌。(宋·释法泰《偈十三首·其一》)
唯见两童子,门外汲井花。(唐·顾况《题卢羽士房》)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唐·贾岛《寻隐者不遇 / 孙革访羊尊师诗》)
诗中的孩童们还有另一种独特的存在——僧童、道童。
这些孩子大多没有很好的出身,不少是被僧道之人养大的,自然而然就生活在寺庙和道不雅观中。当然,也有不少因父母无力养活而送到寺庙的。
这些孩童虽有些故作的老成,但仍如一缕清音,让古诗的意境渺远了起来。
光阴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一直止向前,读读诗中的孩童,我们才会创造,千年剧变,唯一不变的是孩子们固有的那份油滑、天真与烂漫。
许是,越纯挚的东西越历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