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牛远远过前村落,短笛风吹隔陇闻。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八岁时,家乡有位举子进京赶考,黄庭坚写了一首《送人赴举》诗,“已非髫稚语也”:
青衫乌帽芦花鞭,送君归去明主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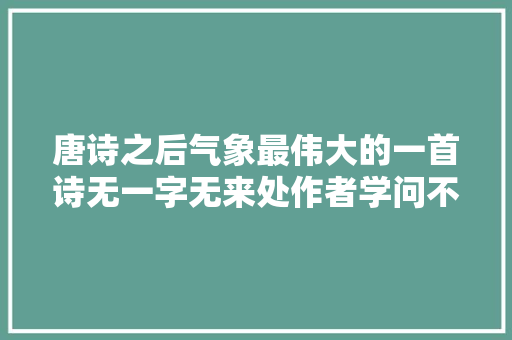
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
黄庭坚两次为乡试解头(第一),治平四年(一〇六七)进士及第,熙宁五年(一〇七二)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元丰三年(一〇八〇)除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县令。
元丰五年(一〇八二)深秋的一天傍晚,黄庭坚登临县城东边的“快阁”不雅观览,便写下了这首七律名篇《登快阁》: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黄庭坚说:“ 子美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杜、韩自作此语耳。古人之为文章,真能熏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文字,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卷一引山谷黄鲁直《诗话》)这既是对杜甫、韩愈等人的推崇,也是黄庭坚的役夫自道。“无一字无来处”,“灵丹一粒,点铁成金”,正是黄庭坚诗歌的一大特色。在《登快阁》诗中,这一特色尤为突出。
“公家事”并非日常事务
“痴儿了却公家事”,典出《晋书·傅咸传》。西晋惠帝时,外戚权臣杨骏辅政,权倾朝野。尚书左丞傅咸屡次上书直言朝政弊端,又给杨骏写信切直讽谏, 杨骏便想让傅咸出任京兆、弘农太守。杨骏的外甥李斌劝杨骏不该贬斥正派的人出任外官, 杨骏这才作罢。杨骏的弟弟杨济一向与傅咸友好,便给傅咸写信说,天下大事, 不可能全部了却, 可是您对每件事都想了却它。俗话说:“生子痴,了官事。”天生痴呆的人做官,总想着了却官事,实在,官事是不随意马虎了却的。对付官事只有装痴作呆才能快乐,如果齐心专心扑在公事上,那便是傻子。
“生子痴,了官事”,乃君主专制时期的官箴金鉴,而黄庭坚却说自己正是这样的“痴儿”,齐心专心想“了却公家事”,本日“公家事”总算了却了,这才登上快阁,欣赏晚晴。曾子鲁师长西席把“了却公家事”解作“处理完了一天的公务”(朱安群主编《黄庭坚诗词赏析集》,巴蜀书社1990年6月初版第66页),似不当。由于如果这样阐明,那每天放工后都可以登快阁,而黄庭坚到任已经一年半多了,这才“了却公家事”而登快阁,可知这里的“公家事”绝不这天常公务,而是另有所指。
那么,黄庭坚“了却”的“公家事”到底是什么呢?实在,县令最紧张的“公家事”便是每年为朝廷收取赋税,黄庭坚一到任就面临着“了却”这个“公家事”的难题。当时,王安石二次罢相赋闲江宁(今江苏南京),“新法”的弊端日益显现,国家财政极度困难。朝廷便于元丰三年敕令增销官盐配额,各地新增收的盐款全部上缴朝廷,以缓解经济危急。食盐本来就有官家逼迫性专卖的定额,官盐比私盐质次价高,但官府规定百姓必须购足了定额的官盐之后才能购买私盐,否则就会受到严厉惩办,结果使得许多穷苦百姓长期吃不到盐。
苏轼就曾讥讽过盐法的峻急:“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山村落五绝》其三)苏诗“意言山中之人饥贫无食,虽老犹自采笋蕨充饥,时盐法峻急,僻远之人,无盐食用,动经数月。若古之圣贤,则能闻《韶》忘味,山中小民岂能食淡而乐乎?以讥盐法太急也。”(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
春秋时候,孔子到齐国,宴席中乐师演奏舜帝时流传下来的《韶》乐,孔子欣赏着迷,竟然没有尝出宴席上的肉味。他感叹说:“想不到音乐有如此美妙的境界。”今本《论语·述而篇第七》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古书是竖着书写的,“三月”实际是“音”字的讹误,也便是说,原文是“子在齐闻《韶》音不知肉味”,而非“三月不知肉味”。苏轼在《上文侍中论榷(专卖)盐书》中说:“私贩法重而官盐贵,则民之贫而懦者或不食盐。往在浙中,见山谷之人,有数月食无盐者。”
江西发卖的官盐一向是淮盐,如今又要在原发卖定额之外增销广盐,这就使本来已经不堪重负的穷苦百姓更加苦不堪“盐”。而黄庭坚这个地方官所要“了却”的,便是这样的“公家事”。他到任的第一年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到下面“劝盐推新令”,结果创造百姓竟然淡食无盐——“此邦淡食伧”;家中更是一贫如洗——“俭陋深次骨”。可是,自己还要对这些穷到骨头的百姓进行搜刮搜聚,情何以堪?本来天子对百姓恩如父母,但是下面的小吏为了完成收缴任务,竟然用鞭子抽打那些交不上钱的百姓:“县官(天子)恩乳哺,下吏用反攻。”下吏如此欺凌百姓都是上面逼迫所致,朝廷为什么要频繁地以赋税的收缴情形来考察地方官执政的能力,评定其政绩的等级呢?想到这些,他真想把官印解下来,弃官归隐算了:“何频课殿上?解绶行采葛。”(《仲春二日晓梦会于庐陵西斋作寄陈适用》)
梦幻是现实的变相投影,从这记梦诗中,我们可以隐约感知到他去年的考课很可能不佳。但毕竟是上任的头一年,新官总要有个适应的过程,还可以推说以前的底子不好。第二年可就不同了,必须完成赋税的征收任务才行。因此,这年三月,黄庭坚便深入到山区配售官盐。他亲眼目睹了百姓的悲惨生活:“黄雾冥冥小石门,苔衣草路无人迹。”“穷乡有米无食盐,今日有田无米食。”很多庄家的门前小路上都长满了苔衣野草,荒无人迹。以前是有米无盐,尚可淡食,如今连米也没有了,官府还要强行增售官盐。“但愿官清不爱钱,长养儿孙听使令。”(《大蒙笼》)墨客希望统治者不要这样强行搜刮,由于杀鸡取卵,后必无卵;竭泽而渔,后必无鱼。不如给百姓留条活路,使他们得以休养生息,子孙能够绵延不绝,统治者也好世代有所使令。否则,百姓都去世光了,统治者往后还使令谁呢?
可是,不管你怎么说,朝廷每年规定的赋税是绝不暗昧的。黄庭坚清正廉明,除了上缴朝廷的赋税之外,地方上的征收只管即便减少,轻徭薄赋,勤政爱民。他书写了《戒石铭》镌刻在县城的戒石上:“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摘引五代十国后蜀末代天子孟昶《戒石铭》)在征收赋税的时候,“未尝督责百姓甚急也”(《上运使刘朝请书》),从而赢得了百姓的理解和爱戴。从三月到八月,黄庭坚深入所辖山区四处奔波,本日总算“了却”了“公家事”,这才登临不雅观景,放松一下。
“倚晚晴”不是倚靠晚晴
“快阁东西倚晚晴”,很多选本这句没有加注,可能以为句意大略明了无须再注,实在这是全诗中最难明得的一句。孔凡礼、刘尚荣师长西席在《黄庭坚诗词选》中注云:“倚:倚靠。倚着栏杆、柱子看晚晴。”(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1版第82页)”这注释本来还算清楚,可是接着又说:“也可以理解为心神专注于晚晴,就彷佛靠着天边。”这就不当了,由于“倚晚晴”并非倚靠着晚晴。“快阁东西倚晚晴”只是省略了一些词语,逐一补上便是“(登)快阁东西倚(栏)(赏)晚晴”。缪钺师长西席说:“‘倚’……这个字的用法实自杜甫《缚鸡行》‘瞩目寒江倚山阁’句学来。”(《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599页)但“瞩目寒江倚山阁”只是“倚山阁瞩目寒江”的倒装,并没有什么省略,且“倚山阁”是正常的动宾构造,便是倚靠着山阁,全句清通无碍,与“倚晚晴”关系不大。
《黄庭坚选集》注释“倚晚晴”说:“李商隐《即日》:‘小苑试春衣,高楼倚暮晖。’又《晚晴》:‘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所倚‘晚晴’,非详细之物,其造语生新,正仿李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一四一页)“倚暮晖”是动宾构造,按照正常的词语搭配,“暮晖”是无法“倚”、不可“倚”的,因此属于超常搭配,确乎“造语生新”。但“倚晚晴”却不然,“倚”的宾语是省略的“栏”,“晚晴”的动词谓语是省略的“赏”,“倚”和“晚晴”既不是动宾构造,也不是其他构造,二者只是挨在一起的词结而非词组,更非超常搭配,“造语”并不“生新”。如果硬要说是“仿李诗”,那也只是表面上的佯仿,似仿而非仿。
这句中的“东西”也很随意马虎误解。《黄庭坚诗词选》阐明说:“云‘东西’,自东到西,从西到东,要尽情,尽兴不雅观赏。”(同前81页)《黄庭坚诗词赏析集》解作“东西徘徊”。《黄庭坚诗选》注释说:“时而东时而西,来往不雅观赏。”(刘逸生主编、陈永正选注,广东公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77页)实在,这里的“东西”并非实指东方西方,而是代指四方,墨客不可能只看东面西面而不看南面北面。把“东西”解作“四方”,在训诂上也是有根据的,《汉语大词典》“东西”条第四个义项便是“犹四方”。
以景写情写何情?
颔联是对所赏晚晴的详细描写,由远及近,先高后低。群山上树木的叶子已经落尽,天空显得更加高远。墨客尽情地欣赏着晚晴的美景,从夕阳西下,欣赏到明月当空,一道清澈的江水,把月光映照得更为通亮。李白诗云:“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秋夜宿龙门喷鼻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柳宗元诗云:“木落寒山静,江空秋月高。”(《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黄诗颔联正是由此化出。“落木千山”,季候当在深秋,即农历玄月;“月分明”,当在农历十五前后。由此推断,本诗当作于农历玄月十五前后,很可能就作于农历玄月十五这天。
《黄庭坚诗选》将第四句解作:“澄澈的赣江在快阁下流过,薄暮,映着一弯初月,更觉分明。”(同前77页)蒋方师长西席在《痴儿、青眼及白鸥———黄庭坚诗赏析》一文中也说:“赣江澄澈,横亘在天地之间,映照着一弯秋月,是那样的清亮,那样的分明。” (《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3期)快阁在太和县城东侧,墨客能看见“澄江一道月分明”,一定是面向东边,薄暮时满月由东方升起,映在江中才会“分明”(通亮)。如果是“一弯初月”,“一弯秋月”,这时的月光并欠亨亮,而且是从西方升起,墨客怎能看见“澄江一道月分明”呢?
王国维师长西席说:“统统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删稿》)本诗的颔联正是以景写情,情寓景中。“落木千山天远大”,而自己这个“痴儿”也“了却”了“公家事”,如释重负,赏心悦目。“澄江一道月分明”,自己开阔的心地,正像这澄澈江水映照的月色一样通亮。墨客之以是要表明自己心地光明,是由于他在“乌台诗案”中被诬陷而受牵连,这既是为自己申述,也是为心腹苏轼鸣不平。
“佳人”到底指何人?
颈联由外转内,由颔联对面远景物的描写,转为对内心天下的阐述,慨叹知音不再,只能借酒浇愁。“朱弦已为佳人绝”,典出《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朱弦指琴弦,佳人喻心腹。伯牙善鼓琴,锺子期善听琴,锺子期去世后,伯牙将琴摔破,将琴弦弄断,表示这辈子不再鼓琴,由于这个世上再也没有值得自己为他鼓琴的人了。黄庭坚说自己也已经把琴弦弄断不再弹奏了,也是由于没有赏识自己的知音了。他在另一首诗中也说:“当时朱弦写心曲,果在高山流水间。”(《再答明略二首》其一)由此可见,黄庭坚确实碰着过知音,只是如今知音不在了。
那么,这曾经的知音究竟是谁呢?宋代史容说“不知谓谁”(《山谷外集诗注》卷十三)。我们可以从黄庭坚其他作品中推测出一些信息。黄庭坚《玉芝园》诗云:“爱君雷氏琴,汤汤(shāngshāng)发朱弦。但恨赏音人,大半随逝川。平生有诗罪,如痼不可痊。今当痛自改,三衅(比喻反复自省)复三湔(jiān,洗)。”由“但恨赏音人,大半随逝川”两句可以推知,黄庭坚所说的心腹“赏音人”并非一人。如《不雅观化十五首》(其六)云:“故人去后绝朱弦,不报双鱼已隔年。”此诗作于熙宁元年(一〇六八),当时黄庭坚二十四岁。诗云“不报双鱼已隔年”,是说已经隔年没有给知音的“故人”写信了,“故人”当指墨客的知音李询。两年前的治平三年(一〇六五),二十二岁的黄庭坚“再赴乡举。诗以《野无遗贤》命题,主文衡者庐陵李询,读师长西席诗中两句云:‘渭水空藏月,傅岩深锁烟。’击节称赏,以谓此人不惟文理冠场,异日当以诗名擅四海。师长西席遂膺首选。”(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五十三)黄庭坚写《不雅观化十五首》的时候,李询可能已经故去,因此诗中才说“故人去后绝朱弦”。
结合《玉芝园》诗和其他资料来剖析,“朱弦已为佳人绝”中的“佳人”当指另一位心腹苏轼。
熙宁五年(一〇七二)十仲春,苏轼任杭州通判,因筑堤之事到湖州拜见黄庭坚的岳父杭州知州孙莘老,在那里读到了黄庭坚的诗,“屹然异之,以为非现代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苏轼《答黄鲁直书》)
元丰元年(一〇七八)正月,苏轼调任徐州知州,履新途中经由济南时,拜访了黄庭坚的舅舅齐州知州李公择。李公择拿出黄庭坚的诗文请他是正,苏轼大为讴歌。黄庭坚得知后,便于仲春致书苏轼,并寄去了《古风二首上苏子瞻》。苏轼在《答黄鲁直书》中夸奖黄庭坚:“《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墨客之风。”并“聊复次韵,以为一笑。”
元丰二年(一〇七九) 三月,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今浙江吴兴)太守。六月,御史台(全国最高监察机关)的李定、何正臣、舒亶(dǎn)等人摘引苏轼诗文中的某些句子断章取义,上表弹劾苏轼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处去世刑。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湖州被捕,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监狱。十仲春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贬苏轼为黄州(今属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不能随便离开,也无权签署公函。在这场“乌台诗案”中,有二十九位大臣绅士因收藏苏轼的讥讽笔墨受到牵连,王诜(shēn)、王巩被发配,苏辙被降职,张方平等八人各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黄庭坚等十八人各罚红铜二十斤。因此,黄庭坚在《玉芝园》诗中才说:“平生有诗罪,如痼不可痊。今当痛自改,三衅复三湔。”乌台诗案,苏轼虽然捡了一条命,但政治出息基本没戏了。在这样的白色胆怯中,黄庭坚哪里还敢再弹什么高山流水,他只能为知音的“佳人”“绝朱弦”了!
因何要“与白鸥盟”?
善鼓琴者自“绝朱弦”,实属无奈,因此他整天跟阮籍似的白眼向人,郁郁寡欢。“青眼聊因美酒横”,典出《晋书·阮籍传》,阮籍会作青白眼,见到世俗之士,就使黑眼珠藏而不露,全用白眼珠对人。阮籍为母服丧期间,嵇喜前来吊丧, 阮籍就用白眼珠对他。白眼珠当然看不见东西,便是不想见他,嵇喜很不高兴地退了出去。嵇喜的弟弟嵇康听说之后,便带着酒挟着琴来看他, 阮籍很高兴, 便露出了黑眼珠。墨客本日“了却”了“公家事”,登上快阁欣赏晚晴,顺便喝上几杯美酒,这才瞪起眼睛,露出黑眼珠,表现出喜悦之情。可是醒酒之后创造,借酒浇愁的结果是“愁更愁”!
虽然今年“了却”了“公家事”,但往后每年的“公家事”又如何“了却”呢?还不如趁早乘坐“万里归船”吹着长笛归隐江湖,与白鸥结伴为友算了!
“万里归船”,暗用杜甫《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为什么要“弄长笛”呢?由于长笛“可以通灵感物,写神喻意,致诚效志,率作兴事,溉盥污濊,澡雪垢滓”(东汉马融《长笛赋》)。
“此心吾与白鸥盟”,既是化用杜甫“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名句,又是暗用《列子•黄帝》中的典故:“海上之人有好沤(鸥)鸟者,每旦之(到)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嫡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白鸥不像人那样机心诡诈,黄庭坚表示愿与白鸥盟而不愿做官,这是对官场尔虞我诈的莫大讽刺。
黄庭坚对当时社会阴郁和官场险恶的认识并非始于今日,归隐江湖的想法更是由来已久。早在熙宁元年(一〇六八),二十四岁的黄庭坚就在诗中写道:“安得酒船二万斛,棹歌长入白鸥群。”(《不雅观化十五首》之七)这与本诗尾联切实其实便是同样的话再说一遍。
归隐江湖,“与白鸥盟”,说说随意马虎,但真正做起来却殊非易事。如果家里没有田产,归隐之后如何生存呢?因此,黄庭坚归隐的牢骚语虽然说了无数遍,但终极也没能兑现“与白鸥盟”的诺言。崇宁四年乙酉(逐一〇五)玄月三旬日甲子,黄庭坚逝世于宜州(今广西宜山)贬所,终年六十一岁。
这首七律诗,短短五十六个字,信息量如此之大,而且拿捏得恰到好处。兀傲奇崛,精切无瑕。思想与艺术二美并具,风骨与情韵熊鱼得兼。足为点铁成金之模范,夺胎换骨之珠峰!
教诲部新颁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将其列入推举背诵篇目,真可谓慧眼识珠!
主编:王多
栏目主编:王多 笔墨编辑: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笪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