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作者:娟子
“一别,便是生平”,是张爱玲的句子,旧时,不理解,还硬着心肠想,交通发达,通讯便捷,如何就能“一别音容两渺茫” 呢?
一起经历了无数毕业季,每次毕业的时候都相拥而泣,反复叮嘱,“常联系,莫相忘啊。”最初的两年,尚能记起承诺,稍事联系,逐渐地随着光阴推移,拿起发话器,就无话可说了,就消淡了那份顾虑心,就失落去了联系的冲动。如果不是被偶尔的“同学会”打捞,恐怕好多人都再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容貌了。
那日到另一所学校搞宣扬,刚把车子停好,穿着土黄装的保安就踅过来了。还以为,我的占道有问题,心间不禁恼生抵触。哪知道,那个保安激情亲切非常,“老同学,还认识我吗?”细瞧阳光下的这个中年胖墩,脑门透亮,举头纹里绽出惊诧的笑意。我寻思了一会,实在没有什么印象,就胡诌了一个名字,没想到他大为冲动,“你说的名字,也是我的同学呀,他在街头卖豆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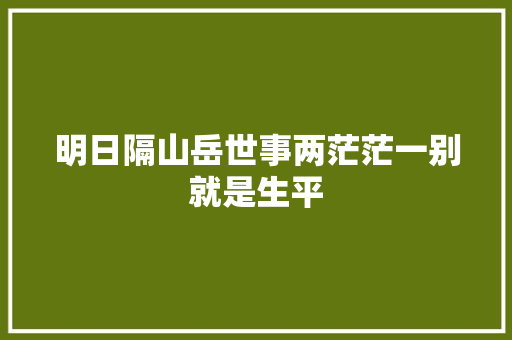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我恍惚忆起,那时候,他们都瘦,个子又高,坐在末了一排,不爱说话。紧接着,他酡颜了似的,说:“小时候,没好好学,小学毕业,就出来混饭了,没想到,你还能记起我们。”随后,我们聊了好多小学的人和事,教我们课的盛老师和一个女同学菊十多年前就去世了,还有一个叫磊的同学在车祸中失落去了一条腿,把自己关子屋里,再也不愿出门……这些不幸的身影当年是什么样子容貌,我已经模糊,末了他无不遗憾地说,“那天,我请班长再搞一次同学聚会,班长没赞许,看样子大家都忙。”
是的,人若蝼蚁,忙劳碌碌,为了生活整天转个一直。年轻的时候为奇迹,壮年的时候为老人和孩子,退休了有些闲,可能已经老病缠身,纵使有相见的心,行动已经不便。
以是,过去的每年,轮到毕业班,同学们痛哭流涕,说,“老师,我们会来看你。”我都豪迈地说,“不要转头,向着远方,那才是方向。”事实也是如此,大家擦干眼泪,整顿行囊,各奔东西,能回来探望的寥寥无几。根本教诲,人生的出发点,比起夸夸其言的远方,忘却我,再正常不过。
但每一届,新生入学,读着那些清纯的的脸颊,我仍在心底说,“好好珍惜这三年,每一天,每个人,三年之后,不复相见,如果他年还有人乐意回顾,我们都没有虚度,就好。”
是的,很多人,一散开,就成了沙漠里的颗粒,细碎,干燥,再也没有粘连的可能。别了,忘了,走着走着,就各自老了。“嫡隔山峰,世事两茫茫”,再殷勤地期待,都抵不过人生的短暂,山河岁月的空茫。
90年代,小学毕业季,我是在县城读的,那时候,也讲升学率,还要考重点初中。但,学校周围的菜地,木柴行,村落落里的果园,大坝上的灌木林,成了我们天然的氧吧,游戏的乐园。两个时令开学前,我都提前从家返校,和一帮处的不久的同学,嬉闹着玩。教我们的语文老师,皮肤白皙,短发齐耳,裙摆蹁跹,能歌善舞,极有活力,我一下子就喜好上了她。那一年,每学期的作文,都能得到市级的名誉。想想喜好文学,大概在那时候就埋下了种子。想想,毕业后,我对她一贯念念不忘。
思品老师,是胖乎乎的老太太,普通话说的特殊好,极爱笑,让我们整段整段地背。印象里,她的想学方法,便是冒死背诵。数学老师,喜好吸烟,不苟言笑,但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就主动把烟熄了,极有规矩。这些老师的音容笑脸,我虽然记得清晰,但一贯没有坐在一块的机会,当然也永久没有了机会。分别在五年前和一年前,思品和数学老师都突发脑溢血,走了。有时机会在管理户籍的同学那里看到语文老师的身份证照片,面庞被皱纹丰裕着,苍然白发。一种被赫然唤醒的老态,让我顿时失落语,不相信人间的沧桑,不相信生命对抗岁月竟如此悲剧,也无奈地俯首称臣。“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不道归来迟晚,多少人已经迟暮。
想想这些相隔并不迢遥,也很难相见的人,不由喟叹:四季可以循环,人生不可从头再来,碰着了,唯有珍惜,珍惜面前,方不负这一场场俏丽的重逢,方玉成俗世静好,岁月安闲。
高山流水,红拂绿绮,不是刻意,而是重逢;雪夜寻友,月下独往,不为苛求,只为兴起。如果有一天,相互遇见,请相信吧, 那都是最美好的时候;那么,请至心相待面前,由于一别,便复永生难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