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豪放派代表词人欧阳修
一、婉约不婉转——柳永词中的反讽柳永是我国北宋期间一位精彩的作词年夜师,他一方面扩展了北宋词初期沿袭花间词派的狭小词境,多写慢词长调,并将白描、直陈其事等写作手腕加入词中,大大增强了词作的可读性,另一方面柳永在词中加入了对仕途官场、阴郁统治、羁旅行役的真实描述与讽刺抒怀,提升了宋词的思想内涵。
柳永的为官之路十分坎坷,他渴望功名,但却始终难登皇榜,虽然历经多年努力,终于考中进士,但却由于写词不合规范而被天子厌恶,导致所得功名被除,未能如愿做官,后期更是厌倦官场,对功名利禄满怀鄙视之情,因此柳永的词作中大多充斥着对朝廷官场、不平现实的讽刺,以及对凄苦人生的多层认识。
柳永的《少年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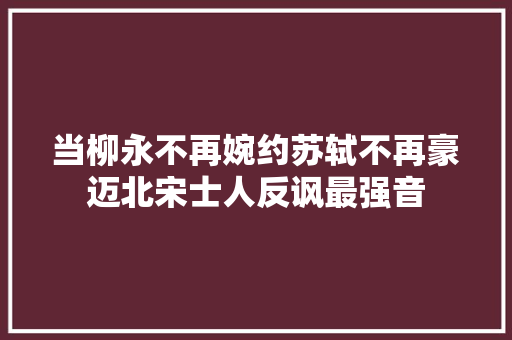
1、鞭笞朝廷社会的反讽类型
(1)主题性反讽
柳永少年时对宦途颇具期望而后却接连落榜,因此其前期喜悦之作便成为与后期失落意词为难刁难比强烈的主题型反讽作品。如《龟龄乐》中"临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说异日殿试与天子相隔咫尺,这次定能一举高中,然而事与愿违,后来的残酷结果是对词中欢畅心情的惨痛否定,因此整首词的主题反讽意味颇深,超出个别语句涵义而上升至整体反讽。
又如《玉楼春》中柳永全词描述北宋天禧二年的汴京繁华之貌,并歌颂了北宋初期的清廉政治,表现出对朝政、时局的关注,但却与北宋末期的朝廷腐败、政治腐烂形成光鲜比拟,词中同样蕴含了柳永对光明仕途的希冀,亦与后期流连于娼寮瓦肆并多与歌妓结交的没落形成比拟,同样是上升至主题的反讽类型。
柳永流连瓦肆的经典形象
(2)讥讽与浮夸陈述型反讽
这两种反讽类型最能凸显柳永的写词风格与处世态度。如在《鹤冲天》中,柳永参加科举考试失落意,便直接向朝廷发出"明代暂遗贤,如何向"的疑问,意为开明的朝代怎可遗落贤臣?进而反讽朝廷及科举制度。此种讥讽型反讽的利用较为大胆,虽直抒胸臆、语气冲动大方却随意马虎招致罪祸。浮夸陈述型反讽更能彰显柳永的放荡不羁与大胆直刺。还有《鹤冲天》中"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更是夸年夜戏谑。作为才华横溢的词作者,虽其仕途失落意受阻,却敢称"白衣卿相",实以夸年夜戏谑的口吻对朝廷进行反讽,而这种自我封官的自傲洋溢大抵只有在柳永身上才能得到如此光鲜的表示。
又如《归朝欢》中"往来人,只轮双桨,尽是名利客",作者这里讲到连过往行人都只顾追求名利,官场中人更是如蚁附膻,通过"尽是"制造一种浮夸语境,说大家皆是如此,实则并非大家贪慕虚荣,用浮夸陈述手腕反讽物欲横流的物质社会,亦讽刺了朝廷主导的思想方向。
"白衣卿相"柳永
2、抒发心中不平的反讽类型
(1)悖论措辞论性反讽
在《凤归来》中,柳永写道"蝇头利禄,蜗角功名",将利禄与蝇头、功名与蜗角两组比拟光鲜的词语同时置于句中,不仅反讽了当时汴京争名夺利的阴郁官场,更表达了自身鄙视功名的超然心态。又如《双声子》中"繁华处,悄无睹,惟闻糜鹿哟哟","当日风骚,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此首作于苏州郊野春秋期间的馆娃宫遗址,颇具登临怀古之气候。作者将繁华城市、当日风骚与万古遗愁作比,更加彰显了其警示君王、借古讽今之意。还有《离去难》中"最苦是,好景良天,尊前歌笑",好天美景、杯前美女应是极美之景,而作者却说是最苦,反讽意味亦十分强烈。
(2)正话反说型反讽
这种类型在柳词中较为常见,如其代表作《鹤冲天》中"青春都一铜。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讲到青春如此短暂,不如将功名抛却去换美酒低唱,而事实上柳永为考取功名苦心研读,拜见宰相晏殊并四处奔忙,因而"忍换浮名"却是"不忍换浮名"。其心中始终未能放下对功名的追求,但也曾对功名产生过厌恶鄙视之感,同样表现对传统封建思想的背叛。
同样还有《轮台子》中的"干名利禄终无益,念岁间阻,迢迢紫陌"也表达了作者对付名利的抵牾情绪。说"终无益",柳永却从未停滞追逐,由此换来遭人暗讽、隔断的结果,因而从反面剖析才能得到正解。正是反讽词句的多次直白涌现,柳永终惹怒朝廷,落得丢官罢职。
官场失落意的柳永
二、豪放不旷达——苏轼词中的反讽苏轼是宋代最具代表性的豪放词人。他文学造诣很高,在诗、词、文、书、画等多方面均有建树。在宋词方面造诣更为突出,他冲破了唐五代以来只专注于男女情爱、景物描摹、羁旅行役为主的狭窄取词题材,更加关注民生疾苦,所写词作中有很多跟现实社会有关的内容,苏轼不仅改变了笼罩词坛多年的婉丽花间词风,而且扩大了作词主题,丰富了词的意境,且善用多种艺术创作风格,并将北宋诗文改造运动的文学创新精神带入宋词,渐成充足冲动大方的豪放词风。
苏轼词中的反讽多表示在其贬谪期间、登高怀古以及对个人生存状态的反思词作当中,这类词作与苏轼的做官经历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说苏轼宦途一贯伴随新旧两党的轮流执政而升迁浮沉。虽然为官期间的多次贬谪使苏轼备受折磨,但是这样的一段经历却亦是其创作的高峰期间,苏轼的大部分词都彰显了其豁达爽朗的乐不雅观心态、人买卖义及哲思体会,也彰显了其自身的反讽精神。
苏轼画像
1、表达个人政见的悖论措辞反讽类型
《千秋岁·次韵少游》中"新恩犹可凯,旧学终难改","君命重,臣结在"的词句将悖论措辞扩大到君臣对立,指出两者存在无法调和的抵牾。欲为国效力却又无法折中,并讲到自身深记天子恩典,但却无法因此改变自身政见。皇命重于泰山,而作者亦有节操,这是十分罕见的将封建士大夫在君、臣两极对立中进退两难的生存状态真正客不雅观地展现出来的悖论措辞,这也正是反讽的浸染之一。
2、抒发个人心境的反讽类型
(1)正话反说型反讽
《行喷鼻香子·过七里濑》里的"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写于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过激而外放至杭州之时。表面说古来明君高士的功名犹如浮云一样平常,皆是浮名而己,实际上反讽当目前廷大兴改革,劳民伤财,亦借助君臣的浮名表达自身被贬的苦闷心情。
同样表述其词中豁达爽朗、急流勇退而又无法真正摆脱官场的那种抵牾思想情绪的词句还有《水龙吟》中"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临江仙·夜归临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八声甘州》"约它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这些词句都阐明了苏轼欲退隐江湖、不问世事之心,但实际上苏轼始终难舍功名,因而在奔波效命与高雅隐居的对抗中形成了正话反说型反讽。
寄情于山水的苏轼
(2)浮夸及低调陈述型反讽
《沁园春·赴密州早行》中"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词句,通过笔、卷数量的放大造成浮夸语境,实则并未如此之多,而是借助浮夸语境描述自身壮志难酬的苦闷,而后面乐不雅观期待君主圣明却也是对现实中无法报国反而连遭贬谪的反衬。又如《满庭芳》中"百年里,浑身是醉,五万六千场"的词句,苏轼说自己生平只知醉酒,醉达五万多场,浑浑噩噩度过余生,实则是浮夸陈述,当然并非真欲此般烂醉,而是在使自身显得无知可笑之时凸显匆匆使自身醉酒而非积极做官的反讽精神。
我们非常熟习的那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便是低调陈述型反讽。这首词是苏轼的《定风波》,写于作者被贬黄州第三年感雨之时。说生平有一件遮雨蓑衣足己,显然使自身处于低位而使听者知其重,亦从侧面反响了自身虽有报国激情亲切,却终难实现。
苏轼的为官之路也十分坎坷
三、反讽手腕的艺术代价1、对付创作者的代价
(1)开拓创作思路
对付反讽者或反讽作家来说,反讽本就不断传承的否定及多义成分可以使反讽作家避免单一视域的涌现,进而增强其思想的多义性、繁芜性,开拓其精神天下。单一视域的直接涌现虽易使作品及作家本人的意识内容较为大略地被读者所接管、理解,但如果作家长期利用单一视域,易使自身情绪不受任何阻挡而直接宣泄下来,随意马虎造成主体意识僵化,难以达到文学创新的效果。
因此,反讽可以使得反讽作家的思想既有表层措辞根本又有思想深度,可以使得审美主体感情的宣泄具有弯曲激荡之美。平铺直叙的措辞固然浅近易懂,但是就如河流一样平常,笔直顺畅的小河常日没有太大波澜,但是拥有弯道的河流却更加澎湃湍急,给人以触目惊心之感。反讽就像河流中的弯道,看似阻碍了作家流畅的创作思路,实际却起到加速作家情绪宣泄的浸染。
婉约派代表词人李清照
(2)提升创作水平
反讽可以匆匆使创作者在创作中不断挖掘自身的反讽意识,从而加强、凝炼其审美思维,进而开拓审美主体的精神天下。反讽的涌现紧张是通过语境对陈述语句进行压迫及扭曲,即语境施加语句以压力,而如何设置奥妙的语境是创作者使反讽成功凸显浸染的条件,因而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要时候保持精神的转换与集中,不断通过词语、词调的变革与语境一直保持着一种或强或弱的对抗关系。因此反讽语句的涌现、高潮直至结束是一个精心加工的过程。
(3)凸显创作风格
在风格层上,反讽使得文本既有艰深晦涩的冷峻风格,又有流于戏谑的轻快风格。反讽的利用多是出于讽刺的须要,因而作者有时多利用批驳之词,凸显严厉不易之风格。而反讽的利用有时又让人忍俊不禁,形成轻松、笑剧意境。如南宋墨客赵汝鐩《耕织叹》"我身不暖暖他人,终日茅檐愁冻去世"就营造一种风趣可笑的场景,即自身衣单却为他人添衣,但是又恐怖寒冷,进而来反讽耕者不得食、织者不得衣的封建制度。
反讽手腕的浸染还表现为反讽的利用能够凸显作家的写作风格。如柳永词中多采取浮夸陈述型反讽,就凸显了他放荡不羁、敢于直言的文风特色。而晏殊词中的反讽则以人生深刻感悟、哲理为主,多采取悖论措辞论性反讽,抒怀亦较为平缓,就彰显了他婉丽平和的写作特色。又如苏轼词中的反讽始终穿插乐不雅观的旷达精神就构建了苏词反讽的最大特色,彰显其豪放不羁的写作特色,可见通过对诸家词中的反讽剖析更易看出其各自的写作风格。
晏殊的词中也利用了反讽手腕
2、对付读者的意义
(1)增强读者体验
反讽的利用可以增强读者的审美体验,进而拓展审美主体的精神天下。缘于作家反讽的须要,他们或借古讽今,或针砭现实,总是合营反讽的行为大声疾呼。如北宋词人柳永于《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中写道"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对现实的不满就以激愤的反讽句进行情绪抒发。
艺术作品随着创作者的情绪流动进行抒怀、议论,同样反讽的利用使读者与作者在完成情绪宣泄之际,又使得情绪在反讽锋芒中完成主题性的流动深化。双向建构性指的是创作审美主体与艺术作品、艺术作品与读者审美主体的两层双向建构。反讽的利用使得双向建构更具动态性、互动性,由于读者在反讽中进行了更具深度的思想熏陶,作者亦在反讽的帮助下得以进行更加锐利的反讽创作,因而不管是读者还是作家都在反讽的利用中加深、加强了审美体验,从而丰富了审美主体的精神天下。
南宋的豪放派代表——辛弃疾
(2)丰富认识评价
在认识评价层面上,反讽的利用使得文本认识与评价更趋于多样性,已成为后人评价的焦点,同样丰富了其认识评价层面。如柳永词的雅俗问题一贯是后世学人辩论之焦点,诸家对柳永词的认识评价也不尽相同,而个中造成这种文学征象的缘故原由之一便是其词中的反讽利用。
柳永既有"明代暂遗贤,如何向?"等反讽当目前廷不识贤人,且唾弃功名利禄之词,又有以反讽口吻写成的"且恁偎红倚翠,风骚事,平生畅","好景良天,尊前歌笑"等浮艳之词,来表达难入仕途的苦闷情愫,因而反讽使得柳永词呈现出多义性,进而使读者对文本衍生出多种阐释与评价。
乐不雅观豁达的苏轼
结语:纵不雅观全体宋词反讽的发展,反讽手腕与宋词词体本身、宋朝社会现实包括政治、经济、封建系统编制等多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宋词词坛上始终交织着婉约与豪放两种词风,因而反讽在两种词中的表现与浸染办法也多有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婉约反讽之美与豪放反讽之美相互交织、相继呈现,共同构成宋词中的反讽美感。反讽审美态度的涌现使作者对所指向的客不雅观事物产生独具反讽成分的代价评价标准,因而反讽与宋词的发展紧密相连,不仅增强了宋词词体、内容的多样性,而且丰富了宋词审美与主体评价的可能性。总而言之,反讽在宋词中的利用不仅丰富了词人的主不雅观天下,还加强了其所写词作特有的审美特性。
参考文献:
1、《柳永词新释辑评》
2、《苏轼词集》
3、《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