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鼓谤木
直诉制度适用的案件历代法律都是禁止越诉的,但有一种例外,即如果是重大冤案,或情形紧急的案件,则可以直诉。
汉朝以前,关于直诉案件的受理情形无明确记载。根据有关史料可以看出,西周时只假如百姓有冤屈而不能申者,都可以通过"路鼓"和"肺石"哀求最高统治者进行审理。从唐朝开始,关于直诉必须为重大冤案的法律规定逐渐完善。在唐代贞元十四年,唐德宗恩准奏请,对付官员失落职、由于婚姻而发生争讼以及追理财物等案件,必须按照程序先由本司审理裁决,然后再到省司直至三司进行理断,如果三司不予受理,这时才可以"投巨状"。
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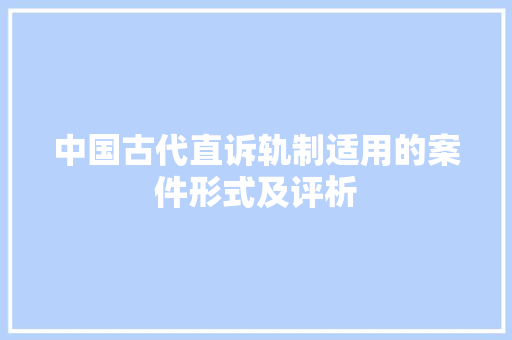
在封建社会,杀人等的刑事案件属于重大的案件。根据元朝的法律规定,"为人杀其父母兄弟夫妇,冤无所诉",可以越诉直诉,但是"以细事冒昧者论如法"。明朝同样规定有关户婚田土之轇轕不属于直诉案件。清朝的法律规定,只有涉及军国重务,有关大贪大恶,滥用权力的案件以及冤情重大的案件才能越级直诉。但在适用实践中,也有因民间琐事而直诉的,如"宋代牟晖击鼓案"记载牟晖因家奴丢失一头母猪,便击鼓直诉。可看出,原则上直诉案件该当是案情重大的,但在专制统治中,为表示德政、爱民,对一些不符合直诉条件的,在某些情形下统治者也受理。
直诉制度运用的形式邀车驾
邀车驾,据有关资料显示,"邀车驾"在汉朝就已经存在,《后汉书》中记载杨政邀车驾为其老师鸣冤。南北朝期间,邀车驾仍旧是百姓直接向最高统治者鸣冤的主要形式。在唐朝,邀车驾成为正式的法律制度。根据唐朝法律规定,凡是案情重大而又不能伸冤者,可以在天子出巡时,在天子车驾通畅处,跪伏路旁,申说冤情要求天子为其做主。《唐律疏议》规定,"在路邀驾申说有不实者,杖八十",同时规定"主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又规定邀车驾申说者,"自毁伤者,杖一百。虽得实,而自毁伤者,答五十。"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唐朝的邀车驾制度已经发展等比较完备,在规定当事人可以直诉的同时,还对不实申说和以自残身体的办法进行申说的行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和详细的惩罚方法。
挝登闻鼓
挝登闻鼓,宋朝继续前代的登闻鼓制度,并且设置了专门卖力登闻鼓的机构。宋太宗改设"登闻院","置鼓于禁门外"。"挝登闻鼓"是通过直诉启动最高法律权,对付平反冤狱,实现公正、公道具有主要的浸染。宋真宗规定诉讼先经由鼓院、检院,"不受"且"判状付之","许邀车驾"。宋朝期间的"挝登闻鼓"制度通过一系列改革己经规定得很完善了。
"立肺石",唐朝对起源于西周期间的肺石制度进行了继续。《唐六典》规定,孤寡老幼不能陈述自己冤情的,可以站在肺石上,就会有专门的官吏向其讯问案情。可见,唐朝期间,肺石制度同样属于直诉的主要形式。但根据《唐六典》的记载,该制度只适用于"载独老幼,不能自申者",也便是说,"肺石"制度的适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定,是对其他直诉形式的主要补充。
"上表",在汉朝上表制度的根本上,唐朝的上表制度更为完善。唐朝初期卖力受理上表投诉的是中书省和门下省。贞不雅观元年"救中书令侍中朝堂受讼辞,有陈事者悉上封"。《唐六典·刑部》规定"经三司申报又不伏者,上表。"唐朝的上表制度较汉朝明显完善,不仅规定了上表的主体为"天下冤滞未申及官吏刻害者",而且规定了上表的受理机关和受案范围,这较汉朝的规定明显更加详细,可操作性更强。
对直诉制度的评析直诉制度作为我国古代一项理冤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起到了非常主要的影响浸染,其积极的影响紧张有:首先,在掩护法律公道方面。古代诉讼制度规定了严格的审级限定,要逐级上诉,同时,也设有直诉制度,给有冤情的人供应了其余一种伸冤的合法路子,增加了人们通过合法路子得到公道的希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逐级上诉过程中可能涌现的官官相护的环境。一旦天子亲自参与了直诉案件的审判,一样平常都能够得到公道的裁决。一个案件得到公道裁决,对其他类似案件的裁判也有示范效应,其他案件当事人一样平常也能因此获益,这对实现法律公道有着重要的保障浸染。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开封有一女子被无赖骗婚后卷财逃逸,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丈夫亡命的女子在六年往后才可以出嫁。该女子"迫于饥寒诣登闻鼓上诉",宋真宗特下诏书曰"不逞之民娶妻给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天子的诏令相称于法律,因此直诉案件的审判结果能产生更多影响,很多相同命运的人都可因此获益。
案件审理
其次,在缓和社会抵牾方面。封建专制时期,社会抵牾尖锐,由于冤情不能申说而怨恨社会的大有人在。封建朝廷为了缓和社会抵牾,掩护其统治就会用尽各种办法。直诉制度正是一项能够起到缓和抵牾的制度。直诉制度的存在,使得那些有冤情的人有了一个可以使冤情平反的路子,至少是给了他们得到公道的希望,因而能够抚平一部分的反抗感情,有利于缓和社会抵牾,掩护个中间集权的专制统治。
再次,在理冤制度和诉讼制度的完善方面,直诉制度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浸染。直诉制度的存在,使得各朝代的理冤制度和诉讼制度设置更加全面,为人们申说冤情供应了制度保障。
末了,直诉案件会直接或者间接反响社会秩序的稳定情形,从而反馈给主持审理统治者大量的社会信息。一件直诉案件每每会牵扯到吏治的好坏,可以对法律官吏进行监督,从而给法律活动一定的约束,对普通百姓实施法律救援。虽然在法律实践中,通过直诉制度处理的案件为数不多,但是每每影响很深。总之,中国古代直诉制度的积极浸染,就天子而言,其存在增强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成为其获取地方信息,鞭策地方官员的主要手段。对普通的百姓而言,是其寻求正义的末了机会。虽然直诉的过程弯曲困难,却也给了绝望中的申冤者以希望。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其意义已不再是有多少冤案得以平反,而在于其作为追求正义的象征符号所蕴含的意义。
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直诉制度也不例外。其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古代社会,有冤情的人很多,由于交通不便,直诉用度很弘大,抱屈枉的人家很多都不能承受这个包袱,直诉是一种奢望。天子的精力有限,能够直接申报于天子的只是个中很小一部分。"天下狱二千所,其冤去世者多少相覆"。在大量的冤狱当中,真正能够直诉于天子并得到公道裁决的极少。此外,唐朝以前直诉者为了表达自己坚持诉讼的决心、表明自己确有冤屈,会选择自残的办法,如蔫耳、赘面、钉手等等,这严重影响了直诉制度设立的本意。唐宋往后直至清朝,随着历代法律的严厉禁止,直诉中自毁伤的现像才日渐减少。
其次,从审判方面看,直诉是否受理及能否得到及时处理,很多情形下与天子自身的本色、直诉案件的多少、处理直诉案件效率的高低等也有很大关系。如清政府对直诉干系政策和处理办法进行过一系列的改进和完善,但仍旧奏效甚微。一件直诉案件少则两三年,多则十几年才能审结,直诉当事人冒着倾家荡产乃至家破人亡的危险,而结果以"申说不实"、"捏词具控"、"越诉"者居多。到了光绪年间,则"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的记载就极为常见了。这样使得本来象征着公正正义的直诉制度实际上成为了一场人为的灾害。
再次,由于中国古代一向的厌诉、止讼思想的存在,各朝代法律中都有很多关于直诉的限定性规定,有些朝代为了限定越诉,规定不仅直诉案件内容涉虚处以刑罚,案情真实亦会处以越诉之罪。末了,到了清朝中后期,"细故混争"且涌现了来自于刑名幕吏、地方痞徒等的所谓讼棍,他们或经办词讼,或指导并帮助他人进京诬告等,在吏治腐败、审案效率低下的根本上,日益增多的直诉案件,使适合局疲于应对,也就使得直诉制度局限性越来越大。
结语:直诉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非常主要的理冤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理冤制度和诉讼制度的完善、法律公道的掩护、社会抵牾的缓和等各方面都起到了主要的积极浸染。虽然直诉制度设置并没有明显消减古代冤案,但在当时社会的法律环境中这一制度仍旧是积极之处更多。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这一制度对社会产生的某些方面的影响至今仍旧存在。我们该当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看待这一制度,切不可只看到制度的上风而不切实际的认为某一制度也应在现今社会中运用。
参考文献
1. 张金鉴:《中国法制史概要》
2.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律制度史》
3. 周密:《宋代刑法史》
4. 何勤华主编:《法律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