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山中有山山外有山的大别山里,混迹于草木昆虫奔兽流水之间,日与日的变革极其细微,岁月温吞光阴绵绵,又兼皮已厚肉已糙,我常常忘却人间易老。前夜读唐人《化度寺碑》,见“泡电同奔”四字,心中一凛。比少年时初见《金刚经》中“统统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不雅观”,比弱冠时初听苏子说“人间如寄,一樽还酹江月”,更加有所触动。但是一夜春秋大梦之后,心间那一点惊竦消逝得无影无踪,日子依旧貌似轰轰然实则寂寂然地向前,我也早已习气现世安稳。生理学有选择性影象一说,甚有道理,人的潜意识里的确有一道防御墙,自动遮蔽掉一些不愿意记起的事物。想起旧时乡间的茅厕,门口挂着的那一条破麻袋。
月光与水流泄于石上,小虫嘶语于草叶中,尘世的灯光近在一里之遥,又远在天边。隔,疏离,安静,天地有大美而虫言之。夜色迷离而美好,仿佛是一件隐身衣,一身铜铠甲。如果我乐意,可以脱得一丝不挂,到溪里拍浮,可以在青草河堤上像原始人一样披头散发狂野地舞蹈。也可以想象自己变成了一只虫子,豆丹、椿象、七星瓢虫或者金铃子,在草丛中蛰伏、嘶鸣、蹦跶、餐风饮露,与另一只雌虫子肆无忌惮地交尾。想起来真叫人灰心:人的肉身太重,人间的规矩又太多,人无论如何也做不了自由清闲的虫子,勉强算虫子,也是科幻片中那类胆怯血腥的害人虫。
有两三年我耽于虫子,夏秋两季放工后,常常在单位后面的山谷中静坐,或者蹑手蹑脚地闲走,只为了听满山满谷的虫鸣。那座山也叫花果山,虽然既无花也无果,但老松蔚茂茅草披离,山谷中藏着万千只虫子,自下午至第二天清晨一贯弹唱不休,有时独奏,东隅一声,西隅一声,嘀嘀咕咕;有时对唱情歌,雄一言,雌一语,如《上邪》之誓;有时多声部交响,疑是在大剧院的音乐厅里听门德尔松。我尤其爱听金铃子,滴呤呤,滴呤呤,倏然破空而来,干净清越一如古谣曲,如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如万串风铃迎风脆生生地响。
前些天与三五人小聚,席间听人说,他特殊讨厌听到蝉叫,由于太吵。真是蠢物。一只蝉便是一个哲学家。它住在高高的树上,一幅天下云烟尽收眼底、万千机变了然于胸的样子,很是有些哲学的意味。沉默时,它纹丝不动,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唱歌时,它左一个“知了”右一个“知了”,仿佛世间事它无所不知。就连遭遇捕捉时,它撒一泡尿就走的从容姿态,也很是高蹈,近似兵法中的“走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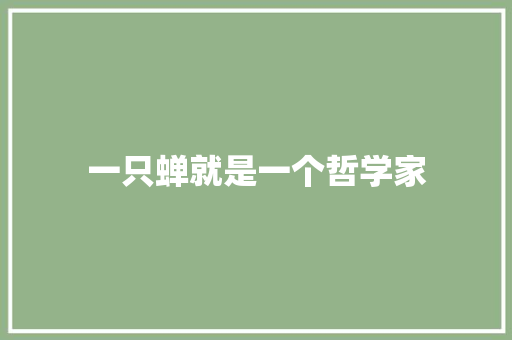
忽然念起王祥夫师长西席的工笔草虫。王师是小说大匠,也是画坛高手,性年夜方,酒量与度量并洪,酒后面色潮红斗志昂扬,妙语似珠穿。我在笔会中见过两次,敬其文章与画艺,尤其倾慕其风采和为人。仲夏时同游九华,在莲花佛国下的青阳,酒兵之间,他和我说,他认识的姓储的作家,一个是江苏的储福金,一个是安徽的储劲松。我说,还有一个唐代的储光羲。王师大乐,耳语云:酒后别走,有笔会,我给你写字。
果真有。王师赠我“听松”二字,逸笔草草。仍旧不知足。其笔下的枇杷、田鸡、菖蒲、莲藕、竹笋、蘑菇、草虫、小鸟、冻秋梨,点染之间纤毫毕现,得风致,得神韵,得买卖,得自然,我神往之久矣。师无奈,又耳语云:酒后字画都是狗屁。笑罢仍为我画一鱼,游弋纸上,骨骼历历,题名“珊瑚堂”。
昨日在微信上见王师画枇杷小虫,题曰:买画者对予说,藤黄不贵哦,不像洋红那样贵,就多多画几个枇杷果给我哦。我说是的是的,藤黄不贵。便欣然命笔大画枇杷,并奉送小蜜蜂一只。一时主客皆大欢畅。
王师食荤茹素,言谈亦荤亦素。荤素里有风情,有风概,有风月。以为他是草虫幻化,一举足一落笔,就到了宋元。
还是以为他欠我一只虫子。
栏目主编:孔令君 笔墨编辑:陈抒怡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