蒹 葭
诗经·国风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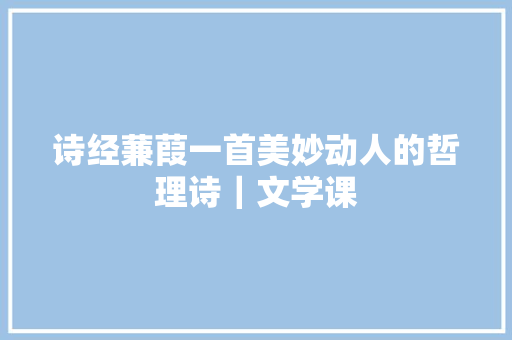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心。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中记载:乾隆年间,会稽胡西垞咏《蓼花》诗有句云:“何草不黄秋往后;伊人宛在水之湄。”上联引《诗经·小雅》,以百草枯黄喻人生干瘪,实写征夫行役之苦;下联虚写秋水伊人,通过《诗经·蒹葭》中“宛在”二字,渲染凄清景象、痴迷心象、模糊意象,营造一种若隐若现、若即若离、若有若无的朦胧意境。
同人生一样,诗文也有境与遇之分。《蒹葭》写的是境,而不是遇。“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佛学经典语)这里所说的境,或谓意境,指的是墨客(主人公?)的意识中的景象与情境。境生于象,又超乎象;而意则是情与理的统一。在《蒹葭》之类抒怀性作品中,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一种情与景汇、意与象通、情景交融、相互感应,生动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
《蒹葭》写的是实人实景,却又朦胧缥缈、扑朔迷离,既合乎自然,又邻于空想,可说是造境与写境、空想与实际、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范本。“意境空旷,寄托元淡。秦川咫尺,宛然有三山云气,竹影仙风。故此诗在《国风》为第一篇缥缈笔墨,宜以恍惚迷离读之。”(晚清·陈继揆语)
说到缥缈,首先会想到本诗的主旨。历来对此,歧见纷呈,莫衷一是,就连宋代的大学问家朱熹都说:“不知其何所指也”。今人多主“追慕意中人”之说;但过去有的说是为“朋友相念而作”,有的说是访贤不遇诗,有人解读为假托思美怀人、寄寓空想之不能实现,有的说是隐士“明志之作”,旧说还有:“《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
诗中的主人公,飘忽的行踪、痴迷的心境、离奇的幻觉,忽而“溯洄”,忽而“溯游”, 往来来往辗转,闪烁不定,同样令人生发出虚幻莫测的觉得。而那个只在意念中、始终不露面的“伊人”,更是恍兮惚兮,除了“在水一方”,其他任何情形,诸如性别、年事、身份、地位、外面、生理、情绪、癖好等等,统统略去。彼何人斯?是美女?是靓男?是恋人 ?是石友?是贤臣?是君子?是隐士?是遗民?谁也弄不清楚。
诚然,“伊人宛在水之湄”,既不邈远,也不神秘,不像《庄子》笔下的“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高踞于渺茫、虚幻的“藐姑射之山”。绝妙之处在于,墨客“着手成春”,经由一番随意的“点化”,这现实中的普通人物、常见情景,便升华为艺术中的一种意象、一个范式、一重境界。无形无影、无迹无踪的“伊人”,成为世间万千客体形象的一个空想的化身;而“在水一方”,则幻化为一处意蕴丰盈的供人想象、耐人咀嚼、引人遐思的艺术空间,只要一提起、一想到它,便会感到无限温馨而神驰意往。
这种言近旨远、超乎象外、能指大于所指的艺术征象,充分地表示了《蒹葭》的又一至美特色——与朦胧之美紧干系联的蕴藉之美。
一样平常认为,蕴藉该当包括如下意蕴:含而不露,耐人寻味,予人以思考的余地;蕴蓄深厚,却不露形迹,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骚”;以简驭繁,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如果使之具象化,不妨借用《沧浪诗话》中的“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概之。对照《蒹葭》一诗,该当说是般般俱在,丝丝入扣——
诗中并未描写主人公思慕意中人的生理活动,也没有调遣“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之类的用语,只写他“溯洄”、“溯游”的行动,略过了直接的意向表达,但是,那种如痴如醉的苦苦追求情态,却隐约跳荡于字里行间。
依赖于蕴藉的功力,使“伊人”及“在水一方”两种意象,引人思慕无穷,永怀遐想。清代画家戴熙有“画令人惊,不若令人喜;令人喜,不若令人思”之说,道理在于,惊、喜都是感情外溢,有时而尽的,而思则是此意绵绵,可望持久。
“伊人”的归宿,更是蕴藉蕴藉,有余不尽,只以“宛在”二字了之——实际是“了犹未了”,留下一串可以玩味于无穷的悬念,付诸余生梦想。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指出:“艺术的显现通过它本身而指引到它本身之外。”这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讲求,就上升为哲理性了。
钱锺书师长西席在《管锥编》中最先指出,《蒹葭》所表示的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企慕之情境”。它“以‘在水一方’寓慕悦之情,示神往之境”;亦即海涅所创造的“取象于隔深渊而睹奇卉,闻远喷鼻香,爱不能即”的浪漫主义的美学情境。
就此,当代学者陈子谦在《钱学论》中作了阐释:“企慕情境,便是这一样心境:它表现所渴望所追求的工具在远方,在对岸,可以眼望心至,却不可以手触身接,是永久可以神往,但不能到达的境界”;“在我国,最早揭示这一境界的是《诗•蒹葭》”,“‘在水一方’,即是一种茫茫苍苍的飘缈之感,寻寻觅觅的神往之情……‘从之’而不能得之,‘望之’而不能近之,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犹如水中不雅观月,镜里看花,可望不可求”。
《蒹葭》中的企慕情境,含蕴着这样一些生理特色——
其一,诗中所呈现的是向而不能往、望而不能即的企盼与倾慕之情的结念落想;外化为行动,便是一个“望”字。举头张望,举目眺望,深情瞩望,衷心想望,都表示着一种寄托与期待;如果不能实现,则会感到失落望,情怀怅惘。正如唐·李峤《楚望赋》中所言:“故夫望之为体也,使人惨凄伊郁,惆怅不平,兴发思考,惊荡心灵。其始也,惘若有求而不致也,怅乎若有待而不至也”。
其二,明明近在面前,却因河水阻隔而形成了远在天边之感的间隔怅惘。瑞士生理学家布洛有“生理间隔”一说:“美感的产生缘于保持一定的间隔”。一旦间隔拉开,悬想之境遂生。《蒹葭》一诗正是由于主体与客体之间保持着难以超出,却又适度的空间间隔与生理间隔,从而产生了最佳的审美效果。
其三,愈是不能实现,便愈是神往,对方形象在自己的心里便愈是美好,因而产生更加的期盼。正所谓:“物之更好者輒在不可到处,可覩也,远不可致也”;“跑了的鱼,是大的”;“吃不到的葡萄,会想象它格外地甜”。还有,东坡居士的诗句:“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清·陈启源所言:“夫说(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悦)益至”。这些,都可视为对付企慕情境的恰切阐明。
作为一种心灵体验或者人生履历,与这种企慕情境符合合的,是有待而不至、有期而不来的等待心境。宋人陈师道诗云:“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次开?”可人之客,期而不来,其伫望之殷、怀思之切,可以想见。而世路无常,人生多故,离多聚少,遇合难期,主不雅观与客不雅观、期望和现实之间呈现背反,又是多发与常见的。
这种期待之未能实现和欲望的无法达成所带来的忧思苦绪,无疑都带有悲剧意识。若是遭逢了诗仙李白,就会悲吟:“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当代学者石鹏飞认为,不圆满的人生或许才是最具哲学意蕴的人生。人生一旦梦想成真,既看得见,又摸得着,那文明还有什么提高可言呢?最好的人生状态该当是让你想得到,让你看得见,却让你摸不着。于是,你必须有一种向上蹦一蹦或者向前跑一跑的意识,哪怕终极都得不到,而过程却早已彰显了人生的意义和代价。以是,《蒹葭》那寻寻觅觅之中若隐若现的目标,才是人类不断向前的动力,才有可能让我们像屈原那样发出“天问”,才有可能立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高下而求索”的宏图远志。
是的,《蒹葭》中的望而不见,正是表现为一种动力,一种张力。李峤《楚望赋》中还有下面两句:“故望之动听深矣,而人之激情至矣”。这个“动听深矣”、“激情至矣”,正是动力与张力的详细表示。从《蒹葭》的深邃寓意中,我们可以悟解到,人生对付美的追求与探索,每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人们正是在这一绵绵无尽的追索过程中,饱享着绵绵无尽的心灵愉悦与精神知足。
看得出来,《蒹葭》中的等待心境所展现的,是一种充满期待与渴求的积极情愫。虽然终极仍是望而未即,但总还贯穿着一种温馨的神往、愉悦的怀思——“虽不能至,心神往之”;“中央藏之,无日忘之”。并不像西方后当代主义的荒诞戏剧《等待戈多》那样,喻示人生乃是一场无尽无望的等待,所表达的也并非天下荒诞、人生痛楚的存在主义思想和空虚绝望的精神状态。
《蒹葭》中所企慕、追求、等待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诗中悬置着一种意象,供普天下人执着地追寻。我们不妨把“伊人”看作是一种美好事物的象征,比如,深埋心底的一番刻骨铭心的爱恋之情,一贯苦苦追求却无法实现的美好欲望,一场甜蜜无比却瞬息消散的梦境,一方终生企慕但遥不可及的彼岸,一段代表着代价和意义的完美的过程,乃至是一座灯塔,一束星光,一种崇奉,一个空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蒹葭》是一首美妙动人的哲理诗。
本文选自《诗外文章》,公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更多文学课 点击下方标题即可阅读
扫上方二维码,即为购书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