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清,袁枚诗中写到:”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牧童骑着黄牛,头戴笠帽,手握柳条,横笛斜挎,歌声阵阵,飘荡于绿林,飘向绿野。听见了蝉鸣,意欲捕之,歌声嘎然而止,闭口立于原地,不敢发出一点声响。一个活泼可爱的牧童活灵巧现。
袁枚的牧童,无拘无束,十分逍遥,自由清闲,彷佛是天外飞来的小仙。比较之下,我这个牧童,可就短缺了袁枚笔下描述的洋洋得意,天真天真,高枕而卧的少年形象。
回顾童年,心里面,还多少有点儿酸酸的,甜甜的,略带苦涩的觉得。那年月,常常过着不是缺吃少穿,便是疾病缠身,无钱医治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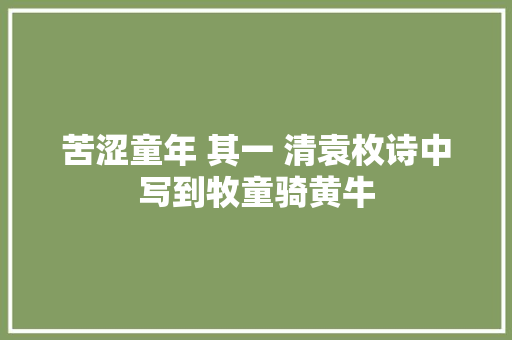
我们家兄弟姐妹多,挣工分的人少,是有名的缺粮户。常遭生产队长、余粮户们的白眼和不耐烦。记得那年,我八岁。本来是入学的年事,但为了多挣工分,不得不先不入学,先给生产队放牛。放一头牛,一天可以记五分(整劳力每天每人10分)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放的牛,一头很俊秀的牛,水白色,骨架硕大,能生很俊秀的牛犊。那个年代,牛是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主要的生产力。每年生一个牛犊,那可是生产队的大元勋,大宝贝。这样的宝贝,要找专人放养。我正是应了这样的天时,才当上放牛娃的。
缺少营养,我的个子还沒有牛头高,一个瘦字了得。粗麻杆一样的身子,细麻杆一样的四肢,瘦长的头颅,用骨瘦如柴去形容,一点儿都不为过。
放牛时的装扮,十分大略。尤其是夏季
景象酷热,头戴一顶破草帽或凉帽。光脚,穿个小裤衩,背心儿也沒得穿。一只手拉着长长的牛缰绳,一只手拿一杆小扎鞭。骑黄牛,牛是生产队的,舍不得骑的,牛是宝贝,金贵着呢!
每天放牛也会有危险。一天,午后。日头可毒了,火辣辣的,烤得大地快要冒烟了。赤足走在滚烫的小路上,牛随着我,逐步地朝河边走着。长长的缰绳在我的小手里牢牢的攥着,恐怕牛跑了似的。实在牛很听话,一步不离地跟在我后面,牛也怕我跑了。
毗河岸上放牛,长长的缰绳拖在地上,牛在烈日下,懶洋洋地吃着草,牛舌头
马蜂去世的去世了,飞歨的飞走了,可毒刺留在了我身上。坐在田埂上,一个一个
地抜毒刺。我多想大哭一场,眼泪在眼眶里转圈,又狠狠地把它们憋了回去,不能哭,我要做一个男子汉。
眼睛无助地、呆呆地望着,流淌热泪一样的河水,心里面祈祷着,赶紧终年夜吧:终年夜了,我也要每天挣10个工分。
到那时,再也不怕马蜂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