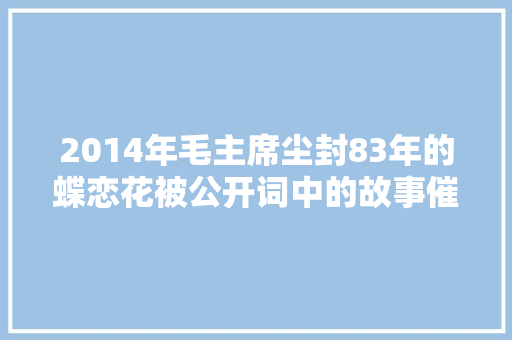长久以来,人们都以为这首词是毛主席为杨开慧写下的唯一一首悼亡词。不过奇怪的是,杨开慧义士早在1930年就罹难了,为何毛主席要到二十多年往后才为她填词作祭呢?
这个谜团直至2014年,官方媒体公布了毛主席在1930年12月年写下的另一首悼亡词,才得以解开。这首词是用羊毫字写在一张10行信笺纸上的,名为《蝶恋花·向板仓》。
一、《蝶恋花·向板仓》赏析《蝶恋花·向板仓》
霞光褪去何凄楚,万箭穿心不似这般苦。
奈何吾身百莫赎,待到地府愧谢汝。
无感霜风侵蚀骨,此生煎熬难与外人吐。
恸声悲歌催战鼓,更起刀枪向敌仇。
词作大意:
你那彩霞的光辉褪去之后,我的心情是多么地悲惨、苦楚啊。这种痛楚,就好比有一万支羽箭,同时射穿了我的心脏。
无奈我现在就算是去世过一百回,也没有办法赎回我的罪过了。只有等到将来,在地府之下相见的时候,再惭愧地向你赔礼。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管霜风雨雪若何侵袭、堕落着我的骨头,我都不会有什么觉得。但是我这生平中所受到的煎熬,除了你又该向谁去倾吐呢?
一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放声大哭。而我在这个时候能做的,只是在沙场上以悲愤的歌声催动着战鼓,又提起刀枪,不顾统统地冲向仇敌。
许多文学爱好者看过这首词后,都评价说它写得“情真意切”。事实上,这首词里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典故”,也没有任何华美的修辞手腕。
就连第一句里面的“霞”,也是出自杨开慧本身的字号。杨开慧字霞,毛主席字润之。他们二人从前书信往来时,常以“霞”、“润”互称。
这首悼亡词不以文文意境取胜,而胜在情真意切,字字泣血,让人读之泪如雨下。这种感想熏染大概没有经历过亲人亡故,生离去世别的人,很难解白透彻。
二、毛主席和杨开慧的爱情故事杨开慧较毛主席小八岁,但是她却是毛主席的初恋爱人。他少年时期在湖南上学时,杨昌济是他的老师。杨昌济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因此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了他很多帮助。
杨昌济带着家人到北大去事情往后,毛主席、蔡和森等几个同学也一起到北京发展。等到了北京,由于没有钱,大家一开始就直接住在杨家。
后来搬出去租了房,毛主席也时常与同学们一起到杨家拜访。一群学生还以杨家为据点搞了一个“新民学会”,大家一起畅谈时势政治,议论中国的未来。
杨昌济的小女儿杨开慧,那个时候也常常会搬着小板凳过来旁听,就这样不知不觉,毛主席和杨开慧二人就产生了感情。
实在按照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的说法,在到达北京之前,毛主席曾经和蔡和森等人有过约定,说要为了革命奇迹“终生不婚”。
但是后来毛主席碰着杨开慧,这个想法就彻底发生了转变。本来那一段在北京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很苦的,就像《蝶恋花·向板仓》里写的那样——“无感霜风侵蚀骨”。
当时青年毛主席齐心专心想干出一番大奇迹,再到韶山冲看望父母,但是父亲见到他长久没有事情,认为他在外“吊儿郎当”,为了逼迫他回到家中,竟然断了他的生活费。
后来毛主席去到北京时,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和八个同学合租了一间房,寒冬尾月大家睡在一个通铺上,所有人共用一件大衣。也便是说,谁出门就让谁穿。
后来有好些个朋友弄到了钱,终于也买了大衣,但是毛主席始终没有。当时他用饭也很成问题,常常是一天只吃一顿土豆、白菜,绝不吃肉。
再今后,毛主席的同学大多选择了去法国留学,不想去留学的人末了也回家乡去了,但是他仍旧坚持留在北京。
末了,通过杨昌济的帮助,毛主席才到北大当了个图书管理员。就这样,他的生活状况才逐步好了起来。
一九一九年的冬天,毛主席和杨开慧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他回顾起这段光阴时,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故都的美对付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
由于有了爱情的滋润津润,以是毛主席以为这个冬天也变得不再寒冷了,也有心情到北海去欣赏风景,看冰晶倒挂在梅花、杨树上的美妙奇不雅观。
后来在毛主席的诗词作品里,梅花与杨柳自然而然就成了杨开慧的化身。一九二〇年他和杨开慧结婚,一年后他因公离家外出。
由于思念杨开慧,毛主席写下了一首《西江月·枕上》,个中提到自己由于半夜惦记杨开慧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末了只能爬上屋顶去数星星,数着数着还堕泪了。
这首词真是把一个缠绵小儿女的情态写得活灵巧现,以至于三十多年后李淑一向毛主席索要这首词时,他不再美意思拿出来,于是又重写了那一首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毛主席和杨开慧二人的感情很好,由于他们都有共产主义的信念,并且志趣相投。青年时期的毛主席在湖南办报,提倡妇女革命。
同时,毛主席还写了不少文章鞭笞旧社会对女性的伤害,并歌颂敢于背叛礼教的女子。杨开慧性情十分刚烈,就敢公然剪短头发去女校上课,结果差点被学校开除。
在人生中不得意的光阴里,毛主席心头的千言万语找不到旁人陈说,他只能对杨开慧讲。可想而知杨开慧的存在,对他来说是多么田主要。
秋收叛逆之后,毛主席带着军队上了井冈山。一九二八年,他派人到杨开慧的老家板仓打听她和几个孩子的着落。
当时由于国民党“还乡团”打来,地方上的人为了保护杨开慧母子,假传她的去世讯。毛主席惊闻噩耗心如去世灰,但是当时他正身处于仇敌的包围之中,根本没有办法亲自前往实地调查。
一九三〇年,杨开慧被捕入狱,当年十一月国民党的媒体传出了她的去世讯。那时毛主席正在江西沙场上与仇敌浴血奋战,于是他就提笔写下了这首词。
结语记不清是托尔斯泰还是谁曾经说过,他为了写好小说,曾经在亲人去世的时候,暗中琢磨该用什么样的办法去描述自己那种感想熏染。但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每每无法做到这一点。
毛主席一贯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细腻的人,以是当他听到爱人去世讯的时候,除了悲痛欲绝之外,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思考、去琢磨,该当用什么样的修辞手腕去传达这种感情。
本来这种词作,毛主席大可以在创作往后,等到伤痛平复再来润色。但是从这首词的表现来看,我们现在看到的“终稿”,很可能便是它的“初稿”了。
毛主席平生创作的大部分诗词,都有过反复修正的经历,有一部分修正润色的过程乃至横跨数十年,从抗战期间一贯持续到了五、六十年代。
但是毛主席偏偏没有对这首悼亡词作过多的修正,恐怕便是由于这首词中的感情,已经真实地还原了他当年的感想熏染。
诗言志,词言情。情真意切才是词作难能名贵的地方,再在上面添油加醋,刻意地利用一些华美的修辞手腕,便是多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