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之以是成为诗词,是由于除了格律、句式、节奏等硬性的标准以外,诗词必须具有诗词的气质,这种气质是由诗词自身独特的措辞体系所决定的,这种措辞体系便是常日说的诗家语、词家语。
毫无疑问,诗词属于文学艺术的范畴,而且是更高雅、更高等的文学艺术,是文学中的文学,非普通文学、大众文学可比,普通大众文学的哀求只需语句畅通、言情叙事合理就行了,而诗词(尤其是格律诗)则是在有限的篇幅、字数以及平仄粘替等等规则之内以最少的词句表达出丰富的内涵、深远的意境、深刻的思想,并做到小中见大、浅中见深、微中显著,对笔墨编排、闪攒腾挪的功夫哀求极高,尤其须要有炼字炼意的能力,学会利用诗家语、词家语,便是诗词的高等属性使然。
诗词不同于散文、记叙文、解释文,也不是山歌、快板书、顺口溜,平铺直叙、面面俱到、普通易懂并不是诗词的要点,诗词更讲究的是含而不露,对付所要表达的情绪或景致,应以“不说穿”来传达“说不出”的情绪,至于如何做到含而不露,就须要每一个诗词爱好者平时多阅读古人作品、多揣摩、多练手,逐渐培养属于诗歌的语感了!
那么词家语呢?常说诗词难分家,因此词家语和诗家语之家也存在天然的“继续关系”。诗家语的语法可以用在词家语上。使词感变得峻峭挺立,但是反过来就弗成了。词家语用在诗中,就会让诗显得软媚。总体而言,词以言情见长,正适宜消化和领悟软媚的词句。
现在很多诗词爱好者都兴致勃勃地努力创作,一天三篇,一辰几吟,然后在朋友圈里、抖音上连篇累牍地揭橥,或者是古风诗词的模式,或者挂个律诗词牌什么的,俨然以里手自居,生手看来很唬人,但细读之下,大多干涩、不耐嚼、无美味余味,究其缘故原由,不是说说虚情假意、也不是没有思想内容,很多时候还是可以看出作者的构思和意象的选择是很存心的,但是为何写成作品往后就变味了呢?便是由于他们处理不好诗词表达时的语感!
乃至以为生造古风或者大口语,然后就好了!
实在说穿了,这种做法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积累不足、探索不努力却又梦想所谓的诗词才子浮名找借口罢了。而要想写出有诗味的作品,就不得不花心思节制精确的诗词措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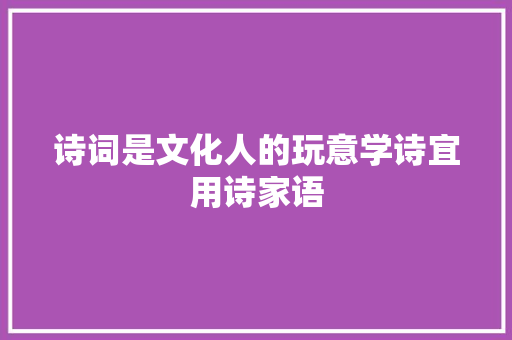
大家都笃信“文无定法”,但首先你得是文,其次必须有法,然后再说定不定的!
诗词既然是一种文体,就必须遵照一定的文法。诗家语和词家语便是诗词创作过程中必须把稳的一种措辞表达风格,比如温庭筠的“雁飞残月天”,意境何等凄零空冷,同样是表达大雁飞过夜空,如果不把稳诗词措辞的意趣性,直白地表示“大雁飞夜空/月空”,美感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以是美感是诗词措辞的第一关,首先考虑的应是如何落语,如何使诗具有美感。你可以通过虚实穿插,时空跳跃、回旋往来来往等各种手腕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但一定不能直写。
为什么?由于诗家语、词家语还要讲究意趣,意思解释白的同时还哀求有意见意义性,干巴巴地说完了,没有一点个性的气息展现在作品中,作品缺少灵动、回味的特点,读来味同嚼蜡,不雅观之如木乃伊无甚分别。比如刘禹锡的“如今直上银河去”,一个“直上”就把黄河苍凉雄伟的气势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果稍改一下“远上”,气势就会削弱很多,黄河再也不这天夜奔驰、令孔役夫感叹“逝者如此”的黄河了。
再者,诗家语和词家语最好要蕴藉,桃花不说桃花,要说落红。蕴藉有利于读者产生想象和寄托。比如苏东坡“梦随风万里,又还被、莺呼起”,把杨花拟人化,使描写的工具呈现立体的觉得,使人有庄周梦蝶之感,到底是在说花还是说人?这种虚实穿插之手腕,是诗词措辞的独特韵味所在。
末了,须要表明的一个不雅观点便是:诗词措辞并不一定具有交际性。我们知道措辞的最大浸染便是互换,但是诗词措辞作为文学措辞的一种,并不承担让所有人都看明白的义务。它该当属于少数人书面纸面互换的分外符号。诗词的措辞须要闪攒腾挪、蕴藉回旋、一唱三叹、不苟言笑,因此它的交际功能会有所退化,而文学的不雅观赏功能会大大提升。就像说妹子的脚,山野村落夫会唱“妹子小脚尖又尖,彷佛湖上一小船”,而在诗词的表达中则会说成“帘底纤纤月”。前者直白普通,一看就明白,后者则须要一定文学素养才能回过味来!
这也便是诗词措辞的文学性大于交际性的特色之一。同时也解释诗词实在只能是一种小众文化,而不是大多数人所能接管的。很多初学者乃至自诩入道良久的诗词作者,总以为普通易懂、贴近大众的才是好的,以是认为诗词就要写成口语,针言、形容词顺手拈来,拿了就上,于是才造成了套话一大堆、大而无当、词不达意、表达不真切的短板,成为不忍卒读的泛泛之作。既然要写,自然要脱开口头表达的窠臼,如果只是想让大众明白,那么写成散文、记叙文就好,何必用诗词的形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