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从前他抛弃官职,投奔临邛县,由于他听说临邛县的卓王孙有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儿叫卓文君。有一次他去卓家做客,用琴声表达了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鼓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兮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人去楼空毒我肠,何由交卸为鸳鸯?”
求爱之心溢于言表,其大胆和坦直,即便在本日看来仍旧让人含羞。不过,在帘后谛听的卓文君却为之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后一见钟情。卓文君当时是一位望门寡妇,丈夫在结婚之前即已去世去,根据儒家规范,她不能再嫁别的男人。
于是,当夜,卓文君整顿细软从家中逃了出来,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二人私奔了。这可能也是最早的私奔记录。
司马相如带着卓文君回到成都老家后,面对徒有四壁的贫寒家境,卓文君绝不介意。后来二人又返回临邛,开了家小酒馆,卓文君当垆卖酒,坚持家用。末了二人的爱情冲动了卓文君的父亲,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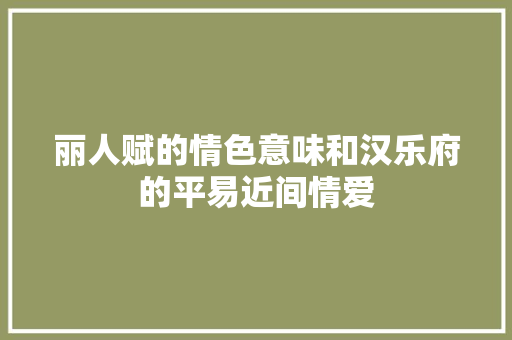
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来看,他是反对儒家教条的。从“赋”这种文体看来,司马相如承继了战国时期的楚人宋玉的风格。宋玉曾有一篇著名的《登徒子好色赋》,说的是:
楚国大夫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说宋玉的坏话,说宋玉漂亮,长于辞令,而且贪爱女色,委实不宜让他出入宫廷。楚王于是质问宋玉,宋玉说:边幅漂亮,是上天所生;长于辞令,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至于贪爱女色,则完备是登徒子的曲解。楚王不信宋玉不贪爱女色,宋玉于是说,天下的美女,没有谁比得上楚国女子,楚国美女,又没有谁能超过他家乡的,而他家乡最俏丽的姑娘是他的一位芳邻。这位姑娘——
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
但是这样一位女子,站在墙头看了宋玉三年,宋玉也没有动心。而登徒子呢,他的老婆蓬葆垢面,耳朵挛缩,嘴唇外翻且牙齿参差不齐,弯腰驼背,走路一瘸一拐,又患有疥疾和痔疮。这样一位丑陋的妇女,登徒子却与之频繁行房,并且生有五个孩子。那么究竟谁是好色之徒呢?
宋玉和登徒子的差异是:前者经受得住美的诱惑,而后者连丑女都难以抵挡。
插入宋玉,旨在解释司马相如所作的《美人赋》与前者一模一样。在《美人赋》中,美女不仅是登墙而窥了,而是赤裸裸的性诱惑——
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鉔薰喷鼻香,黼帐低垂。裀襦重陈,角枕横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
不仅露出了亵服和身体,还上前亲吻撩拨,在此环境下,激情是一触即发的。但司马相如的选择是:“气服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便是不为所动,且丢下这个诱人的美女,与之长辞了。
作为反对儒家教条和道德说辞的两篇文章,宋玉和司马相如都显得正气凛然。他们不是忽略美女的存在,而是强调自己真正的情操。在他们看来,儒家的可笑之处是嘴上说的那一套,经不起任何磨练,在诱惑面前,他们急速弃甲屈膝降服佩服。
不过,这两篇文章毕竟是政论性子的檄文。文章之下,二人的情欲还是真切的,乃至是可以触摸的。由于在描述中,我们分明已经窥见了宋玉和司马相如强烈的性意识,他们最少是正视人的性欲的。这些对女人的性感描述在后世成为正视情欲的典范作品。
由上所知,宫廷的淫乱和知识分子对性爱的正视,都是对儒家学说和《礼记》规范的反动。王朝国家对待性问题,在上层,一贯都是言行不一的分裂状况;在民间,却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性自由。这些自然和自由的性不雅观念,和《诗经》时期一样,仍旧保留在民间歌谣之中,在汉代乐府诗集中可谓俯仰皆是。
《月下吹箫图》,费丹旭绘。图中女子在月下神色落寞地吹着长萧,表达的便是闺怨之情。在《古诗十九首》中,大量诗篇描述着这种“闺怨”。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这实在是一首汉代期间关于女人装饰的诗歌,高髻、大眉和广袖。这是汉代美女的标准打扮。在《陌上桑》中,还对一位叫罗敷的劳动妇女的装饰有更为详细的铺陈描述,她的美不仅使少年容身,而且使“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后来来了一位使君,他调戏并困惑罗敷,后者通过对自己丈夫的虚构和想象谢绝了对方的企图。
在《古诗十九首》中,描述妇女的篇章很多。有“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性苦闷,这些怨妇们总是“忧闷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常常性失落眠和嗟叹。在平时的劳动中,她们“纤纤擢素手,札札弄心裁。终日不成章,泣涕泣如雨”。墨客们是用“闺怨”来记录这些民间女人情爱上的追求。
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源自汉代乐府。这个故事除了控诉等级制对男女情爱的伤害,紧张还是表达劳动者对性爱自由的追求。织女由于森严的宫廷制度,过着没有性爱的僧侣生活;牛郎由于贫穷,被剥夺了性爱的权利。他们的结合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然力量的使令。
儒家的规范和制度,终于在《孔雀东南飞》中酿成了悲剧。男女主人公被人为分离,先后自尽。不过,它的结局是魔幻主义式的光明:“两家求合葬,合葬西岳傍。东西植松柏,旁边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容身听,寡妇起彷徨。”这种魔幻主义加浪漫主义,在后来的《梁祝》故事中被再次重复,梁山伯和祝英台的魂灵化为翩翩蝴蝶而比翼双飞。
可以这么说,在汉代乐府中,在民间,性爱的美好并没有由于儒家学说和《礼记》规范而凋零,民众除了遵守,也有激烈的控诉和反抗,有时乃至是血腥的。此外,也正是远在庙堂之外,性意识仍旧可以说是鲜活的,是直接和自然的,一如村落野之夫和使君对罗敷表示出来的希望。大概正是民间的这种力量,才担保了人口的大面积繁衍和社会生产的进步,从而担保了汉代的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