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辛弃疾《清平乐》
辛弃疾也是到过江南的,而且那段时候,他没那么迫切,金戈铁马的激越,挑灯看剑的豪迈,在江南那水乡里也被旖旎了,险些消逝殆尽,剩下的只是惬意闲适。这彷佛是得了"吴音"的好处。"醉里吴音相媚好",吴音,且还是"媚"的,这风情,想想都让人醉。
01 吴音为诗词增长了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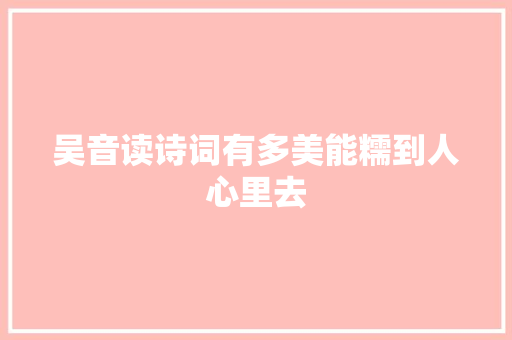
唐诗宋词中多"吴音"二字。现今懂日语的人,提起"吴音",多数便想起的这天语的读音。但日语这种音读,确是从中国"偷"去的,唐诗宋词的吴音,日本人未必懂。
诗词中"吴音"二字,实指"吴语"。在中国,语前带着地方,多数是说措辞。那么吴语是一种措辞了。就像我们说"这天津话说的不错",吴语也是一种话,说是江浙话,彷佛大家就都明白了。但既然称为"吴",我们熟习的有三国时的东吴,那这吴地便有讲求了。
三国里提起东吴,也称江东,也说江南,其地包括如今的上海、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福建北边一点,也算是江东。
实在地方不算大,但由于一江之隔的人基本都这样说话,影响力自然是大的。
南方人说话,有点"拐弯抹角",紧张是音调好听,不易听得清楚,但听起来"鸟语花香"。即便是吵架,也像是鸟鸣,快而细碎,悦耳动听,蛮是有趣。南方人发生抵牾,多以吴语吵架而少动手,大概也是由于说话好听。这种架,一吵半个小时,也不嫌烦,乃至吵一天,也没事,反正不动手,权当听南方相声。
吴语好听,紧张是由于保留了一些古汉语的用字用语,而且有平仄,古汉语的四声八调,非常整洁好听,吴语都大大的继续发扬了。
02.南北方言互异,对文学艺术影响非常大中国有个词叫"南腔北调"。
人分南北东西,天下各地都有。但方言分南北,只有中国有。
而且,不能换,南腔北调,你不能说是"南调北腔",就像你不能把南辕北辙说成"南辙北辕"一样。
彷佛确实南北有别。
有别在什么地方呢?比如措辞,为啥就南方是腔,北方是调呢?这很让人头疼,何况北方还有个地方戏叫"秦腔",又变成腔了。
想来是北方措辞唱起来,是腔,说话却是另一个调调。
但南北方的方言差异实在太大。
汉语有七大方言。
江浙话,便是吴音,是其一。
但还有湖南话。
江西话。客家话。广东话。闽南话(闽南闽北各不同)。
这都属于"南腔"。
北方话大体上不分这么细,虽然北方地方大的惊人,但实际上的北方话彼此大致都能听得明白,东北人说话,西北人能听懂,反之亦然。由于北方话基本没有浊塞音,腔基本一样,调子不同而已。
南方话就愁人了。
即便是吴语,温州跟杭州离得不远,都是吴语,但温州话跟杭州差了老远,彼此未必听得懂。乃至,即便是温州,各地的话,也未必相互全懂。
腔不一样,调不一样,就让人为难了。
北方人说吃,华北、西北、东北,无论哪里人,说吃听起来都是吃。无非是说的调门高低音调是非罢了。可是你去江南转一圈,从上海开始,到杭州,到诸暨,到温州,到福建,说什么的都有,七饭、夹饭、塞饭、噎饭、携饭,怎么听都不是"用饭"。
单是人称。
吴语里,她,叫伊。还叫"匆匆"、"其"。
你,吴语叫"侬",你侬我侬嘛。
遇见亲戚,爸爸的妈妈,北方都叫奶奶。
温州见到爸爸的妈妈,可不叫奶奶,叫"娘娘"。南昌叫"婆婆"。厦门叫"妈仔"。广州叫"阿嬷"。福州叫"依嬷"。
岳阳干脆把爸爸的妈妈叫爹——"细爹"。
长沙叫"娱驰"。
看看这南腔北调,爸爸的妈妈也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了。一个老段子说,八十年代的一个南方学校校长说:"教职工开会,家属也参加。"结果一个北方西席听成了"叫鸡公开会,家畜也参加。"苏州姑娘说:"我被他吓了一跳。"但她说出来你完备听不懂,由于她会说:"泥拨侄吓仔一跳。"
吴语也让人饿。去杭州,问这附近有餐馆么,杭州人说:"馍"。听着都饿,但实际上人家说的是"没有"。
03 北言铿锵,南语柔糯,朱唇一启,诗词便美到民气里去了但吴语便是好听,你听听那一首"外婆谣"。你读金庸《射雕英雄传》,知道这谣的词是"摇啊摇,要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这读起来就没啥意思,但用吴语唱出来,真是糯到民气里去了。
无怪白居易说"何以醒我酒,吴音吟一声"。听见吴音,他连酒都醒了,醒酒汤用不着。王昌龄听北方师父诵经估计昏昏欲睡,就爱听南方尼姑诵经,由于"朱唇皓齿能诵经,吴音唤字更分明"。刘长卿更过分,直接说"云房寂寂夜钟後,吴音清切令人听"。
这几位大概不足解风情,直通通的,便是听着好听,由于音调好听"唤字分明"或者"清切喜人"。
苏轼却是天生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竟然听出了娇软,听出了痴,听出了愁——"吴音娇软带儿痴,无限闲愁总未知"。
遇上杜牧这种人,吴音里有娇软糯人了,想想二十四桥明月夜,一位美男朱唇就箫,伴随着那糯糯的吴语歌吟,谁不像是在梦里?
听唱歌的,没有不爱听吴语唱歌的,所谓"爱渔舟荡雪,击楫起吴音"。赵孟頫在湖州,日子过得像神仙,就爱吴音的娇——"曲里吴音娇未改,障羞"。
为什么古人这么讴歌吴音,而不是我们如今说的这种普通话?
由于吴音保留了很多中原"雅言"。古音跟现今读音是有差异的,比如古汉语中,"者",也读"du",行者武松,放到上古,就读行者(du)武松。到现在,福州话也把猪叫du。由于这个偏旁的字,比如赌、堵、都、睹,都读du。只不过中古之后这种古音变了,这偏旁的字有一部分也读zhu,比如猪、诸、煮、著、褚等。
这种类似的,北方话都改过来了,但是吴语保留了很多。以是说吴音比较"高雅"一点,或者"古雅"一点,至少是古朴的。而且很多词汇比较书面化,北方说脸,人家说面。北方说眼,人家说目。北方说喝,人家说饮。锅在南方措辞里,也叫"鼎",一瓶酒,人家可以说"一樽酒"。
吴音还有一点,可以用袁宏道的一句诗来解释——"一瓶一笠一条簑,善掺吴音与楚歌"。
看,吴音,楚歌。
为什么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由于这两个是表亲关系。
湖南话是继续楚语的,两者属于嫡亲关系。
很多时候,吴语和楚语被算作一个东西,以是古诗词里多有吴楚并列,比如"吴楚东南坼"。当年楚国灭了吴越,统一了一段韶光,相互领悟是一定的。杭州人、上海人本日把"吃"叫"恰",湖南也叫"恰"。爸爸叫"爷"(念ya),都差不多。到隋唐,吴语跟楚语都是被算作一个东西的。乃至到了明朝,也是"才闻出夹吴音少,稍入中流楚调多"。
但中间变革也多,方言甚是繁芜,不必细说了。
但我们知道吴音清切动听,多听听,也是不妨的。听说上海姑娘很嗲,那不是上海姑娘有本事,是上海姑娘沾了吴音的光。有一个电影,一女子上海话里夹着英语,那真是又脆有嗲又有趣,嗲去世人不偿命。快去找吧。
但听吴音,建议喝点酒,微醉,效果最好,由于"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这彷佛是可以"白头偕老"的一种情调。至少,来个"相媚好",那也是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