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桃源与沅州
一只桃源小小船上只能装载一二客人。照例要个舵手,管理后梢,调动船只旁边。张挂风帆,松紧帆索,捕捉河面山谷中的微风。放缆拉船,量渡河面宽窄与河流水势,伸缩竹缆。其余还要个拦头工人,上滩下滩时看水认容口,失事条件示舵手躲避石头、恶浪与流,出事后点篙子须要准确,端庄。这种人还要有胆量,有力气,有履历。张帆落帆都得很敏捷的即时拉桅下绳索。走风船行如箭时,便蹲坐在船头上叫喝呼啸,嘲笑同行掉队的船只。自己船只掉队被人嘲骂时,还要回骂;人家唱歌也得用歌声作答。两船相碰说理时,不让别人占便宜。动手斗殴时,先把篙子抽出拿在手上。船只逼入急流乱石中,不问冬夏,都得敏捷而年夜胆的脱光衣裤,向急流中跑去,在水里尽肩背之力使船只离开险境。掌舵的因事件不能尽职,就从船顶爬过船尾去,作个临时舵手。船上若有小水手,还应事事照料小水手,指示小水手。更有一份不可推却的职务,便是在统统过失落上,应与掌舵的各据小船一头,相互辱宗骂祖,连续使船提高,小船除此两人以外,尚须要个小水手居于杂务地位,淘米,煮饭,切菜,洗碗,无事不作。行船时应荡桨就帮同荡桨,应点篙就帮同持篙。这种小水手大都在学习期间,应处处把稳,取得履历同本领。除了学习看水,看风,记石头,利用篙桨以外,也学习挨打挨骂。尽各种古怪稀奇字眼儿整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的保留在影象里,将来终年夜时再用它来辱骂旁人。上行无风吹,一个人还负了纤板,曳着一段竹缆,在荒凉河岸小路上拉船提高。小船停泊码头边时,又得规规矩矩守船。关于他们的经济情势,舵手多为船家长年雇工,均匀算来合八分到一角钱一天。拦头工有长年雇定的,人若年富力强多履历,报酬同掌舵的差不多。若只是短期包来回,上行均匀每天可得一毛或一毛五分钱,下行则尽责任吃白饭而已。至于小水手,学习期限看年事同本事来,有些人每天可得两分钱作零用,有些人在船上三年五载吃白饭。上滩时一个欠妥心,闪不知被自己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流中,泅水技能又不在行,在水中淹去世了,船主方面写得有字据,死活家长不能干涉干与。掌舵的把去世者剩余的一点衣服交给亲长解释白落水环境后,烧几百钱纸,手续便清楚了。
一只桃源小船,有了这样三个水手,再加上一个须要赶路,有耐心,不嫌孤独,能花个二十三十的搭客,这船便在一条清明透澈的沅水高下游移动起来了。在这条河里在这种小船上作搭客,最先见于记载的一人,应该是那疯疯癫癫的楚逐臣屈原。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就说道:“朝发汪渚兮,夕宿辰阳。”若果他那文章还值得称引,我们尚可以就“沅有芷兮澧有兰”与“乘上沅”这些话,估想他当年或许就坐了这种小船,溯流而上,到过出产喷鼻香草喷鼻香花的沅州。沅州上游不远有个白燕溪,小溪谷里成长芷草,到如今还随处可见。这种兰科植物生根在峭壁罅隙间,或蔓延到松树枝桠上,长叶飘拂,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花叶形体较建兰柔和,喷鼻香味较建兰淡远。游白燕溪的可坐小船去,船上人若伸手可及,多随意伸手摘花,顷刻就成一束。若崖石过高,还可以用竹篙将花打下,尽它堕入清溪洄流里,再用手去清溪里把花捞起。除了兰芷以外,还有不少喷鼻香草喷鼻香花,在溪边崖下繁殖。那种黛色无际的崖石,那种一丛丛清香眩目的奇葩,那种小小洄旋的溪流,合成一个如何不可言说迷民气目的圣境!
若没有这种地方,屈原便再疯一点,据我想来,他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俏丽。
什么人看了我这个记载,若憧憬于喷鼻香草喷鼻香花的沅州,居然从桃源包了小船,过沅州去,希望实地研究办理《楚辞》上几个草木问题。到了沅州南门城边,大概无意中会一眼瞥见城门上有一片触目玄色。因好奇想明白它,一时可无从向谁去讯问。他所见到的只是一片新的血迹,并非什么古迹。大约在清党前后,有个晃州姓唐的青年,北京农科大学毕业生,在沅州晃州两县,用党务特派员资格,率领了两万以上四乡农人和一些青年学生,肩持各种农具,上城请愿。守城兵先已得到主座命令,不许请愿群众进城。于是双方自然而然发生了冲突。一壁是旗帜,木棒,呼喊与愤怒,一壁是高高在上,一尊机关枪同十枝步枪。街道既那么窄,结果站在最前哨上的特派员同四十多个青年学生与农人,便全在城门边捐躯了。别的农人一看环境不对,抛下农具四散跑了。那个特派员的尸体,于是被兵士用刺刀钉在城门木板上示众三天,三天过后,便连同其他捐躯者,一齐抛入屈原所夸奖的清流里喂鱼吃了。几年来本地人在内战反复中被派捐拉夫,在搪塞差役中把日子混过去,大致把这件事也逐步的忘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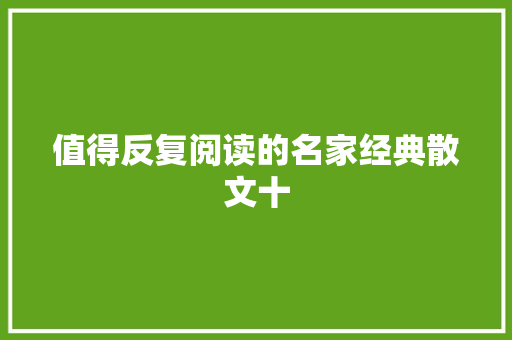
桃源小船载到沅州府,舵手把客人行李扛上岸,讨得酒钱回船时,这些水手必乘兴过南门外皮匠街走走。那里那边所同桃源的后江差不多,住下不少经营最古职业的人物,地方既非商埠,价钱可公道一些。花五角钱关一次门,上船时还可以得一包黄油油的上净烟丝,那是十年前的规矩。照目前百物昂贵环境想来,统统当然已不同了,出钱的花费大概得多一点,收钱的待客大概早已改用“俏丽牌”代替“上净丝”了。
或有人在皮匠街蓦然间遇见水手,对水手发问:“弄船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家里有的你让别人用,用别人的你还得费钱,这上算吗?”
那水手一定会拍着腰间麂皮抱兜,笑眯眯的回答说:“大爷,‘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钱不是我桃源人的钱,上算的。”
他回答的只是后半截,前半截却不必提。本人正在沅州,离桃源远过六七百里,桃源那一个他管不着。
便由于这点哲学,水手们的生活,比起“风雅人”来彷佛也洒脱多了。
若说话不犯忌讳,无人狐疑我“袒护无产阶级”,我还想说,他们的行为,比起那些读了些“子曰”,带了《五百家喷鼻香艳诗》去桃源寻幽访胜,过后江讨履历的“风雅人”来,也实在还道德的多。
钟敬文 西湖的雪景
从来评论辩论西湖之胜景的,大抵瞩目于春夏两季;而各地游客,也多于此时翩然来临。──秋季游人已渐少,入冬后,则更形疏落了。这当中自然有甚至其然的道理。春夏之间,气温和暖,湖上风物,合时佳胜,或“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或“浴晴鸥鹭争飞,拂袂荷风荐爽”,都是要教人眷眷不易忘情的。于此时节,往来湖上,沉醉于柔媚芳馨的情味中,谁说不应该呢?但是春花固可爱,秋月不是也要使人销魂么?四季的烟景不同,而真赏者各能得其佳趣;不过,这未易以论于一样平常人罢了。博识父师长西席曾见告过我们:“若能高朗其怀,旷达其意,超尘脱俗,别具天眼,揽景会心,便得真趣。”我们虽不长进,但对付先贤这种深于体验的话,也忍只当做全无关系的耳边风么?
自宋朝以来,平章西湖风景的,有所谓“西湖十景,钱塘十景”之说,虽里面也曾列入“断桥残雪”,“孤山霁雪”两个名目,但实际上,真的会去抚玩这种清寒不很近情的景致的,怕没有多少人吧。《四季幽赏录》的著者,在“冬时幽赏”门中,言及雪景的,几占十分的七八,其名目有“雪霁策蹇寻梅”,“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扫雪烹茶玩画”,“雪夜煨芋谈禅”,“山窗听雪敲竹”,“雪后镇海楼不雅观晚炊”等。个中大半所述景致,读了不禁移人神思,固不徒笔墨粹美而已。但他是一位洒脱出尘的绅士,以是能够有此独具心眼的幽赏;我们一方面自然佩服贰心境的博识,另方面却也可以证出能领略此中奥味者之以是稀少的一定了。
西湖的雪景,我共玩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此间初下雪的第三天。我于午前十点钟时才出去。一个人从校门乘黄包车到湖滨下车,徒步走出钱塘门。经白堤,旋转入孤山路。沿孤山西行,到西泠桥,折由大道回来。这次雪本不大,加以出去韶光太迟,山野上盖着的,大都已消去,以是没有什么动人之处。现在我要细述的,是第二次的重游。
那天是一月念四日。由于在床上感到意外冰冷之故,清晨初醒来时,我便预知昨宵是下了雪。果真,当我打开房门一看时,对面房屋的瓦上全变成白色了,天井中一株木樨花的枝叶上,也粘缀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白粉。详细的看去,以为比日前两三回所下的都来得大些。由于以前的,虽然也铺盖了屋顶,但有些瓦沟上却仍旧是玄色,这天却一色地白着,绝少铺不匀的地方了。并且都厚厚的,年夜约有一两寸高的程度。日前的雪,虽然铺满了屋顶,但于木樨花树,却彷佛全无关系似的,此回它可不免受影响了,这也是雪落得比较大些的明证。
老李照例是起得很迟的,有时我上了两课下来,才瞥见他在房里穿衣服,预备上办公厅去。这天,我起来跑到他的房里,把他叫醒之后,他犹带着几分睡意的问我:“老钟,本日表面有没有下雪?”我回答他说:“不但有呢,并且颇大。”他起初疑惑着,直待我把窗内的白布幔拉开,让他看见了屋顶才肯相信。“老钟,我们本日到灵隐去耍子吧?”他很高兴的说。我“哼”的应了一声,便回到自己的房里来了。
我们在校门上车时,大约已九点钟旁边了。时小雨霏霏,冷风拂人如泼水。从车帘两旁缺处望出去,路旁高起之地,和所有统统高低不平的屋顶,都撒着白面粉似的,又如铺陈着新打好的棉被一样平常。街上的已大半变成雪泥,车子在上面碾过,不绝的发出唧唧的声音,与车轮迁徙改变时磨擦着中间横木的音响相杂。
我们到了湖滨,便换登汽车。往时这条路线的搭客是颇热闹的,现在却很零落了。同车的不到十个人,为遨游而来的客人还怕没有一半。当车驶过白堤时,我们向车外眺望内外湖风景,但见一片迷蒙的水气弥漫着,对面的山峰,只有一个险些辨不清楚的薄影。葛岭、宝石山这边,由于间隔比较密迩的缘故,山上的积雪和树木,大略可以看得出来;但地位较高的保塔,便陷于朦胧中了。到西泠桥前近时,再回望湖中,见湖心亭四围枯秃的树干,好似怯寒般的在那里呆立着,我不禁遐想起《陶庵梦忆》中一段情词惧幽绝的笔墨来:
崇祯五年十仲春,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这天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天与云与水高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
”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湖心亭看雪》)
不知这时的湖心亭上,尚有此种痴人否?心里不觉漠然了一会。车过西泠桥往后,车暂驶行于两边山岭林木连接着的野道中。所有的山上,都堆积着很厚的雪块,虽然不能如瓦屋上那样铺填得均匀普遍,那一片片明净的光彩,却尽够使我感到宇宙的清寒、壮旷与纯洁!
常绿树的枝叶后所堆着的雪,和枯树上的,很有差别。前者由于有叶子衬托着之故,雪上特殊堆积得大块点,远了望去,如开满了白的山茶花,或吾乡的水锦花。后者,则只有一小小块的雪片能够在上面粘着不堕落下去,与刚著花的梅李树绝地相似。实在,我初头险些把那些近在路旁的几株错认了。野上半黄或全赤了的枯草,多压在两三寸厚的雪褥下面;有些枝条懦弱的树,也被压抑得欹欹倒倒的。路上行人很稀少。道旁野人的屋里,时见有衣饰破旧而笨重的老人、童子,在围着火炉取暖和。看了那种古朴清贫的情形,仿佛令我忘怀了我们所处时期的骚动、繁遽了。
到了灵隐山门,我们便下车了。一走进去,空气怪清冷的,不但没有游客,往时那些卖念珠、古钱、天竺筷子的小贩子也不见了。石道上铺积着颇深的雪泥。飞来峰疏疏落落的着了许多雪块,清冷亭及其它建筑物的顶面,一例的密盖着纯白色的毡毯。一个拍照的,当我们刚进门时,便牢牢的跟在后面。由于老李的高兴,我们便在清泠亭旁照了两个影。
好奇心打动着我,使我觉得到面前所看到的之不知足,而更向处境较幽深的韬光庵去。我幽悄地尽移着步向前走,老李也不张扬的随着我。从灵隐寺到韬光庵的这条山径,实际上虽不见若何的长;但颇深曲而饶于风致。这里的雪,要比城中和湖上各处的都大些。在径上的雪块,大约有半尺来厚,两旁树上的积雪,也最近路上所见的浓重。曾来嬉戏过的人,该不会忘却的吧,这条路上两旁是若何的繁植着高高的绿竹。这时,竹枝和竹叶上,大都着满了雪,向下低低地垂着。《四季幽赏录》“山窗听雪敲竹”条云:“飞雪有声,惟在竹间最雅。山窗寒夜:时听雪洒竹林;淅沥萧萧,连翩瑟瑟,声韵悠然,逸我清听。忽尔回风交急,折竹一声,使我寒毡增冷。”这种风味,可惜我没有福分消受。
在冬天,本来是游客冷落的时候,何况这样雨雪清冷的日子呢?以是当我们跑到庵里时,别的游人一个都没有,──这在我们上山时看山径上的足迹便可以晓得的──而僧人的眼色里,并且也有一种以为怪异的表示。我们一贯跑上末了的不雅观海亭。那里石阶高下都厚厚地堆满了水沫似的雪,亭前的树上,雪着得很重,在雪的下层并结了冰块。阁下有几株山茶花,正在艳开着粉赤色的花朵。那花朵有些堕下来的,半掩在雪花里,红白相映,色彩灿然,使我们感到华而不俗,清而不寒;因而联忆起那“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美人儿来。
登上这亭,在平日是可以近瞰西湖,了望浙江,甚而至于缥缈的沧海的,可是此刻却不能了。离庵不远的山岭、僧房、竹树,尚勉强可见,稍远则封锁在茫漠的烟雾里了。
空斋蹋壁卧, 忽梦溪山好。朝骑秃尾驴,来寻雪中道。石壁引孤松,长空没飞鸟。不见远山横,寒烟起林抄。(《雪中登黄山》)
我倚着亭柱,默默地在咀嚼着王渔洋这首五言诗的清妙;尤其是结尾两句,更道破了雪景的三昧。但说不定许多没有履历的人,要妄笑它是无味的诗句呢。文艺的真赏鉴,本来是件不随意马虎的事,这又何必咄咄见怪?自己讲授了一番,心里也就释然了。
本来拟在僧房里吃素面的,不知为什么,竟跑到山门前的酒楼饮酒了。老李不能多喝,我一个人也就无多兴致干杯了。在那里,我把在山径上带下来的一团冷雪,放进在羽觞里混着喝。堂倌看了说:“这是顶上的冰淇淋呢。”
半由于等不到汽车,半由于想多玩一点雪景,我们决意步辇儿到岳坟才叫小船去游湖。一起上,虽然走的是来时汽车经由的故道,但在徒步不雅观赏中,不免以为更有情味了。我们的革履,踏着一两寸厚的雪泥提高,频频地发出一种清脆的声音。有时路旁树枝上的雪块,忽然掉了下来,着在我们的外套上,正古人所谓“玉堕冰柯,沾衣生湿”的情景。我迟回着我的步履,旷展着我的视域,油然有一脉浓重而灵秘的诗情,浮上我的心头来,使我幽然意远,漠然神凝。郑綮答人家自己的诗思,在灞桥雪中,驴背上,真是怪懂得趣儿的说法!
当我们在岳王庙前登舟时,雪又纷纭的下起来了。湖里除了我们的一只小小船以外,再看不到别的舟楫。平湖漠漠,统统都沉默无哗。舟穿过西泠桥,缓泛里西湖中,孤山和对面诸山及高下的楼亭、房屋,都白了头,在风雪中兀立着。山径上,望不见一个人影;湖面连水鸟都没有踪迹,只有乱飘的雪花堕下时,微起些荡漾而已。柳宗元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我想这时如果有一个渔翁在垂钓,它很可以借来解释面前的景物呢。
舟将驶近断桥的时候,雪花飞飘得更其缭乱。我们向北一壁的外套,差不多大半白而且湿了。风也彷佛吹得格外紧劲些,我的脸不能向它吹来的方面望去。由于革履渗进了雪水的缘故,双足尤冰冻得难忍。这时,从来不多开过口的舟子,忽然问我们说:“你们以为此处比较寒冷么?”我们问他什么缘故。听说是宝石山一带的雪山风吹过来的缘故原由。我于是默默的兴想到知识的范围和它的得到等重大的问题上去了。
我们到湖滨登岸时,已是下午三点余钟了。公园中各处都堆满了雪,有些已变成泥泞。除了极少数在待买卖的舟子和别的苦力之外,平日朝夕在此间舒舒地来往着的少男少女、老爷太太,此时大都密藏在“销金帐中,低斟浅酌,饮羊羔美酒”,──至少也靠在腾着血焰的火炉旁,陪伴家人或石友,无忧虑地在大谈其闲天。──以享乐着他们幸福的光阴,再不愿来风狂雪乱的水涯,消受贫穷汉所应受的寒冷了!
这次的薄游,虽然也给了我些牢骚和别的苦味,但我要用良心做包管的说,它所给予我的心灵深处的欢悦,是无穷地深远的!
可惜我的诗笔是钝秃了。否则,我将如何超越了统统古墨客的狂热地歌咏了它呢!
好吧,容我在这儿恳切沥情地说一声,感激雪的西湖,感激西湖的雪!
孙犁 采蒲台的苇
我到了白洋淀,第一个印象,是水养活了苇草,人们依赖苇生活。这里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人彷佛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一直地在苇里穿来穿去。
我逐渐知道,苇也由于性子的软硬、坚固和薄弱,各有各的用场。个中,大白皮和大头栽由于色白、高大,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正草由于有骨性,则多用来铺房、填房碱;白毛子只有俊秀的形状,却只能当柴烧;假皮织篮捉鱼用。
我来的早,淀里的凌还没有完备融化。苇子的根还埋在冰冷的泥里,看不见大苇形成的海。我走在淀边上,想像如果是五月,那会是苇的天下。
在村落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公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备平复。关于苇塘,就不但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炸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影象。如果纯挚是苇,如果纯挚是好看,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
这里的英雄业绩很多,不能逐一记述。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仇敌的炮火,曾经摧残它们,它们无数次被火烧光,公民的血液保持了它们的明净。
最好的苇出在采蒲台。一次,在采蒲台,十几个干部和全村落男女被仇敌包围。那是冬天,人们被围在冰上,面对着等待收割的大苇塘。
仇敌要搜。干部们有的带着枪,认为是末了战斗流血的时候到来了。妇女们却偷偷地把怀里的孩子递过去,见告他们把枪支插在孩子的裤裆里。查抄的时候,干部又顺手把孩子递给女人……十二个女人不谋而合地这样做了。仇恨是一个,爱是一个,聪慧是一个。
枪掩护过去了,闯过了一关。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从苇塘打苇回来,被仇敌捉住。仇敌问他:“你是八路?”“不是!
”“你村落里有干部?”“没有!
”仇敌砍断他半边脖子,又问:“你的八路?”他歪着头,血流在胸膛上,说:“不是!
”“你村落的八路大大的!
”“没有!
”
妇女们忍不住,她们一齐沙着嗓子喊:“没有!
没有!
”
仇敌杀去世他,他倒在冰上。血冻结了,血是武断的,去世是刚强!
“没有!
没有!
”
这声音将永久响在苇塘附近,永久响在白洋淀公民的耳朵阁下,乃至该当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子孙。永久记住这两名简短有力的话吧!
杨朔 荔枝蜜
花鸟草虫,凡是上得画的,那原物每每也叫人喜好。蜜蜂是画家的爱物,我却总不大喜好。提及来可笑,孩子时候有一回上树掐海棠花,不想叫蜜蜂蜇了一下,痛得我差点儿跌下来。大人见告我说:蜜蜂轻易不蜇人,准是误以为你要侵害它,才蜇。一蜇,它自己就耗尽了生命,也活不久了。我听了,以为那蜜蜂可怜,体谅它了。可是从此往后,每逢瞥见蜜蜂,感情上疙疙瘩瘩的,总不怎么舒畅。
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那里四围是山,环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致,切实其实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刚去确当晚是个阴天,偶尔倚着楼窗一望,奇怪啊,怎么楼前凭空涌起那么多黑洞洞的小山,一重一重的,起伏不断?记得楼前是一片比较平坦的园林,不是山。这到底是什么幻景呢?赶到天明一看,忍不住笑了。原来是满野的荔枝树,一棵连一棵,每棵的叶子都密得不透缝,黑夜看去,可不就像小山似的!
荔枝大概是世上最鲜最美的水果。苏东坡写过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见荔枝的妙处。偏偏我来得不是时候,满树刚开着浅黄色的小花,并不出众。新发的嫩叶,颜色淡红,比花倒还中看些。从着花到果子成熟,大约得三个月,看来我是等不及在从化温泉吃鲜荔枝了。
吃鲜荔枝蜜,倒是时候。有人大概没听说这奇异物儿吧?从化的荔枝树多得像汪洋大海,着花时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那蜜蜂忘却早晚,有时趁着月色还采花酿蜜。荔枝蜜的特点是成色纯,养分大。住在温泉的人多数喜好吃这种蜜,滋养精神。热心肠的同道为我也弄到两瓶。一开瓶子塞儿,便是那么一股甜喷鼻香;调上半杯一喝,甜喷鼻香里带着股清气,很有点鲜荔枝味儿。喝着这样好的蜜,你会以为生活都是甜的呢。
我不觉动了情,想去看看自己一向不大喜好的蜜蜂。
荔枝林深处,模糊露出一角白屋,那是温泉公社的养蜂场,却起了个有趣的名儿,叫“养蜂大厦”。正当十分春色,花开得正闹。一走近“大厦”,只见成群结队的蜜蜂出出进进,飞去飞来,那沸沸扬扬的情景,会使你想:说不定蜜蜂也在赶着培植什么新生活呢。
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叫他老梁,实在是个青年人,举动很风雅。大概是老梁想叫我深入一下蜜蜂的生活,他小小心心地揭开一个木头蜂箱,箱里隔着一排板,板上满是蜜蜂,蠕蠕地爬动。蜂王是黑褐色的,身量特殊长,每只蜜蜂都乐意用采来的花精来养活它。
老梁惊叹似的轻轻说:“你瞧这群鄙吝械,多听话!
”
我就问道:“像这样一窝蜂,一年能割多少蜜?”
老梁说:“能割几十斤。蜜蜂这东西,最爱劳动。广东景象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留下一点点,够它们吃的就行了。它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连续劳动,连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劳……”
我又问道:“这样好蜜,不怕什么东西来挥霍么?”
老梁说:“怎么不怕?你得戒备虫子爬进来,还得戒备大黄蜂。大黄蜂这贼最恶,常常落在蜜蜂窝洞口,专干坏事。”
我不觉笑道:“噢!
自然界也有侵略者。该怎么对付大黄蜂呢?”
老梁说:“赶!
赶不走就打去世它。要让它呆在那儿,会咬去世蜜蜂的。”
我想起一个问题,就问:“一只蜜蜂能活多久?”
老梁回答说:“蜂王可以活三年,一只工蜂最多能活六个月。”
我说:“原来寿命这样短。你不是总得往蜂房外边打扫去世蜜蜂么?”
老梁摇一摇头说:“从来不用。蜜蜂是很懂事的,活到限数,自己便悄悄去世在外边,再也不回来了。”
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微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
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着远远的野外,那儿正有农人立在水田里,辛费力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培植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
这天夜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