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之美,美在词语。唐诗留下了多少独特的词语,诗性与神韵,情绪倏忽来去的瞬间。
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唐代墨客,站在诗歌艺术金字塔的顶端,使汉措辞成为了独美天下的措辞。“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些光大了汉措辞文化的伟大墨客,理应被我们永久铭记。
唐诗源流
唐诗的繁华,既不是历史的有时,亦非瞬息之作。唐朝之前,中国诗歌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至少经历了三次洗礼。《诗经》一也,它是上游,是源头,有开辟之功,是加工致顿中国措辞的辉煌开始,新鲜灵动,晶莹剔透,温顺敦厚;是中国诗歌初试啼声的第一个春天。《楚辞》二也,它是中国诗歌长河由北而南的一次奔流,在楚地的广阔大地上搜集了当地新鲜的、奇崛的神话与想象,屈原之天上人间,芳草美人,朝发苍梧,夕至县圃,其想象之光怪陆离,古人所无,时人仅见。陶渊明其三也,历经两晋和南北朝的分裂、战乱,社会思潮的混浊不清,陶渊明自中年后弃仕务农,耕读自娱,冲淡高洁。他以“劳役”取代“心役”,其乐无穷。《读〈山海经〉》第一首:“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陶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不雅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早晚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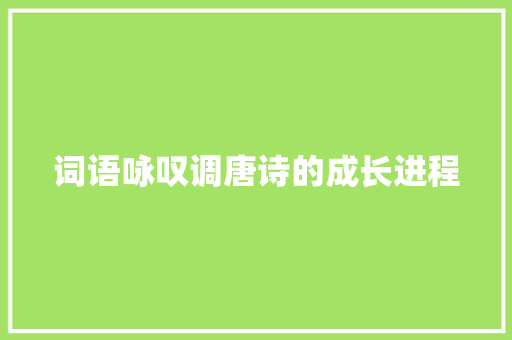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也……无我之境,以物不雅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陱渊明,豪杰之士也。
玫瑰曙光
陆时雍《诗镜总论》评说“初唐四杰”:“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郑振铎称:“沈宋(指沈佺期、宋之问,引者注)时期的到来,盖在四杰的所作里,已看到其先行程的踪迹了。”《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笔下无离情别愁,写送别地长安,为苍茫山野护卫,“城阙辅三秦”也。“海内存心腹,天涯若比邻”,则世代流传。杨炯《王勃集序》说:“动摇文律,宫商有奔命之劳;沃荡词源,河海无息肩之地。”杨炯恃才傲物,善五言。《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诗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六十八行,以“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喷鼻香车”开篇,前三十行中,“得成比目何辞去世,愿作鸳鸯不羡仙”,已为不朽佳句。结尾是:“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当年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寥寂寥寂扬子居,年年纪岁一床书。独占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光阴,永恒者也;松树桂花,柔弱而倔强者也;扬雄,自甘贫穷者也。《长安古意》,及骆宾王其时以为绝唱的《帝京篇》,是初唐七言歌行的代表作。骆宾王以歌行体见长,亦作五言。《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当年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对“初唐四杰”,杜甫有诗赞曰:“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歌行体因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得以传承:“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张若虚的诗存世只两首,另一首为五言《代答闺梦还》。张若虚被称为唐朝墨客中“最
旷野啸声
舒芜夸奖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是“迈向阔大和永恒的诗篇”。其《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舒芜有解:“墨客登上高山之巅,眺望宇宙,只见白日已在西天熄灭,云海正在动荡翻滚。孤零零的一条小鱼,又怎能得到安宁之处呢?墨客眼中的境界便是这样阔大,他把一个人比作孤鳞,密切联系着像云海一样动荡翻滚的大宇宙,来不雅观察他的命运。”陈子昂为初唐作结,韩愈在《荐士》中赞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高蹈,高扬蹈奋者也!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的一条分界。墨客们不得不从繁华中走出来,走向动乱,走向困苦,走向边关,并且外不雅观自察:写什么?若何写?墨客的眼力由此变得冷峻复苏,并以不安焦虑去不雅观照现实。是时也,李白、杜甫双峰凌云。山水诗,戍边诗,蔚然成风,或清啸山水间,或呼啸边塞风沙,映带李杜之侧而增风光。
山水田园派史称“王孟”诗派,王维、孟浩然也。王维先是亦官亦隐,写《终南山》,开唐代宗承陶渊明一派之先声:“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语近天然,深美闳约。《鹿柴》月照青苔也,《鸟鸣涧》空山鸟鸣也;又《竹里馆》对月长啸也,《山居秋瞑》多摇荡洒脱之动感:“空山新雨后,景象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孟浩然是盛唐墨客中的另类,他应举落第后终生不仕,漫游东南,隐居终老。孟浩然是漫游者,诗亦有游走感,《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又:“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淡得不能再淡了,清得不能再清了,一种风景,一样心情,一幅白描,漂移在诗歌的长河中。孟浩然有的诗寻不着一点琢磨的痕迹,《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落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李白《赠孟浩然》云:“吾爱孟役夫,风骚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盛唐边塞诗中最有代表性的墨客是高适和岑参。高适的诗多雄浑凄凉,如《送李侍御赴西安》:“行子对飞蓬,金鞭指铁骢。功名万里外,苦处一杯中。虏障燕支北,秦城太白东。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又《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纭。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郑振铎说岑参是“开天时期,最富有异国情调的墨客”。岑参在唐代边塞墨客中的独特性在于,从天宝八年(749)首次戍边,远赴龟兹,两度出塞,漫游西域,足迹与笔触,直至新疆葱岭内外,无边荒沙,大块荒野。岑参是当时墨客中走得最远、最有荒野气的墨客。岑参善作七言歌行体,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玄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同作于轮台军中,一样风格,两种措辞,各有韵味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全诗均以雪为背景,边塞白雪,春花喻雪,纷纭暮雪。迵然相异的环境,恍若隔世的人生经历,热血沸腾的墨客,笔端蘸满感情的词语,岑参的诗便突兀于绝域风沙中。殷璠论之为“语奇体峻,意亦造奇”。在盛唐以边塞诗有名的,还有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立时催。醉卧疆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之涣有《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东风不度玉门关。”《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穷天地之大不雅观也!
双峰凌霄
现在,我们要仰望盛唐诗歌的两座山顶极峰:李白与杜甫。从创作而言,李杜分属不同期间。李白的名作,大多写于安史之乱前。郑振铎写李白:“他的诗,纵横驰骋,若天马行空,无迹可寻;若燕子追逐于水面之上,倏忽东西,不能羁系……如游丝,如落花,轻隽之极,却不是言之无物;如飞鸟,如流星,自由之极,却不是没有轨辙;如侠少的狂歌,农工的高唱,粗豪之极,却不是没有腔调;他是蓄储着过多的天才的,随笔挥写下来,便是晶光莹莹的珠玉;在腔调的铿锵上,他似尤有特长。他的诗篇险些没有一首不是掷地作金石声的。尤其是他的长歌,险些个个字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吟之使人口齿爽畅,若不可中止。”
李白将功名、寻仙、侠客、饮者,游走江湖集于一身。李白的乐府歌行体长诗,雍容华贵,笔若悬河,倾泻不绝,《将进酒》开卷气吞斗牛,一任想象驰骋,尽遣万斛珍珠,写黄河之来也,天地无穷;二句急转直下,青丝白发,人生短暂,朝暮而已,写流光之逝也!无限感慨之下,“将进酒,杯莫停”,由于“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贬,作《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涯着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写一种告别,也是出发,“明朝散发弄扁舟”也。
胡应麟《诗薮》称:“太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李白在此类作品中表现的,是想象瑰丽,是词语姣好,是意境苍茫。如《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一首七言绝句尽显措辞熬炼之功。峨眉山,天上月,平羌江,清溪,三峡等等,不是嵌入的,而是一体的。其五言绝句亦天人合璧,如:“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李白以谪仙有名,而梁启超则以“情圣”论杜甫:“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杜甫紧张造诣在安史之乱后。杜甫对社会动荡有着极敏锐的觉得。在他四十岁之前,安史之乱还未发生时,便预感到了山雨欲来。如《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诗以浓墨点题,次第展开的,是一幅“爷娘妻子走相送”的长卷别离图。用的是普通口语,爷娘妻子口中出。经由情绪的浸润,成为杜甫笔下诗的措辞。令人惊奇的是,杜甫若何酝酿、熬炼、整理措辞,并使之戛戛独造,如入化境?如果说李白的措辞是从天而泻的,那么,杜甫的诗句便是从地里长出,与生俱来,生生不息;或者经年累月铸炼于肚量胸襟,然后喷薄而出。他的想象若风卷云霞雨露,又落在众生之间;他的情怀能容得四海之内,天下慈悲。“蓄储着过多的天才”,李杜皆然。沉郁抑扬,其风格也;情绪浓郁,其心性也;众体兼备,其才情也;恢宏博大,其境界也。
杜甫以先知预言家,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乾隆十五年《御选唐宋诗醇》论曰:“摅郁结,写胸臆,苍苍莽莽,一气流转。其大段有千里一曲之势,而笔笔抑扬,一曲中又有无数弯曲也。……言言深切,字字沉痛,板荡之后,未有能及此者。此甫之以是度越千古而上继三百篇者乎?”诗自“杜陵有布衣”始,个中有“豪门酒肉臭,路有冻去世骨”句。杜诗集诗歌艺术之大成,是非诗无不精美。《月夜》写月,却是三处月,三处夜,一种境界。鄜州月夜,想象得之;墨客身陷长安而长安月夜未着一字;期待与家人团圆写“清辉月臂寒”。凡此月色,无不从妻儿落笔,诗情从鄜州天上的月光漫泻而至:“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喷鼻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杜甫的诗,写底层民生,却挺立浩然,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至今,“安得广厦千万间”,不仍是人类的梦想吗?杨伦《杜诗镜铨》中赞为“杜集七律第一”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羽觞。”《登高》是词语的典范:通篇对仗,实为律诗之忌。杜甫却笔无稍滞,佳句连篇。“万里,地之远也;悲秋,时之悽惨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极精确。”(罗大经:《鹤林玉露》)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严羽称:“子美不能为太白之洒脱,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良可信也!
以李杜为代表的唐代墨客,在诗歌艺术金字塔的顶端,使汉措辞成为了独美天下的措辞。
韩孟元白
韩孟,韩愈、孟郊也,史称韩孟诗派;元白,元稹、白居易也,史称元白诗派。唐代历史在纷乱不安中,进入了贞元、元和期间,有了中唐诗歌之盛。清人冯班《钝吟杂录》谓:“诗至贞元、元和,古今一大变。”叶燮《百家唐诗序》称,中唐诗非唐诗之“中”,乃“百代之‘中’”。
韩孟二人中孟郊齿长,他生平潦倒穷困,以苦吟著称。其诗讲究炼字造词,境界奇崛。《送殷秀才南游》:“风叶乱辞木,雪猿清叫山。”《远愁曲》:“声翻太白云,泪洗蓝田峰。”韩愈称其“横空盘硬语,妥善力排奡。”其《苦寒吟》:“百泉冻皆咽,我吟寒更切。半夜倚乔松,不觉满衣雪。竹竿有甘苦,我爱抱苦节。鸟声有悲欢,我爱口流血。潘生若解吟,更早生白发。”孟郊诗寒,也有不尽暖意者,《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韩孟诗派中,贾岛诗瘦,苦吟又苦吟故也。贾岛的《绝句》:“海底有明月,圆于天上轮。得之一寸光,可买千里春。”《题诗后》:“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题李凝幽居》:“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一瓢诗话》称:“贾岛诗骨清峭。”韩愈有《赠贾岛》诗:“孟郊去世葬北邙山,从此风云得暂闲。天恐文章浑断绝,重生贾岛著人间。”
清人赵翼写《瓯北诗话》说韩愈,“辟山开道,自成一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郑振铎谓:“而他的才情的弘灏,又足以肆应不穷,其结果,便树立了诗坛上的一个奇帜,一个独创出来的奇帜。”韩愈集奇险、峥嵘的物象于一炉,如《苦寒》:“凶飙搅宇宙,铓刃甚割砭。日月虽云尊,不能活乌蟾。羲和送日出,恇怯频窥觇。炎帝持祝融,呵嘘不相炎。”《南山诗》连绵二百多行中,以五十多个“或”字开头,写山石岩崖之千奇百态,“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辏,或翩若船游,或决若马骤……”想象如风狂雨骤,词语若高山瀑布。
李贺有韩愈风格,“险怪如夜壑风生,瞑岩月堕”(谢榛语),有鬼才之称。其《李凭箜篌引》,一鸣惊人。
在韩孟诗派称雄之际,能我行我素的,是柳宗元、刘禹锡。柳诗无艰深怪异,因着人生蹉跎,他的诗多内向的追思。《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刘禹锡写《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间几次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到处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又写《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赵翼认为:“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峻,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如果说韩孟派的诗,像枝叶落尽的冬日;白居易一派的诗,却如春水盈盈,波光流转的了。”
白居易的《琵琶行》是中国诗史上,李贺《李凭箜篌引》之后,又一首写音乐且影响更广的作品。音乐之声何能写,何能说?能说能写又何必音乐?其知难而写,而妥切者,而比之急雨,密语,大珠小珠落玉盘,想象奇崛动人心魄者,其声若莺语,流泉,银瓶乍破,铁骑突出,四弦裂帛,跃动在字里行间者,非天才不能为也!在唐墨客的序列中,李杜之后,韩愈继之,韩愈之后,白居易为重。“同是天涯沉沦腐化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句,岁月不能磨损其毫末,感慨声至今犹在。元稹与白居易,相与桴鼓,互为木铎。元稹《离思五首》之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
有唐一代,怀古咏史,均涌如今时期风云交会时。晚唐诗坛杜牧和李商隐,史有“小李杜”之称。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有杜诗之“沉郁”也。
李商隐,字义山,他的文学主见是:“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故阴惨阳舒,其途不一,安乐哀思,厥源数千。”他看重人的七情六欲,主见诗应书写性灵、情绪和希望,他用词怪险,造句艰深。敖器之说他“绮密瑰丽”;程梦星说他“诡谲善幻”。无题诗是他的独创,七律是他的奇葩。如《赠刘司户蕡》:“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已断燕鸿初起势,更惊骚客后归魂。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李商隐《咏史》句乃千秋万代座右铭:“历览先哲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破由奢”之明证者,《隋宫》也:“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李商隐的《无题》诗,意境奇特,词语隠微,《无题四首》之一:“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又《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李商隠诗中的形象,时或冷峭,时或斑斓,时或梦幻。“旨意幽深,婉转动情,有如一颗蓝宝石,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吸引着世世代代的读者”(《唐诗鉴赏集》)。凡落花,垂柳,咏月,咏蝶,均有佳作。“远恐芳尘断,轻忧艳雪融”,芳尘能断雪可艳,李商隐之词语也;“相兼惟柳絮,所得是花心。”柳絮飘飏花有心,李商隐之风情也。
吴乔《围炉诗话》说:“于李、杜、韩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惟李义山一人。”他的贡献既不在题材,也不在文体,而是他的措辞。李、杜、韩之后,白居易以夷易浅近的措辞写诗,“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李忱:《吊白居易》);李商隐则凿险缒幽,情思婉转,意境要眇,独构“沉博艳丽”“寄托深而措词婉”(叶燮:《原诗》)的风格。
有李商隐承前启后,唐诗堂庑深广。唐诗幸哉!中国幸哉!
尾声:蓦然回顾
蓦然回顾,是一种意象,也是寻觅和讶异,诗和梦想、情绪瞬间萌发的象征。民气里最柔弱敏感的便是情绪,而最能触碰情绪的便是诗。唐诗留下了多少独特的词语,诗性与神韵,情绪倏忽来去的瞬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也。唐诗焉能不读?焉可不读?王夫之《俟解》谓:“贤人以诗歌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然诗由词语组成,词语由字组成,诗的措辞绝对是不一般的措辞。以诗歌荡涤其心者,必得识字明词,是有识字闻道说,是有措辞文明说。
梁启超在《国文语原解》中说:“国民之所以为国民以独立于天下者,实受自历史上之感化,与夫其先代伟人哲士之鼓铸也。而我笔墨起于数千年前,一国历史及无数伟人哲士之精神所攸托也。”梁启超见告我们,我国笔墨行之数千年,中华民族发奋图强亦几千年。笔墨独立而民族独立,笔墨相续而文明相续。笔墨之功全赖先代伟人哲士之“鼓铸”也;鼓铸者,鼓风扬火熏陶熬炼笔墨、词语之谓也,然后有诗。人类学家李济认为,汉语“在动荡变迁中留存至今,它已保护了中华文明四千多年。它是稳固的,方正的,正如它代表的精神一样俏丽”。汉措辞的主要性于此可见。
想起了屠格涅夫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揭幕仪式上的演说》:“是普希金末了加工了我们的措辞……是他用范例形象和不朽音韵,对俄罗斯生活的统统潮流作出反应。末了,是他第一个用强有力的手臂,把诗歌的旗帜深深插进俄罗斯的地皮。”屠格涅夫在《关于〈父与子〉》的结末处,对年轻的俄罗斯文学家们的“末了的要求”是:“请爱护我们的措辞,爱护我们美妙的俄罗斯措辞,这一宝藏,这一财富,因此光辉的普希金为首的先行者传给我们的!”
朋友们,请爱护我们无比美妙的中国措辞,请铭记那些比普希金更早的、使中华民族成为诗性民族的、“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的伟人哲士。请保重来自远古的情绪和词语,还有蓦然回顾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