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一座多水的城市,而西湖的水则是这座城市最为显眼的名片,西湖水量充足,有多条山涧溪水注入,像金沙涧、龙泓涧、赤山涧、长桥溪这四条天然的地表水不谋而合地向一个地方流去,形成了风采绰约的西湖。
西湖,犹如一块被镶嵌在群山中的蓝宝石,一年四季变换着不同的风采,但不管如何,那都是“淡妆浓抹总合适”的迷人风光。喜好西湖的人很多,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个中之一,他对西湖的喜好,浸润着繁芜的情绪,有许多深奥深厚的怀恋。
张岱,字宗子,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生于仕宦世家,过着巨室公子的生活,精于茶艺鉴赏,喜好游山玩水,通达音乐戏曲,善于散文诗词。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三不朽图赞》等文学名著。张岱与杭州西湖的渊源深厚。
小时候,他祖父带他来杭州,赏景、探友,祖父在西湖有别墅寄园。就在那个时候,西湖在张岱心中打下了底色。张岱后来寓居杭州,写有许多散文诗词,描写他喜好的杭州、西湖、西溪。在张岱的作品中,留下了他在杭州生活的许多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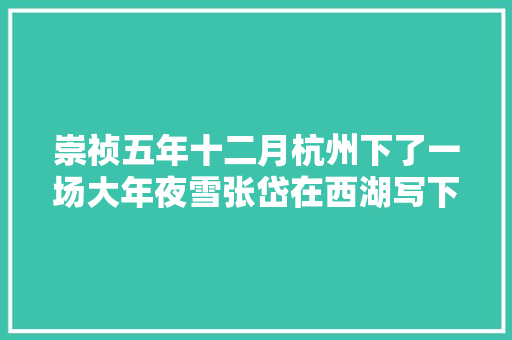
中年之前,张岱目睹了晚明西湖世俗社会的繁华和文人聚会的风雅。西湖有他的许多人生回顾。明朝风雨飘摇之际,张岱离开了杭州。明亡后,他作为前朝遗民,入剡溪山中隐居著书,在山中回顾往昔,遥想当年西湖的湖光山色、人物风骚。
在张岱的心目中,西湖是故国故宅的详细表示。在阔别杭州的二十八年里,西湖常常进入张岱的梦中。他于顺治十一年(1654)、顺治十四年(1657)两次到杭州。嫡黄花,经历过战火洗礼的杭州西湖,已不是当年的西湖,重游西湖的觉得也是“终不似少年游”的觉得。
他感到失落落,遗憾地感叹:“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备无恙也。”在他的梦中,西湖是最华美的景象。然而他梦中西湖所存在的东西,在现实的西湖中反倒没有了。
于是,张岱在这样的心态下写成《陶庵梦忆》八卷、《西湖梦寻》七十二则,将亲自经历过的事情和江南及西湖景物,在笔端娓娓道来,给后世留下了一片篇篇浮光掠影般的文化印记,张岱自己也说:“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
在《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中,可看到他曾过眼的西湖繁华,读出他散文的特色和他所具有的魏晋风姿。《陶庵梦忆》中,有一篇《湖心亭看雪》,追忆了他重游西湖的故事,文章安谧的美感,读来意境非凡,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崇祯五年(1632)十仲春,张岱住在西湖边。一个下了三天算夜雪之后的晚上,湖上一片寂静,没有一点人和鸟的声音。他乘一叶小舟,穿着毛皮衣,带着火炉,独往湖心亭看雪,并将这次独特的西湖之行写成一篇精美的小品文《湖心亭看雪》。
湖心亭,中国四大名亭之一,位于西湖中心,与三潭印月、阮公墩合称湖中三岛,是西湖三岛中最早营建的岛,在宋、元时曾有湖心寺,后倾圮。明代有知府孙孟建振鹭亭,后改清喜阁,是湖心亭的前身。在湖心亭纵目四眺,湖光皆收眼底,群山如列翠屏,在西湖十八景中称为“湖心平眺”。
晚明小品在中国散文史上虽然不如先秦诸子或唐宋八大家那样引人瞩目,却也霸占一席之地。它如开放在深山石隙间的一丛幽兰,疏花续蕊,迎风吐馨,虽无灼灼之艳,却自有一种清高拔俗的风采。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便是这样的一篇美文,原文如下:
崇祯五年十仲春,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这天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高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
”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崇祯五年十仲春,余住西湖。开头两句点明韶光、地点。大意是说:崇祯五年十仲春,我住在西湖边。张岱的文集中但凡涉及纪游之作,大多标明朝纪年,以示不忘故国。
文章开篇的“崇祯五年”既点明详细韶光,也表示自己不忘故国的情怀。农历十仲春正当隆冬多雪之时,“余住西湖”,则点明所居邻西湖。这开头的闲闲两句,却从韶光和地点两个方面不着痕迹地引出下文的大雪和湖上看雪。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紧承开头,只此两句,大雪封湖之状就令人可想,读来如觉寒气逼人。作者妙在不从视觉写大雪,而通过听觉来写,大雪过后的西湖一片静寂,湖山封冻,人、鸟都瑟缩着不敢外出,寒战得不敢作声,连空气也仿佛凝集了,连韶光彷佛都停滞了。
一个“绝”字,传出雪窖冰天、万籁无声的森然寒意。这是高度的写意手腕,奥妙地从人的听觉和生理感想熏染上画出了大雪的威严。这个“绝“字会让人情不自禁地遐想起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江雪》一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这幅江天算夜雪图是从视觉着眼的,江天茫茫,人鸟无踪,独占一个雪中垂钓的渔翁,一种孤寂之感跃然纸上。张岱笔下的西湖则是“人鸟无声”,但这无声却正是人的听觉感想熏染,因而无声中仍有人在。
柳宗元的《江雪》一诗末了才点出一个“雪”字,可谓即果溯因。张岱则开篇明义,地说道,连续下了三天雪,导致湖中人鸟声俱绝,可谓先因后果。虽然两人的切入点和视角不一样,却同样达到写景真切的艺术效果。
如果说,柳宗元的《江雪》中的前两句是为了渲染和衬托寒江独钓的渔翁;那么张岱《湖心亭看雪》中的前两句则为下文有人冒寒看雪做足了行文上的铺垫和气氛上的渲染。
这天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接下来的这四句大意是说:这天初更时分,我撑着一叶小舟,裹着细毛皮衣,带着火炉,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
更定,指初更时分,大致相称于晚上八点旁边。试想,在雪窖冰天里,竟有人夜深出门,前往湖心亭看雪,这是一种何等迥绝流俗的孤怀雅兴啊。
杭州在地理上位于江南,雪并不常见,何况大雪连下了三天。这不能不让居住在西湖的张岱感到愉快。于是准备好保暖衣物和小火炉,欣然起行。
如果说“余拏一小舟”重在表现轻松清闲之感的话,那么,“余舟一芥”则是将作者置身于大西湖的背景下,突感自己微如草芥的悲叹。
《庄子·逍遥游》云:“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芥,即眇小意。张岱此处以舟喻芥,来反衬西湖之阔、天地之大,感叹人之微小如沧海一粟,沉沉浮浮,不由自主,流落之感油然而生。
本为轻松赏雪而来,为何又遁入流落不定的情网中呢?在这里,张岱那种独抱冰雪之操守和孤高自赏的情调,不是溢于言外了吗?其以是要夜深独往,大约是既不欲人见,也不欲见人;那么,这种孤寂的情怀中,不也蕴含着避世的幽愤吗?
请看作者以何等空灵之笔来写湖中雪景: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高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 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这真是一幅水墨模糊的湖山夜雪图,雾凇沆砀是形容湖上雪光水气,一片弥漫。“天与云与山与水,高下一白”,迭用三个“与”字,生动地写出天空、云层、湖水之间白茫茫浑然难辨的景象。
张岱所见的雪景起笔即描写西湖的雾凇景象,这种景象对读者理解“高下一白”是很主要的。 形成雾凇是由于冬天景象寒冷,雾气凝集于树上,就结成了微粒,而沆砀则是空气中的白气还未凝集的状态,以是一片迷蒙。
那时候大概没有景象变暖,大雪三日后的景象极寒,又近水面,连西湖的夜雪也可见雾凇。白气、水雾、颗粒,从空中到树上,弥漫一片,虚幻看不清,的确便是混沌一片的开始。看不清的,还有天、云、山、水,连长堤、湖心亭、舟、人,也都不可避免地被笼罩,轮廓全模糊了,混入全白的一 片水汽里,构成“高下一白”的混沌画面中依稀可辨的元素。
其余,同行者明明有“两三粒”,但张岱为何要说成是“独往”呢?除有文人的清高之外,还与柳宗元《小石潭记》一文有异曲同工之妙。柳宗元《小石潭记》写道:“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同游小石潭的人,除了柳宗元,还有五人,可是柳宗元偏偏却说寂寥无人,这样的抵牾皆与柳宗元由小潭的幽寂勾起了积郁在内心深处的清冷与孤寂,终极凄神寒骨、深陷个中,全然忘怀了他人的存在。
张岱也有此意,但又比柳宗元多了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追求。这种希夷之境的追寻既有精神上的崇高,同时亦是作者的无奈之举。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简约的画,梦幻般的诗,给人一种似有若无、依稀恍惚之感。作者对数量词的熬炼功夫,不得不使我们惊叹。文中的“痕”“点”“芥”“粒”等量词,一个小似一个,写出视线的移动,景物的变革,使人以为天造地设,生定在那儿,丝毫也撼动它不得。
这一段是写景,却又不止于写景;我们从这个混沌一片的冰雪天下中,不难感想熏染到作者那种人生天地间茫茫如沧海一粟的深奥深厚感慨。
张岱寥寥数语,把西湖雪景一笔带过,之后便不再提及,转为弃景写人,文章又呈现出另一个境界: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
”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独往湖心亭看雪”,却不虞亭上已有人先我而至;这意外之笔,写出了作者意外的惊喜,也引起读者意外的惊异。但作者并不说自己惊喜,反写先到的两位游客见到作者的惊喜之情。
“湖中焉得更有此人!
”这一惊叹虽然出自二客之口,实为作者的心声。作者妙在不发一语,而尽得风骚。二客“拉余同饮”,鼎足而三,颇有幸逢心腹之乐,彷佛给冷寂的湖山增长了一分暖色,然而骨子里依然不改其凄清的基调。“强饮三大白”,是为了酬谢心腹。作者本来是不饮酒的,但对此景,当此时,逢此人,却不可不饮。饮罢相别,始“问其姓氏”,却又妙在语焉不详,只说:“是金陵人,客此。”可见这两位西湖雪景中偶遇的心腹,原是他乡游子,言外有后约难期之慨。
这一补叙之笔,透露出作者的无限怅惘:茫茫六合,心腹难逢,人生如雪泥鸿爪,转眼各复西东。言念及此,岂不让人黯然神伤。
行文至此,在我们看来,也算得神完意足、毫发无憾了。但作者意犹未尽,复笔写了这样几句:及下船,舟子喃喃自语道:“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读至此,真使人拍桌赞叹!
古人论词,有点、染之说,这个尾声,可谓融点、染于一体。借舟子之口,点出一个“痴”字;又以相公之“痴”与“痴似相公者”比较较、相感化,把一个“痴”字写透。所谓“痴似相公”,并非减损相公之“痴”,而因此同调来映衬相公之“痴”。“喃喃”二字,形容舟子自言自语、大惑不解之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这种地方,也正是作者的得意处和感慨处。文情荡漾,余味无穷。痴字表明特有的感想熏染,来展示他钟情山水,淡泊孤寂的独特个性。
对张岱来说,西湖是他的梦里水乡,他在这种魂牵梦绕的忆恋西湖旧景中,抒发着时期变迁的感慨。张岱的这一篇小品文,融叙事、写景、抒怀于一炉,偶写人物,亦口吻如生。淡淡写来,情致深长,而全文连标点在内还不到二百字,光是这一点,就很值得文学爱好者借鉴和学习。
小话诗词
张岱湖心亭看雪之事发生在明末崇祯五年,是作者五十岁之后的事情。由于时期的巨变,他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宴游无拘、裘马浮滑的绅士生活烟消云散后,他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明代遗民。
隆冬大雪之夜,独身只身孤舟湖中看雪,意趣迥异于凡人。读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很随意马虎遐想到《世说新语》中的《王子猷访戴》,同样是在大雪天,同样是驾着小舟别出心裁的特立独行,同样有酒,同样的奇遇。
在文章的结尾,王子猷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张岱借童子的口说:“莫道相公痴, 更有痴似相公者。”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子猷作为东晋大士族家庭中的一员,大书法家王羲之第五子,是一个凭禀性行事,任性而为、不拘常礼、玩世不恭的人。王子猷访戴多被算作是绅士的任性放肆,洒脱自适。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或许也是绅士任性放肆的魏晋遗风的延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