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不仅仅因此一种和“比”、“赋”并列的表现技巧,它更是一首诗歌整体构思的艺术思维办法。
提到诗歌中“兴”,我们自然会想起《毛诗序》中的一段话: “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三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
孔颖达《毛诗正义》阐明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 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风、雅、颂是《诗经》中的三种文体。赋、比、兴是表现方法.。这是《毛诗序》以及孔颖达《毛诗正义》的阐明。
对付“赋、比、兴”中的“赋”和“比”的界定历来比较清楚,也比较同等,认为比较纯挚可解,是表现手腕其技巧性很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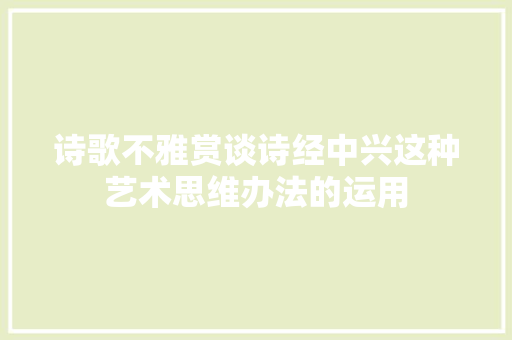
对付“比”界定的最好的,也是人们常常引用的,便是南宋的经学大师朱熹说的:“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对付“赋”便是直叙其事,大都以晋代挚虞的:“赋者,敷陈之称也。”为引据。
而争议比较多的是“兴”的界定。最早给“兴”下定义的是汉儒郑众,他在注《周礼》中说:“兴者,托事于物也。”其意为:“兴”便是把要说的意思,寄托在一种事物上。
宋朱熹定义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以上这些说法,对“兴”的认识紧张局限在表现技巧,手腕上。
到了晋代挚虞,他对“赋比兴”做了全面阐明,他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文章流别论》)
他以“有感”阐明“兴”不再把“兴”当作纯挚的艺术技巧来看了。南朝刘勰进一步指出:“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兴则环譬以托讽。”《文心雕龙.比兴》)
这里,他指明了"兴"的主要特性是"起情",在事物之间的奇妙联系中引起墨客的情思。(这已经不是像“赋”和“比”仅仅是一种遣词造句和行文的技巧而是对整体诗歌的构思的艺术思维。在这里他指明了“兴”的主要特性是“起”;起什么?起情;若何起法?在事物之间的奇妙联系中引起墨客的情思,“兴”体也就形成了。显然刘勰捉住了“兴”与诗歌传达思想内容的主要性,已经初步地把“兴”纳入了艺术构思范畴之中)
和刘勰同时期的钟嵘则从艺术效果方面间接探寻“兴”的实质,认为“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诗品序》)这是曲以表意,暗示了“兴”必须与思想内容的艺术传达联系在一起。联系《诗经》的“兴”法多在首句起兴的显著特色,钟嵘是从诗的总体的艺术构思着眼的。
到了唐代有着创作履历的苦吟墨客贾岛的一段话更明确他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日“兴”。(《二南密旨》)他已经清楚地讲明白了诗歌创作是被外物所触动后“内动于情,情不可遏”而“兴”起,便写出诗歌来的详细过程。
宋李仲蒙还有"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的阐明。
李硕说:“自古工诗,未尝无兴也,睹物有感焉则有兴。”梅尧臣说:“贤人于诗言,曾不专,个中 ;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李硕和梅尧臣两个人的说法,异曲同工。 解释诗歌创作必须由感起兴而产生,由感物而写成的诗,既有真情实感而内容充足,又能情物相通,情景交融。
宋代杨万里乃至以此衡量诗:“大抵诗作也,兴上也,赋次之。
宋代杨万里乃至以此衡量诗:“大抵诗作也,兴上也,赋次之,赓和(注:续用他人原韵或题意唱和),不得已也。“
杨万里的意思是说:赋诗与和诗都次于兴诗,其缘故原由在于不是对物的直接感想熏染,墨客的情绪只有被现实生活中的有关事、有关情绪、有关理所激,因物兴以通,才能写出好诗来。
由于"兴"是由外物触及到墨客们的内心,墨客们早就各自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履历、需求渴望、感情态度、情绪特质等的差 异。与外物的往来赠答就会千差万别,而由于外物只是一个触发诱因,而不是外物的再现,因而写出来的诗便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 的效果.即钟嵘所言"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诗品序》)
中国诗论一向推崇富有"兴"味之诗。宋代著名学者罗大经提出:"诗莫尚乎兴"的不雅观点.他认为:
"诗莫尚乎兴.……盖兴者,因物感触,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玩味乃可识,非若赋,比之直陈其事也.故兴多兼比赋,比赋不兼兴,古诗皆然."(《鹤林玉露.诗兴》)
兴之以是在诗艺上要比“比”和“赋”高,就在于兴有寓意言外的特点,他可以兼有赋比之义,而直陈其事的赋和大略的比就不具备这种特点,也便是说,兴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还与内容的艺术表现密切干系,同样是“咏梅”毛主席的“咏梅”与陆游的“咏梅”在“寓意言外”上,其思想内容就不一样。以是与仅作为表现技巧的“赋”与“比”一比较,就高了,诗没有了“兴”也就没有内在神采了。
总之:兴”不仅仅因此一种和“比”、“赋”并列的表现技巧,它更是一首诗歌整体构思的艺术思维办法。
二.举例剖析《诗经》中“兴”这种艺术思维办法的利用诗歌创作须要形象思维,只有把摸不着,看不见的墨客的主不雅观思想情绪通过生动可感的形象诉诸给读者的感官,读者在想象中才能还原那深潜隐形的墨客内在思想感情。诗歌艺术必须通过以外物写情志,以景语写情语的办法来塑造诗歌艺术形象,离开了外物和景语的办法就成了内心情志的直接陈言,无法引起真正的想象,也就无法构成艺术形象。遐想与想象的翅膀,只能在形象的天地里展开飞行。 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情中景,景中情。” 黑格尔说:“艺术是把心灵的东西借感性显示出来。”
“兴”正是一种领悟心物的艺术思维形式,他把心灵物象化,客不雅观化,以维妙维肖的艺术形象,展现内心深处的主体情思,构成情景相生,物我浑然的艺术系统,因此可以说是“兴”把诗歌带进了艺术的殿堂。
下面我们一起举例剖析《诗经》中“兴”这种艺术思维办法的利用。
是从水鸟合欢上兴发到人类君子淑女的合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起兴在每一章首句的反复咏唱。
(一).比喻兴:
这是一种以相似遐想为思维办法的起兴办法。哀求诗歌每一节的首句的起句即先言“他物”与被引起的正文辞语之间是恰切的明显的比喻关系。从物到情,吟咏出诗情画意来。比如《国风.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该当指出,这种起兴法的比喻与“赋、比、兴”中的“比”不同,由于它不是大略的类比,以彼物比此物,而是“触物起情”。是从水鸟合欢上兴发到人类君子淑女的合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起兴在每一章首句的反复咏唱,是触物构成整首诗的意境、氛围、色调浑然成为整首诗的艺术系统之所在,不是为表君子淑女之合欢而探求水鸟来定量比喻描述:君子与淑女合欢与之一样平常。
一样平常修辞中的比喻句是闭合的、一对一的有定的,而兴中的“比”则是“兴”的一种手段、办法,是开放的,物与心之间同构成一种意象、意境。而不是一种等额关系。只有这样,它对读者的启悟力、传染力才不是有限的。
(二).象征兴:《诗经.小雅.节南山》
象征具有确定性:人们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自然形成一种习气,大家约定俗成地按照某种习气性的联系去理解象征客体及其象征意义,比如我们习惯用乌鸦象征噩耗,用青松象征龟龄等;
但是象征又具有不愿定性比如狮子可以象征刚强,也可以象征横暴。猫捕鼠机警机动可作为正面人物的象征,也有时因猫的驯良听话而把它作为阿谀奉承奴性十足的反面人物。以是象征具有多义性。
象征兴中的先言他物的起兴之辞同被引起之辞之间只有一点的意义上有共同点,或能弯曲地、隐约地有着意义上的启迪就行。诚如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比兴》说:“但有一端之相似,即可取以为兴,虽鸟兽之名无嫌也。”这种兴在《诗经》中用的比较普遍。
象征意义上,这些物象,却兴发了那虽然气概、高大显赫,却冥顽不化的太师形象
比如《诗经.小雅.节南山》: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
(第一章)
节:通“巀”。长言之则为巀嶭(jié niè),亦即嵯峨;岩岩:山崖嵬峨的样子。高显的南山,堆积的石岩象征虽然高大显赫,气概,有权有势却也有冥顽不化之意。
这里以高显的南山,堆积的石岩,以兴下文之太师的有权有势,万民所瞻而却旷废职务,使国运濒于灭绝,但在象征意义上,这些物象,却兴发了那虽然气概、高大显赫,却冥顽不化的太师形象,极尽对他的抑低感情。
三气氛兴:气氛兴也是从物与情的奇妙联系的遐想出发的,它不用比喻,也不用象征,每每捉住物质的声音、色彩,稍加点染便能托兴出,情绪、意绪与被引起的所咏之词,构成和谐的意境,领悟为一种情调,表现出特定的情思,如诗经中常常用青色,绿色等颜色兴发和表现某种怀念、感伤的感情。
比如《郑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葛维其已”(绿外衣啊绿外衣, 绿外衣里是黄衣。 心忧伤啊心优伤, 忧伤何时才停滞? );
还有《小雅.采绿》: 终朝采绿,不盈一匊。予发曲局,薄言归沐。 终朝采蓝,不盈一襜。五日为期,六日不詹。(整天在外采荩草,还是不满两手抱。头发波折成卷毛,我要回家洗沐好。
整天在外采蓼蓝,衣兜还是装不满。(装不满的忧闷)五月之日是约期,六月之日不回还。)
还有《郑风.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思念的忧闷)
还有《秦风.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心。
葛草蒹葭之类与人的怀念伤感之情,对应联接紧张是那颜色刺激所致,生理学实验表明,红橙黄等颜色属于暖色调,会使人产生间隔贴近和温静的觉得,而青绿蓝等颜色属于冷色调,每每使人产生间隔迢遥和冷凉的觉得。由间隔远和冷的觉得,使人遐想到亲友的别离,引发怀念的情绪产生不能相会的伤感。《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
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由葛的青色引发怀人的情绪,而朋侪不能到来,惆怅顿生,故有“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强烈感怀和焦虑。同样的道理,写现实的欢畅,每每又是由暖色之刺激所兴:
写情人的热恋有“”贻我彤管”: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彤管:不详何物。一说红管的笔,一说和荑应是一物。有的植物初生时或者才萌芽不久时呈赤色,不仅颜色鲜亮,有的还可吃。如是此意,就与下文的“荑”同类。但是也可能是指涂了红颜色的管状乐器等。
写夫妻新婚有《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写夫妻新婚有《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花怒放千万朵,色彩鲜艳红似火。这位姑娘嫁过门,夫妻美满又和顺。夭夭:花朵怒放,俏丽而繁华的样子。灼灼:花朵色彩鲜艳如火,通亮鲜艳的样子。华:同“花”。);
《卫风.硕人》中: “四牡有骄,朱幩镳镳。”(四匹公马多雄壮,红绸挂在马嚼旁。) ;
写友朋之欢宴有《小雅.彤管》:“彤弓弨兮”等。
还有以声音触发起兴的。《乐记》云:“凡音之起,从民气生也。”声音也能起到沟通契合主体情绪意绪并实现同构。 比如描写男女约会的《陈风.东门之杨》: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
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
昏以为期,明星晢晢。
该首诗中“其叶牂牂”、“其叶肺肺”; “牂牂”是杨树叶子在风中摩擦的声音。“肺肺”是风吹过杨树叶产生的声音。一个声音响亮,一个声音细微,陪衬表现出男女约会之热烈感情和款款的柔情,极尽了“人约薄暮后”的美妙情志。
我们再看《齐风.鸡鸣》: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
匪鸡则鸣,苍蝇之声。
东方明矣,朝既昌矣。
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
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
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
这首诗中的“虫飞薨薨”也因此声音起情。 “薨薨”则是指和谐的催眠之声,与主人公“甘与子同梦”的特定感情契合,故成妙境。
以上所说的起兴都是“顺向遐想”形成的“顺向对应”。色彩也好,声音也好和抒情人的情绪是同等的。
还有可以利用“比拟遐想”形成“逆向的对应”,既“反衬”起兴:瞥见俏丽的景致,却伤心,听见欢畅的音乐,却生哀思。
比如《邶风.凯风》: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
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
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痊,在浚之下。
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凯风:和风。一说熏风,夏天的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凯之义本为大,故《广雅》云:‘凯,大也.’秋为敛而主愁,夏为大而主乐,大与乐义正相因." 睍睆(xiàn huǎn现缓):犹"间关",清和宛转的鸟鸣声。一说俏丽,好看。黄鸟:黄雀。
译文 :
和风吹自南方来,吹拂酸枣小树苗。树苗长得茁又壮,母亲养子多费力。
和风吹自南方来,吹拂枣树长成柴。母亲贤惠又慈祥,我辈有愧不长进。
泉水寒冷刺骨凉,就在浚城墙外边。养育儿女七个人,母亲养育多费力。
俏丽可爱的黄鸟叫,清脆婉转似歌唱。养育儿女七个人,无谁能安母亲心。
这首诗中“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睍xiàn睆huǎn:犹“间关”,鸟儿宛转的鸣叫声。一说俏丽,好看。黄鸟:黄雀。)
前两句以关关黄鸟之婉转歌声起情,以兴起下文作为儿子的自我责备之情,是明显的听到快乐的音乐而生起哀思之情。
朱熹阐明说:“黄鸟犹能好其音以悦人,而我之七子有犹不能慰忧母心哉。”(《诗集传》)
《郑笺》 也说:“好其音者,兴其辞令顺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这类兴法,在《诗经》中也霸占相称多的篇目。
四.推理兴:推理兴是从物与心的联结形态上划分的。“他物”与“所言之辞”有某种推理关系。但这不是理性逻辑化的,不仅没有明显的逻辑步骤,是靠直觉感悟联通的,而且这种推理关系也是兴这种方法所特有的。在抽象逻辑里未必说得通。一种遐想和想象的产物。
“人生贵有朋友”。因此,鸟类尚且寻求友声,何况我们人类呢?
如《小雅.伐木》: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
出自深谷,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相彼鸟矣,犹求友声。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译文:
咚咚作响伐木声,
嘤嘤群鸟相和鸣。
鸟儿出自深谷里,
飞往高高大树顶。
小鸟为何要鸣叫?
只是为了求知音。
仔细端详那小鸟,
尚且求友欲相亲。
何况我们这些人,
岂能不知重交情?
天上神灵请聆听,
赐我和乐与宁静。
是由于嘤嘤鸟鸣寻求友声而兴发人之应求友的情绪。“人生贵有朋友”。因此,鸟类尚且寻求友声,何况我们人类呢?
《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
人而无仪,不去世作甚?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
人而无止,不去世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胡不遄去世?
译文
你看这黄鼠还有皮,人咋会不要脸面。
人若不要脸面,还不如去世了算啦。
你看这黄鼠还有牙齿,人却不顾德行。
人要没有德行,不去去世还等什么。
你看这黄鼠还有肢体,人却不知礼义。
人要不知礼义,还不如快快去世去。
此篇三章重叠,以鼠起兴,强调“你看这黄鼠还有皮,人咋会不要脸面!
”意思并列,但各有侧重,第一章“无仪”,指外表;第二章“无止(耻)”,指内心;第三章“无礼”,指行为。“他物”与“所言之辞”有某种推理关系。这种逻辑关系是靠一种遐想和想象的产物。是靠直觉感悟联通的。如果用科学的抽象逻辑思维未必讲得通,但墨客的强烈的情绪成分在里面,便有着震荡民气的传染力和讽刺意味。
总之,通过我们对《诗经》中“兴”这种艺术思维办法的利用的举例剖析,“兴”不仅仅因此一种和“比”、“赋”并列的表现技巧,它更是一首诗歌整体构思的艺术思维办法。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动听,故摇荡脾气,形诸歌咏”,我们人具有情绪天生机制,墨客在诗歌创作中的终极出发点,都是“因物而生情绪””,“兴发而成诗”。我们本日讲的“兴”便是这种特质的表示。宋代胡寅特殊推崇李仲蒙的讲授,他说:“赋比兴,古今论者多矣,惟河南李仲蒙之说最善。”李仲蒙他认为“赋”是“叙事以言情”;“比”是“索物以托情”;而“兴”则是“触物以起情”,这就讲明白了以是要构思诗篇,提笔写诗源于墨客“触物以起情”的结果。而“比”与“赋”仅仅是写作过程的技巧罢了。以是谢榛说:“凡作诗,悲欢皆由乎兴,非兴则造语弗工。”
而无论是当代诗歌还是古典诗歌,我们会创造以“兴”的思维办法构思诗歌的,民歌最多:
仅从诗经三百零五篇看:“兴也”的共一百一十六篇,个中风占七十二篇,小雅占三十八篇,大雅和颂只有六篇。《诗经》中的《国风》共一百六十片而用兴的就有七十二篇,占了近一半。《国风》的作者大都是来自于民间的歌手,代代相传。这些采集来的民歌,是劳动人民发自内心的歌声。是真情的自然流露。由此不雅观之大凡成功之作,都是感情的自然引发起兴乃天籁之音。
诚如李梦阳《诗集自序》引王叔武云:“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士,比兴寡而坦直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蠡蠡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兴也、呻也、呻吟也、行呫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兴焉,非其情也,斯足以不雅观义矣。故曰: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
王叔武说:“诗有六义,比兴最主要。文人学子,比兴少但坦直多,为什么呢?从真情实感出发的少而善于言词的多。那些路途街巷的愚拙之人,本来没有文华词采,竟然他们歌唱的,哼唱的,吟诵的,行走的时候小声低语,坐下来就唱歌,用饭的时候喝斥,睡醒就说话,这里唱起来那里就应和着,没有哪个时候没有比呀兴呀,无处不是他们的真情(在表露),这足以不雅观察到(诗中的)义。以是说:诗,是天地自然之音。”
在这里李梦阳见告我们一个道理:民间墨客在生活中随意马虎被“外物触发”而“起兴”,他们的创作比闷在屋里的创作要好得多。好就好清闲生活中兴发的是自然勃发而得的天籁之音之音。